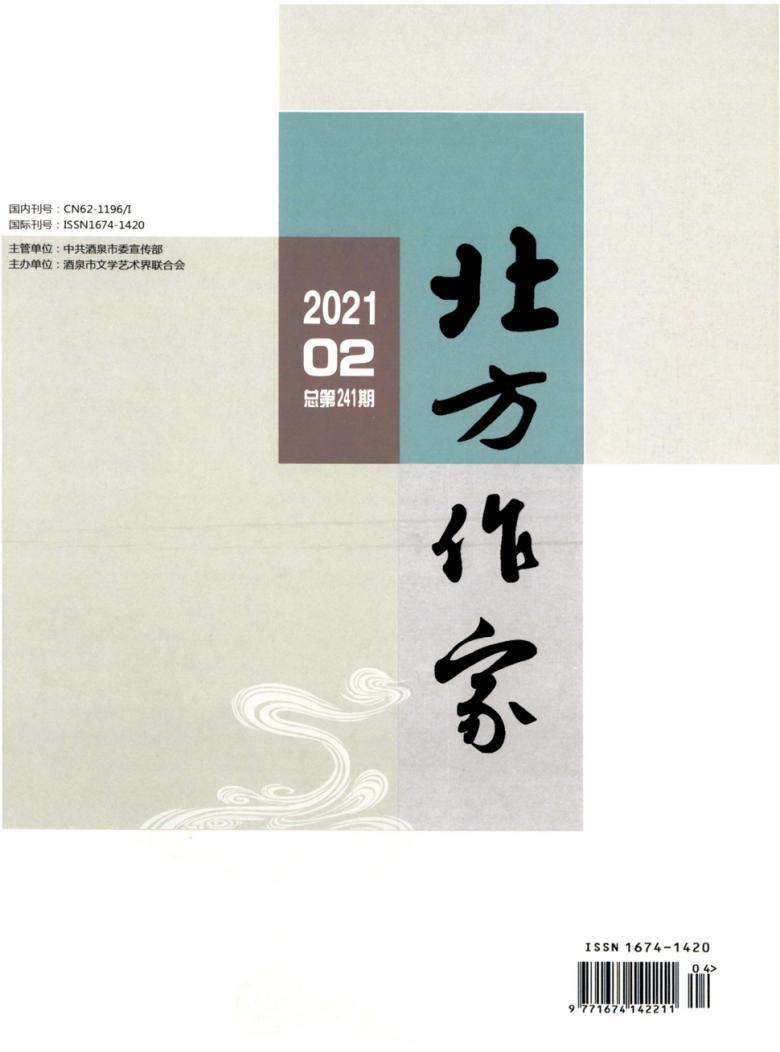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與中國現代歷史研究的互動
王彬彬
首先解題。題中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指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題中的“中國現代歷史研究”則指對中國現代歷史的研究。“互動”,則指兩種研究的相互促進、相得益彰,指兩種研究既相輔相成,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與中國現代歷史研究,不但是兩個各自獨立的學科,而且在大學里,分屬兩個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屬于中文系的學科,而中國現代歷史研究屬于歷史系的學科。如今,學科的設置越來越細化,同屬一系的學科之間,也往往壁壘森嚴,“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學科與學科之間是這樣,具體到研究者個體,通常的情形也是畫地為牢,嚴守自己的“專業”,不越雷池半步。在專業越來越細化的同時,是研究者“專業意識”的越來越強化。香港和臺灣大學里的情形我不太了解,但我知道在中國大陸的大學里,每一“專業”內又叢生出許多“方向”。我們慣常見到的是,一個研究者選擇本“專業”內的某個“方向”,年復一年地“做”著。非本“專業”甚至非本“方向”的書,不讀;非本“專業”甚至非本“方向”的事,不想。這樣“做”的結果,是學術之路越走越窄。至于屬于中文系的中國現代文學專業,與屬于歷史系的中國現代歷史專業,那就非但是“老死不相往來”,甚至連“雞犬之聲”也不“相聞”的。在中文系討生活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認為中國現代歷史,是與自己無關的東西。中國現代歷史研究的現狀如何,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者漠不關心。在中國現代歷史研究界,哪些舊說受到了質疑、哪些新說引起了注意、哪些問題得到了澄清,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習慣于認為那都是“別人家”的事,是他人的“瓦上霜”而非自家的“門前雪”。如果說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者對中國現代歷史不感興趣,那中國現代歷史的研究者,與中國現代文學則更是隔膜了。
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與中國現代歷史研究兩不相干的現象,實在是不合理的。中國現代文學是在中國現代這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發生和發展的,它的興衰、它的演變,都與歷史的進程密切相關。對于歷史進程來說,文學的發展又并不純粹是被動的。文學也有能動的一面。通常我們所說的歷史,是指政治史。政治史當然影響著、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文學史。在中國現代,由于政治與文學的關系空前緊密,政治對文學的作用也就表現得空前明顯。但是,在中國現代,不僅是政治作用于文學,文學也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歷史。換言之,不僅是歷史在某種意義上創造了文學,文學也在一定意義上創造了歷史。所以,將對中國現代歷史的研究與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結合起來,是有著充分的依據的。
一
將歷史研究與文學研究相結合,讓歷史與文學相互印證、相互說明,這方面前輩學者陳寅恪已經樹立了光輝的榜樣。汪榮祖所著《陳寅恪評傳》,第八章專論陳寅恪的“詩史互證”。汪榮祖說:“寅恪早年在清華曾授‘唐詩校釋’一課,晚年復在廣州中山大學講授‘唐代樂府’以及‘唐詩證史’等課程,生平箋證詩篇之作亦復不少。但其箋詩、證詩所憑藉者,乃是歷史的眼光與考據的方法;一方面以詩為史料,或糾舊史之誤,或增補史實闕漏,或別備異說;另一方面以史證詩,不僅考其‘古典’,還求其‘今典’,循次披尋,探其脈絡,以得通解。寅恪以詩為史料,固為史家致知辟一新途徑,清人楊鐘羲于《雪橋詩話》中,雖已言及以詩證史之事,然運用純熟,發明之多,實以寅恪始。寅恪以史證詩,旨在通解詩的內容,得其真相,而不在評論詩之美惡與夫聲韻意境的高下,其旨趣自與正統詩評家有異。”(1)汪榮祖最后所說的陳寅恪以史證詩但不涉及詩之藝術價值一事,尚有商榷之余地,后面再論。這里先指出,汪榮祖據說的“古典”、“今典”,出自陳寅恪《讀哀江南賦》一文的引言。陳寅恪撰《讀哀江南賦》,分上、下兩部分,而在正文前面,有這樣的引言:“古今讀哀江南賦者眾矣,莫不為其所感,而所感之情,則有淺深之異焉。其所感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較多。蘭成(引按:庾信小字蘭成)作賦,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雖不同物,若于異中求同,同中見異,融會異同,混合古今,別造一同異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覺,斯實文章之絕旨,而作者之能事也。自來解釋哀江南賦者,雖于古典極多詮說,時事亦有所征引。然關于子山(引按:庾信字子山)作賦之直接動機及篇中結語特所致意之點,止限于詮說古典,舉其詞語之所從出,而于當日之實事,即子山所用之‘今典’,似猶有未能引證者。故茲篇僅就此二事論證,其他則不并及云。”(2)陳寅恪在這里,其實也言及以史證詩與對詩的藝術鑒賞這二者之間的關系,也姑且不論。從這番引言中,我們可知,陳寅恪以史實證文學作品,是要說明作品寫作時的“當日之事”,即準確地揭示作品產生的時代背景,同時也對作品中“寫實”的部分,做出合理的解釋。
在對唐詩和唐史的研究中,陳寅恪詩史互證的手法用得最多、最典型、最純熟,也最能給人以方法論意義上的啟發。陳寅恪作為歷史研究者和作為文學研究者的雙重身份,在以唐詩證唐史和以唐史證唐詩的過程中,水乳交融、渾然一體,而在這詩史互證過程中所發表的觀點、所得出的結論,則美不勝收。《李德裕貶死年月及歸葬傳說辨證》、《以杜詩證唐史所謂雜種胡之義》、《書杜少陵哀王孫詩后》、《元白詩中俸料錢問題》等論文(3),或以詩證史,或以史證詩,從而精義紛呈。以詩證史,可以《元白詩中俸料錢問題》為例。元白詩中,多涉及俸料之事,白詩中尤多。陳寅恪將元白詩中涉及俸料處,與舊史書中關于唐代官吏俸料的記載相比照,糾正了舊史書中的一些謬誤。陳寅恪發現,凡是中央政府官員的俸料,與元白詩中所言無不相同,但唐代地方官吏之俸料,史籍所載與元白詩中所言差距甚大。陳寅恪說:“凡屬中央政府官吏之俸料,史籍所載數額,與樂天詩文所言者無不相合。獨至地方官吏,(京兆府縣官吏,史籍雖附系于京官之后,其實亦地方官也。)則史籍所載,與樂天詩文所言者,多不相合。且樂天詩文所言之數,悉較史籍所載定額為多。據此可以推知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載于法令,而可以認為正當之收入者,為數遠在中央官吏之上。”(4)從元白詩中所言俸料入手,陳寅恪弄清了唐代歷史上的一個大問題。以史解詩,則可以《書杜少陵哀王孫詩后》為例。這篇作于1953年4月的文章,一開頭就說:“杜少陵哀王孫詩為世人所習誦,自來箋釋之者眾且詳矣,何待今日不學無術,老而健忘者之饒舌耶?然于家塾教稚女誦此詩,至‘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之句,則瞠目結舌,不能下一語,而思別求一新解。”(5)在家中教稚女讀杜甫《哀王孫》詩時,陳寅恪突然發現“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中的“朔方健兒”難以解釋。如果說杜詩中“朔方健兒”指整個朔方軍,則顯然于理不合。安祿山叛變,幸賴朔方軍平定。朔方軍乃唐室中興之關鍵。對朔方軍,杜甫滿懷感激,在不少詩中對朔方軍主帥郭子儀、李光弼等熱情歌頌,所以不可能對朔方軍下“今何愚”之語。如果像一些釋杜詩者那樣,認為“朔方健兒”泛指安祿山所統領的北方軍隊,陳寅恪認為也不通,因為在唐代,“朔方”為一軍政區域的專有名詞,并不能用來泛指北方士卒。陳寅恪憑藉對唐代歷史和地理的熟稔,認為這里的“朔方健兒”指原屬朔方軍的同羅部落。安祿山誘害同羅部落酋長阿布思,襲取其兵卒。同羅部落原為朔方軍勁旅,歸附安祿山后則成為安祿山叛軍之主力。至長安后,同羅部落復又叛歸其舊巢,陳寅恪說:“同羅昔日本是朔方軍勁旅,今則反復變叛,自取敗亡,誠可謂大愚者也。”(6)沒有對唐代歷史和地理的精細知識,就不能對杜甫《哀王孫》詩中“朔方健兒”做出準確的理解;而不能準確地理解“朔方健兒”之意,就很難說準確地理解了整首詩。
最集中也最典型地體現了陳寅恪詩史互證之方法和成就者,還是《元白詩箋證稿》一書。在這部書中,陳寅恪運用他對唐代歷史的多方面的知識解讀元白詩,往往鑿破渾沌、洞幽燭微。同時,也以元白詩中對歷史細節的言說糾正史籍中的某些謬誤。例如,白居易《長恨歌》中有這樣兩句:“云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曖度春宵。”一般人都會認為這只不過是詩人描寫美人的慣常手法,是一種修辭方式而已。但陳寅恪告訴我們,所謂“金步搖”,其實是寫實,因為“天寶初婦人時世妝有步搖釵”(7)。當我們明白楊妃頭上確實戴著那金制的“步搖釵”時,她那美麗的形象就更加清晰了。再例如,《長恨歌》中“漁陽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這一“破”字,人們也習慣于認為指中止、破散,形容慌亂之態。而陳寅恪卻告訴我們,“破”其實是當時的一個樂舞術語。白居易《臥聽法曲霓裳》詩中,有句曰:“宛轉柔聲入破時”,這里的“破”,也是指樂曲的某個階段。所以,“驚破霓裳羽衣曲”:“特取一‘破’字者,蓋破字不僅含有破散或破壞之意,且又為樂舞術語,用之更覺渾成耳。又霓裳羽衣‘入破時’,本奏以緩歌柔聲之絲竹。今以驚天動地急迫之鼓,與之對舉。相映成趣,乃愈見造語之妙矣。”(8)明白了“破”原是一樂舞術語,明白了《霓裳羽衣曲》演奏到“破”時,是“宛轉柔聲”,我們就更好地欣賞了這句詩。類似的例子舉不勝舉。文學研究與歷史研究的互動,在《元白詩箋證稿》中達到了極高的境界。陳寅恪的這部書,既是唐代文學研究,又是唐代歷史研究。唐史研究和唐詩研究的互動,使我們對唐史和唐詩的理解都在多方面更為精細和準確了。
二
陳寅恪以唐史證唐詩,又以唐詩證唐史,這在方法論的意義上給我們以深刻的啟示。
中國現代文學與中國現代歷史的關系,在總體上,遠較唐代文學與唐代歷史的關系更為緊密。在中國現代,有許多事件和人物,既是政治性的,又是文學性的。政治性和文學性在這些事件中,在這些人物身上,往往相互制約、相互影響。“五四運動”被認為是中國現代歷史的開端,同時也被看作是中國現代文學的揭幕。所謂“五四新文學運動”,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之一部分;而所謂“五四新文化運動”則是“五四運動”之一部分。作為一場政治運動的“五四運動”,爆發于1919年5月4日。但新文化運動卻在此前幾年即轟轟烈烈地開始了。作為一場政治運動的“五四運動”,在某種意義上,是此前即展開的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結果,這也基本上是學界的一種共識。而作為一場政治運動的“五四運動”,無疑又在多方面影響了此后的文化和文學的發展。“五四新文學”屬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范疇,而作為一場政治運動的“五四”,則是中國現代史這一學科的研究對象。但是,對“五四新文學”的認識,離不開對整體的“五四運動”的理解;而對整體的“五四運動”的研究,也無法忽視新文學運動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美籍華人學者周策縱是以歷史學家的身份撰寫《五四運動史》的。在這部廣受好評的史學專著中,周策縱充分注意到了新文學運動在整個“五四運動”中的地位。周著第三章為《運動的萌芽階段:早期的文學和思想活動(1917—1919)》。這一章,詳細地論述了1919年5月之前的幾年間,以北京大學為中心的新文學運動,而這種新文學運動正是作為一場政治運動的“五四”的萌芽。對這期間文學運動中的一些細節,周著都高度重視。例如,在論及保守派的反抗時,周著甚至將林紓攻擊陳獨秀、胡適等人的文言小說《荊生》摘錄了千余字。(9)周策縱這樣做的目的,是要說明這個道理:“要是‘五四事件’沒有發生的話,在北大和其他大學里的新思想運動很可能就會被政府鎮壓了。”(10)1919年5月之前興起的新文學運動與1919年5月爆發的作為一場政治運動的“五四”之間,有著這樣一種關系:1919年5月之前的幾年間興起的新文學運動,某種意義上為1919年5月的政治運動做了準備,1919年5月的政治運動,在一定意義上是此前幾年間新文學運動所結出的果實;但另一方面,如果沒有1919年5月爆發的政治運動,新文學運動很可能就會被以強力撲滅。1919年5月的政治運動,既是新文化運動的女兒,又是新文化運動的保姆。周著第七章《新文化運動的擴展(1919—1920)》,則詳細論述了1919年5月之后,新文學運動的蓬勃發展。1919年5月之前的新文學運動,催生了1919年5月的政治運動,而1919年5月的政治運動又為新文學的進一步發展掃除了障礙、開辟了道路:文學與政治(歷史)就是這樣難解難分。有了第三章和第七章的論述,周策縱仍嫌不夠,第十一章《文學革命》,又更集中地對“五四新文學”進行了研究。這一章以這樣的一段話作結:“從1917年開始的新文學運動的實踐是成功的;其結果是,過時的文言和陳腐的舊文學的迅速衰落。白話文開始被寫作和教學廣泛應用。隨著書面語和口語的統一,知識和教育變得更易普及。除此之外,詩歌、散文、短篇小說、長篇小說和戲劇都有新的開端。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也取得了很大進步。文學因此更接近于生活和社會現實。它也受到了更廣泛的喜愛。新文學的自然主義和社會主義傾向,在后來對中國青年的思想和心理發展都產生了巨大影響。正是從這些意義上說,文學革命在現代中國思想和社會政治轉型時期扮演了重要角色。”(11)
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全書連《導言》共14章,而在第三章、第七章和第十一章集中地論述了新文學運動與作為政治運動的“五四”之間的關系。這樣的章節安排是基于這樣的歷史事實,同時也是為了揭示這樣的歷史事實:新文學運動在某種程度上催生了作為政治運動的“五四運動”;作為政治運動的“五四運動”又為新文學運動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條件;新文學的蓬勃發展,導致了白話文的普及,導致了社會意識、群體觀念的眾多變化,而這又深刻地影響了此后的歷史進程。——這讓我們想到,中國現代文學和中國現代歷史,本身就是互動的。
不僅是“五四”時期的文學與政治輔車相依,因而必須將二者結合起來研究,還有一些人物,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和中國現代政治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例如陳獨秀;例如胡適;例如瞿秋白。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帥,陳獨秀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光彩奪目;作為中共的創始者和首任領袖,陳獨秀在政治史上的地位舉足輕重。胡適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自不待言,作為政論家、作為駐美大使、作為1929年“人權運動”的核心人物,胡適在中國現代政治史上也自有一席之地。瞿秋白則既是現代著名政治人物,又在現代左翼文學運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這些人,既是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研究對象,又是中國現代史學科的研究對象。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側重從文學方面研究他們,中國現代史學科則側重從政治方面研究他們。但他們作為一個完整的人,本身卻是無法分割的。 陳寅恪是作為一個杰出的唐史專家以唐史解唐詩的,他用以解唐詩的那些歷史認識,往往是他對歷史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獨特認知。要求一般的古典文學研究者都能達到這種境界,顯然是不現實的。對于一般的古典文學研究者來說,能做到具有盡可能豐富的古代歷史知識,能熟悉古代史籍,能及時關注同時代歷史學界的最新成果,就算難能可貴了。但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來說,這樣的要求卻又并不夠。如果有人認為,現代由于與我們離得近,所以我們對現代史的認識會比對古代史要清楚,那就是極大的誤會。實際上我們對現代史的認識,比起古代來要模糊得多。古代由于年代久遠,有一代又一代研究者的努力,從宏觀到微觀,我們都看得比較清楚了。又由于古代的是非一般說來與我們沒有利害關系,我們在認識和評價古代人和事時,不至于意氣用事,不至于受個人利益的影響。而現代史則不同。現代史正由于離得近,使我們難以看清其真相。這里的原因有這樣幾種:首先,意識形態嚴重地左右著我們對現代史的認識和評價;其次,現代史的許多史料還沒有公開,還沒有“解密”;還有,現代史與我們個人的利益往往糾纏在一起,現代史的研究者,往往是現代史的一部分,這使得人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從總體上說,中國現代史還是一本糊涂賬。由于現代史具有這樣的性質,一般來說,我們便不能無條件地相信關于現代史的那些所謂“定論”,不能無條件地相信關于中國現代史的那些流行見解。
那么,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者,面對現代史這本糊涂賬,應該怎么辦呢?惟一的回答是:自己去一筆一筆地弄清。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者,當我們面對的某個文學問題與某種歷史現象密切相關時,我們切勿輕易地借助和依賴關于此種歷史現象的現存看法,而應該用自己的眼光去分析和研究這種歷史現象。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一個合格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首先應該是一個合格的中國現代歷史研究者。 三
但認可現存的歷史結論并據此解讀評價文學作品和文學現象,在中國大陸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仍是相當普遍的。不妨以對茅盾《子夜》的解讀和評價為例。
幾乎所有的大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撰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都會對《子夜》做出這樣的解讀和評價:進入1930年代,中國理論界發生了一場著名的爭論,“托派”錯誤地認為中國已進入資本主義社會。而茅盾的《子夜》則形象地回答了“托派”的謬論,讓人們看到,中國并沒有走向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中國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通過民族資本家吳蓀甫的悲劇命運,茅盾準確地把握了1930年代中國社會各階級、各階層的思想、性格、心理、命運及其歷史糾葛,完整地反映出整個大時代的全部豐富性與復雜性。吳蓀甫的悲劇命運說明了:在帝國主義統治下,中國民族工業是永遠得不到發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是永遠不可能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
作為所謂社會剖析小說的代表作,《子夜》的價值相當程度上取決于對社會的準確深刻的剖析。如果作品對當時中國社會的剖析真是準確而深刻的,那它的價值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如果作品對其時中國社會的剖析不那么準確深刻,如果其時的中國“不可能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這一結論并不那么正確,《子夜》的價值就十分可疑了。《子夜》通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人物命運的展示來剖析中國社會,而如果這種剖析是片面的、膚淺的、充滿偏見的,那人物形象也只能是虛假的、呆滯的、缺乏藝術光彩的。——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阪口直樹,在《十五年戰爭期的中國文學》一書中,就在對其時中國社會研究的基礎上,質疑了《子夜》的價值。
阪口直樹對國民黨內的政治性分配、南京國民政府與浙江財閥及“四大家庭”的關系、南京國民政府進行的經濟改革等進行了研究,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觀察二三十年代中國經濟體制的另一種角度。阪口直樹贊同這樣的觀點:(一)從1927年至1937年間,中國的全體經濟呈現緩慢的增長,這種經濟增長的過程同時也是經濟自主的過程。(二)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國,要在民族資本家和買辦資本家之間劃出一條清晰的界線,其實是很困難的。(三)蔣介石政權成立之初,雖然是以“四大家族”為經濟后臺,但隨著官僚資本的發展,兩者間的關系亦發生逆轉。(12)這些,都對我們既有的觀念是一種顛覆,也使《子夜》的價值基礎面臨危機。在研究了南京政府所進行的一系列經濟改革后,阪口直樹指出:“以上從南京國民政府實施的一連串財政政策,可看出南京政府意圖從外國資本(帝國主義)中確立財政獨立,自1927年起至1935年為止的八年間,南京國民政府逐漸脫離依賴外國資本(和其勾結的買辦)的體制,故可將此八年定位為‘逐漸轉為自立性體制’的時期。直到目前為止,原本在對中國的經濟結構方面,以‘官僚資本對民族資本’這種單純構圖來理解是很勉強的。”(13)通過研究,阪口直樹強調,在《子夜》所寫的時代,以蔣介石為中心的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經濟結構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官僚資本與買辦資本并不是一回事。本來,與“民族資本”相對的,應該是“外國資本”,而與“官僚資本”相對的,應該是“民間資本”。但“官僚資本”也可以包括私人資本,所以又同時具有“民族資本”的性質。而《子夜》卻把其時中國的經濟結構簡單地歸結為“買辦資本”與“民族資本”的對立,完全忽視“官僚資本”的存在,或者簡單地把“官僚資本”與“買辦資本”混為一談。在歷史研究的基礎上,阪口直樹得出這樣的結論:“《子夜》出版于1933年,而做為《子夜》舞臺的1930年代,正值國民黨形成官僚資本的發展時期。在此時期,以‘四大家族’(浙江財閥)為財政基礎的蔣介石國民黨政權,努力朝向官僚資本主義發展(或蛻變)。上述兩個時期也就因此而交相重疊。其次若從上述觀點來看《子夜》對中國經濟的處理方式,可知其間仍存有重大的問題。換言之,《子夜》是以忽視蔣介石政權及買辦兩者間的差異,而將其合為一體做為處理對象,進而只處理民族資本家及買辦資本家對立的構圖,而未處理兩者間的同質性問題。此點為顯現中國當時全貌的重點,而其認知不足和對趙伯韜曖昧的描寫有很大的關聯性。”(14)阪口直樹認為,《子夜》對其時中國經濟社會的把握是不準確的,有著重大偏差。而這也影響到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子夜》中,趙伯韜的形象,是較為曖昧、模糊的,究其原因,則在于趙伯韜這個人物,現實依據不足,是作者依據某種理念,強行塑造的。
由于我本人是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在本文中,我更多地強調了歷史研究對文學研究的意義。但中國現代歷史的研究者,也同樣不能忽視中國現代文學對歷史進程的影響,也應該意識到,從文學的角度切入某些歷史問題的必要。例如,20世紀30年代,青年知識分子的左傾化潮流,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現象,中共最終戰勝國民黨、奪取大陸政權,都與此有明顯關系。30年代從清華園到了延安的韋君宜晚年回憶說:“有什么路可走?惟一的抗日之路是左傾的路,尤其是左傾的文學的路。魯迅、茅盾、郭沫若、丁玲、巴金……這些名字差不多統領了中國文壇。連不屬左派的文人也是只見往左倒,不往右傾。毛澤東說中國有文化新軍,確實不假。我就因中學的一個老師介紹,讀了這些左翼作品,方知道真抗日的只有左派。”(15)左翼文學在當時的特定條件下,是以一種什么方式讓韋君宜這樣的青年學生認定“真抗日的只有左派”,又是如何使他們放棄了國民黨而選擇了共產黨,這是當時重大的政治問題,在今天,則是重大的歷史問題。左翼文學在現代史上的政治意義,固然也屬現代文學學科的研究范疇,但也是現代史研究者不能回避的。這樣的研究,既是文學研究,也是歷史研究。在這樣的研究過程中,文學與歷史不僅僅是互動,甚至走向交融。
陳寅恪以詩證史,所證的不僅是古代的政治史,也有古代思想史。對于思想史的研究者來說,歷史上的文藝作品也是一種獨特的資料。今人葛兆光,是中國古代思想史的研究者。在論及“什么可以成為思想史的資料”時,強調了“小說話本戲曲唱詞”在思想史研究中的作用。楊家將故事、包公故事、三國故事,都蘊藏著豐富的思想史信息。唐詩宋詞也能成為研究唐宋思想的資料。葛兆光還談到,西方的一些重要的思想著作,如鮑默的《西方近代思想史》、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體》等,在論及那些嚴肅深刻的思想觀念時,常常借助通信、小說、繪畫、雕塑等文藝作品為佐證。(16)在中國現代,文學與思想的關系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緊密,文學作品在思想上的影響,往往超過那些理論性著作。例如,研究20世紀30年代中國思想狀況,就不應該無視茅盾小說《子夜》的存在。《子夜》表達了當時某種很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它比那些純理論性著作更好地顯示了這種思想產生的根源及其破綻、局限。
四
讓我們再回到陳寅恪。前引汪榮祖論陳寅恪以史證詩時,有這樣的話:“寅恪以史證詩,旨在通釋詩的內容,得其真相,而不在評論詩之美惡與夫聲韻意境的高下,其旨趣與正統詩評家有異。”陳寅恪的以史證詩,出發點固然主要不在詩的藝術價值。但是,如果認為以史證詩,全然與對詩的審美鑒賞無關,全然無助于對詩的藝術價值的評說,則又是頗為謬誤的。實際上對文學的“內容”、“真相”的了解,與對其藝術性的鑒賞,往往是相關聯的。對其“內容”、“真相”的了解越準確,對其藝術性的鑒賞就越到位。陳寅恪在以史證詩時,也決不只是“通釋詩的內容,得其真相”。他常常在指出某種史實的同時,或多或少地引伸到對詩的藝術性的評說。例如,前面所引陳寅恪對“漁陽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的評說:“句中特取一‘破’字,蓋破字不僅含有破散或破壞之意,且又為樂舞術語,用之更覺渾成耳。又霓裳羽衣‘入破時’,本奏以緩歌柔聲之絲竹。今以驚天動地急迫之鼓,與之對舉。相映成趣,乃愈見造語之妙矣。”這番話,是在指出“真相”,但更是在進行審美鑒賞。明白了“破”字并非僅僅是詩人藻飾之語,而且也是一種樂舞術語、指樂曲的某個階段時,我們就體會到了詩人下一“破”字時的匠心獨運,也就是陳寅恪所謂的“用之更覺渾成”。霓裳羽衣曲演奏到“破”時,是“緩歌柔聲”的,而值這“緩歌柔聲”之時,有鼓“驚天動地”地響起,兩相對照,更覺意味無窮,也就是陳寅恪所謂的“乃愈見造語之妙”。所以,如果說陳寅恪以史證詩而完全不關乎“詩之美惡與夫聲韻意境的高下”,那顯然是不合乎實際的。
歷史研究對文學研究的意義,不僅僅是外部的,不僅僅只有助于我們全面、準確和深刻地認識文學作品的時代背景,對于我們領會作品的藝術價值,也往往有著直接的幫助。
注釋:
(1)汪榮祖:《陳寅恪評傳》,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頁。
(2)陳寅恪:《讀哀江南賦》,《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09頁。
(3)這些論文均見《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4)陳寅恪:《元白詩中俸料錢問題》,見《金明館叢稿》二編。
(5)(6)陳寅恪:《書杜少陵哀王孫詩后》,《金明館叢稿二編》,第54頁,第57頁。
(7)(8)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4頁,第30頁。
(9)見周策縱:《五四運動史》,岳麓書社,1999年版,第89~91頁。陳永明等譯。
(10)(11)周策縱:《五四運動史》,第99~100頁,第405頁。
(12)(13)(14)阪口直樹:《十五年戰爭期的中國文學》,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年版,第52~53頁,第56頁,第57頁,宋宜靜譯。
(15)韋君宜:《思痛錄》,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2頁。
(16)見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四講《什么可以成為思想史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