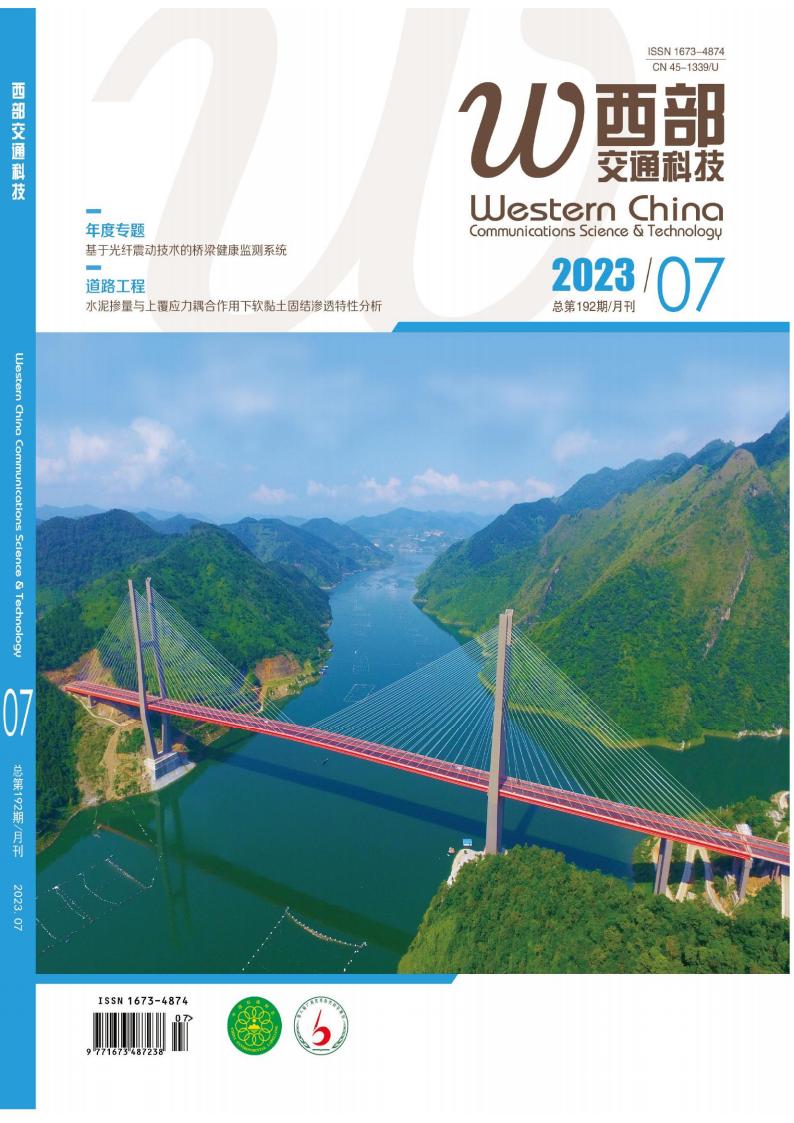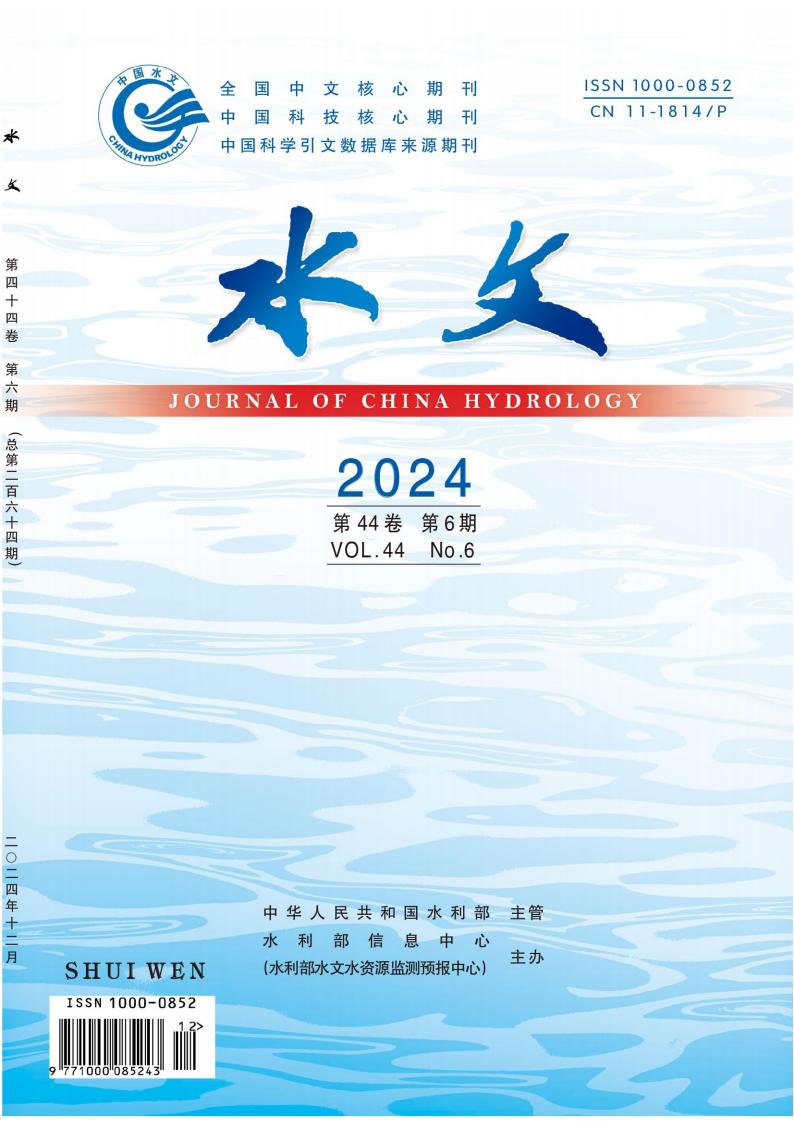關于芥川龍之介文學創作中的中國元素解讀
馬巖
論文關鍵詞:芥川龍之介;新思潮派;文學創作;反自然主義文學;中國元素
論文摘要:芥川龍之介是日本新思潮派最杰出的代表作家,他集新理智派和新技巧派文學特征于一身,無論是在對人物的心理描寫還是在敘事技巧的構建上,都可謂匠心獨運,構思縝密。解讀芥川龍之介文學創作中的中國元素是研究日本近代文學的重要課題之一。
日本中短篇小說家芥川龍之介是一位天才型作家,其作品從內容到形式都經過苦心的雕琢和推敲,意旨幽深,立意精辟,文采清俊,修辭美妙,特別是對人性的刻畫人木三分并富有張力,作品充滿思想性、智慧性和巨大的感染力,代表了日本近代文學創作的最高美學成就及藝術品位。在芥川龍之介的文學創作中有一個極為重要的特征就是中國元素對其創作的影響。
一、芥川龍之介創作中的中國文學思想之成因
芥川龍之介少年時代的生活經歷并不是一帆風順,他生于東京,本姓新原。但因母親精神失常、父親再婚等原因,從小被其舅父芥川道章收養,改姓芥川。芥川家世代在將軍府任文職,明治維新后,養父在東京府任土木科長,養父母精通琴棋書畫,家庭有濃厚的傳統文化藝術氣氛。芥川自幼就受到中日古典文學的熏陶,在養父一家的影響下,尤其喜歡中國古典作品,在童年時代他就被悠久的中國歷史和璀璨的文化所吸引。他讀了很多中國的古典小說,并從中認知、了解中國。芥川龍之介大學時代主攻英文,但最為拿手的卻是漢文。他在念小學時便讀了《水滸傳》、《西廂記》,中學時代又讀了《聊齋志異》、《金瓶梅》和《三國演義》,并喜歡漢詩。這些不僅使他具有較高的中國文學與文化修養,而且更重要的是培養了他的“中國文學與文化的情愫”。中國的文學與文化對他的人生觀、世界觀乃至藝術觀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些在他的文學創作中都有所表現。“自1914年到1927年的文學創作中有12篇是取材于中國。具體有《酒蟲》、《仙人》、《奇遇》、《黃粱夢》、《英雄之器》、《杜子春》、《尾生的守信》、《秋山圖》、《掉頭的故事》、《南京的基督》、《湖南的扇子》、《女體》,在這l2篇作品中,大多數取材于《聊齋志異》、《剪燈夜話》等。”
無論是西方材料還是東方材料,芥川龍之介都能駕馭自如,以其奇拔的方式表現出來,抒發其個人對于人生的感悟及藝術情懷,給予古典文學以現代意義。芥川龍之介涉足文壇之時,正是日本早期無產階級文學席卷全國,反自然主義文學蓬勃興起之時。小牧近江等人創辦的《播種人》雜志讓無產階級文學在日本切實地發展成為時人關注的焦點。《播種人》不同于以往的社會文學和勞動文學,明確提出反戰、反軍國主義的口號,旗幟鮮明地支持俄國十月革命。《播種人》是以文學為中心,具有高度思想性、觀念性和政治色彩的進步雜志。在這種文藝思潮的沖擊下,芥川龍之介以冷靜的旁觀者的眼光來審視各種文學觀,在對待無產階級文藝方面,他不象藝術至上者那樣完全否認文學的政治價值,他曾說過:“我在氣質上是一個浪漫主義者,在人生觀上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在政治上是一個共產主義者。”
1921年(日本大正十年)3月19日,芥川龍之介做為大阪每日新聞社的海外特派員從東京出發,開始了他四個多月的中國視察旅行,足跡遍及大半個中國,這也是他多年來夢寐以求的一個愿望。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初期的中國,正處于一種政治上被壓迫、軍事上被占領、經濟上被掠奪的境地,最下層勞動人民的生活更是處在水深火熱之中。中國當時面臨著非常嚴重的災難。芥川龍之介來中國時正是上海各界為反對北洋政府和帝國主義之間的勾結,舉行罷工、罷市、罷課運動之時。在這樣一種社會背景下芥川龍之介來中國的目的不能不說是政治高于藝術。
芥川龍之介可以說是和中國學者接觸較多的日本作家之一,他利用旅行之便去拜訪了一些當時著名的政治家、學者。在上海見了章太炎和李漢俊,在北京見了胡適等人。與章太炎等中國知識分子的見面,使芥川龍之介了解到他們對中國社會的憂慮和思考,這是芥川龍之介在日本時所不曾考慮過的,同時也對他日后的思想觀念帶來了很大的影響。這在作家后來所寫的隨筆《僻見》(1924年3月至9月)一文中就道出了對章太炎的崇敬之意:“我在上海的法國租界拜訪了章太炎先生,在懸掛著剝制的鱷魚皮的書房里,與先生探討中日關系。那時先生講述的話語,至今仍在我的耳邊縈繞。難以忘懷。——‘我最厭惡的日本人是討伐鬼之島的桃太郎。對于喜歡桃太郎的日本人,也不能不說有些反感。’先生的確是位圣賢之輩。我時常聽到外國人嘲笑山縣公爵,贊揚葛飾北齋,痛罵澀澤子爵,但是,還從來沒有聽到過任何日本通像章先生這樣一箭射向自桃而生的桃太郎。且先生此箭之真理勝于任何日本通的雄辯。”瑚章太炎一針見血地揭露了潛藏在日本民族血液中的侵略性,并指出自己對于日本的不滿情緒。正是這次談話芥川龍之介受到了章太炎言論的影響,后來創作了反戰小說《桃太郎》。二十年代的中國正是反日愛國情緒高漲之時,中國就象一頭沉睡多年的獅子,正處在一種黎明前的朦朧狀態中,舉國上下在血腥和硝煙的惡臭中混雜著民眾憤怒的吶喊。在這吶喊聲中芥川龍之介似乎感覺到日本知識分子和中國緊密相關的宿命。
二、二十年代的中國讓芥川龍之介走出夢境
在芥川龍之介的文學創作中短篇小說最為著名,其題材廣泛,內容新穎,語言簡練,寓意深刻,膾炙人口。《上海游記》(1921)、《將軍》(1922)、《桃太郎》(1924)、《河童》(1927)等作品是作者回日本后所寫的游記和短篇小說。作品都從側面反映出了當時芥川龍之介心中的中國印象。作者通過具有普遍性的典型人物和矛盾沖突,非常鮮明地反應了那個特定時代中國的社會現實,并提出了對戰爭的思考。在《上海游記》中芥川龍之介并沒有像很多中外作家那樣站出來慷慨陳詞地正面批判,而是回避了當時人們所目睹的那個沸沸揚揚、錯綜復雜的場面,他對二十年代貧困的中國和動亂中的上海沒有做任何正面的理論上的評論,而是從人和物人手,通過舊上海的風土人情和所見所聞細膩地再現了當時的情景。芥川龍之介很早就偏好超現實的、怪異的東西,同時具有重視形式和格式、拘泥于瑣碎小事的生活態度,這自然也對其作品風格形成有所影響。在文體上他吸收西方小說文學結構樣式,平衡了“自我”的“寫實”與“虛構”的“創作”之間的矛盾,開創了獨樹一幟的文學敘事形式。
由于芥川龍之介自幼就受到中國古典文學的影響,他想像中的中國是那么美好、到處充滿詩情畫意、鶯歌燕舞。可是當他一踏上中國這片土地,映人眼簾的卻是掠奪、欺壓、貧困、骯臟、落后……作者用一雙嚴厲的觀察家的眼睛審視著這個被歐化了的上海。他發現在這個列強主導的上海有很多矛盾之處。在大眾公園(現黃浦公園)的門口立著一塊看牌,上面寫著“中國人與狗不準入內”。在《上海游記》第十二章《西洋》中作者這樣寫到:“那個公園很有意思,外國人進去可以,中國人一個都不能進去。而且還叫‘大眾公園’命名真是妙極了這塊讓中國人悲憤萬分,飽受莫大污辱的牌子,在芥川看來難道就真是“妙極了”嗎?回答是否定的。在這里芥川龍之介并沒有像很多中外作家那樣站出來慷慨陳詞地進行正面批判,而是使用了這種辛辣、諷刺、詼諧的方法來激起當時對現實社會漠不關心、麻木不仁的中國老百姓的覺醒、憤怒和抗爭。
在《上海游記》第四章《第一瞥》(下)中作者這樣描寫到:“英國水兵連的大兵在舞廳門口因為喝醉酒而打落賣花老太婆的花籃,老太婆嘴里一邊叨咕著什么一邊撿著玫瑰花,就在這時水兵們用腳踐踏著那些散落在地上的玫瑰……我馬上站起身,我們的腳下也點點滴滴地踏著零亂的玫瑰,我向門口走去……”在這里作者首先把賣花老太婆遭到英國水兵欺辱的一個場景真實地展現在讀者的面前。英國水兵——象征歐洲人的群體,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在中國的土地上欺負一個中國老百姓,被他們打落在地上的美麗的玫瑰花——象征美好的東西,可以任意地他們被踐踏。隨之而來的還有東洋人……作者本人作為一個東洋人他并沒有掩飾或袒護自己的民族,而是通過具有普遍性的典型人物和矛盾沖突非常尖銳地指出了在那個特定時期中國的社會現狀,反映了中國當時社會所呈現的紛繁復雜的面貌。 據增田涉回憶,魯迅曾對他說過:“芥川龍之介寫的游記中講了很多中國的壞話,在中國評價很不好。但那是介紹者(翻譯者)的作法不當,本來是不該急切地介紹那些東西的。我想讓中國的青年更多讀芥川的作品,所以打算今后再譯一些。”拍魯迅這段話的意思是中國的青年并沒有真正地懂得芥川“壞話”的含義,他想通過自己的翻譯讓中國青年更多地了解芥川龍之介的寫作方法和思考問題的方式。
如果讀過芥川龍之介從中國旅行回到日本三年后所創作的短篇小說《桃太郎》(《寸、/尹——每日》1924年7月1日)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作者的意圖。桃太郎正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化身。關于這點,日本作家桑原三郎寫到:“芥川的《桃太郎》所隱喻的是橫行霸道的侵略者在鬼島上進行了非人道的燒、殺、掠、搶之后,鬼們奮起報復,使他們不得不生活在一種坐落不安、無法擺脫的地步。這個結果正說明了這是一篇象征著日本帝國主義末路的短篇小說。”
從以上作品中不難發現作者非常擅長利用過往的材料,再加以近代人的巧思妙想、合理地剖析、解釋現實和人生中存在的問題并給予現代意義。《桃太郎》、《將軍》、《河童》等作品可以說是芥川龍之介到中國旅行后的新思考,當然也不排除芥J7i龍之介當時受到無產階級思想影響的可能性。通過這次中國之旅,芥川龍之介改變了頭腦中對中國古典的印象,使他對中國有了一個全新的真實的認識。
三、芥川龍之介作品中的理性思考
“文學就是用語言來創造形象、典型和性格,用語言來反映現實事件,自然景象和思維過程。”芥川龍之介有著豐厚的歷史知識和深厚的古典文學素養。他一直追求用東、西方的文藝精神來營造自己獨特的藝術世界,并進而選擇了以歷史小說這一形式來實現自己的理想。其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部分是武士、平民、盜賊、乞丐,以及狐貍、天狗、鬼怪等等,作者以這種表現形式來追求精神的革命。如《羅生門》、《鼻子》、《芋粥》、《地獄變》、《莽從中》、《六個宮姬》等一系列小說,正像葉渭渠先生所說:“它們大多采用歷史上奇異的,超自然的事件,描寫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民眾,面對地獄般的現實,不斷復蘇野性的生命,頑強地掙扎著繼續生存所展現的野性美。”芥川龍之介是要借助歷史的舞臺來展示現代之事,這并非憧憬昔日之事,而是對現實和人生進行理性的揭露予以思考。用自身設定的主題并使之成為藝術化的手段,將不便直接講出的社會狀態或異常事件寫成小說,用以再現現實之事,將歷史事件寓意化,通過歷史人物、事件來表達自己的主觀思想。
每個作家的思想都具有時代的特質,并受個人境遇的制約。同樣每個作家的作品所表現的思想,也受到時代、階級和歷史的制約。芥川龍之介生活在一個不安定的時代之中,接觸到許多不合理的實際,自然地流露出對社會上利己主義的不滿、對資本主義的現實不滿,感到周圍的現實充滿不可調和的矛盾。作者一生都在研究“美與丑、善與惡”的矛盾,芥川龍之介認為只有文學才能包容人生的美與丑、善與惡的所有矛盾,也只有文學才能完成美,而且是永恒的美。芥川龍之介認為必須正視周圍的一切丑與惡,通過丑惡去理解善與美,理解了善與美才能更深刻地去理解丑與惡,這是一對不可分的矛盾體。也就是說,丑是美的本源,愈是理解丑,就愈能理解、追求美的存在的意義。
芥川龍之介深刻剖析人物的心理狀態,將下層人們的悲歡離合,通過其作品進行充分哲理化的藝術加工,再把生活中的現實折射出來,并注入新的生命,給今人以借鑒和反省。不過他雖然努力去尋找時代和社會的病根,但卻沒有力量去解決現實的丑惡問題,于是企圖調和現實與理想之問的距離,從現實中尋找理想的可能性,企圖從藝術中拂去不和諧的人生。他出于對資本主義體制、道德和現代社會種種束縛的不滿,因而對馬克思主義抱有一定的興趣。“他對于社會和人生采取一半肯定,一半否定的態度。可以說芥川的人生觀的核心思想是以中庸之道來統一的自由意志與宿命的矛盾。”這種矛盾從芥川的后期創作中可以發現,其創作思想上從對人生的解釋、批判、追求、不安轉為對人生、社會的不滿和憎惡以及對前途毀滅的意識。這也正是他對待人生的態度,導致最終無法自拔。
眾所周知,在文學創作中如果說技巧的運用還可以憑著藝術的靈感在短時間內能領略到,但是深刻的思想即作家的個性、氣質之類的東西,嚴格說是無法模仿的,即便是生活經歷等完全屬于后天所得,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必須要有某種精神,正是這種精神才能使人堅定意志,不斷去追求,從而在這大千世界中保持自我的獨立性。
四、結語
王富仁指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和文學家的杰出意義,不在于他提供了另一個偉大思想家或文學家所已經提供了為任何人所未曾提供的東西,而在于他具有為他人所不可逾越的獨立貢獻。”芥川龍之介是二十世紀日本乃至世界文學史上比較重要的作家之一,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文學創作上都顯示了巨大的生命力,這其中蘊藏著中國文學與文化的浸潤是不可忽視的。也正是在此基礎上奠定了他的文藝主張,并影響了他的文學創作。從芥川龍之介作品中不難發現作者取材遍及古代及近世的各個歷史時期,巧妙地用近代人的利己主義來解剖歷史上的人物心理,對人性賦予了新的解釋。他以熱情與冷酷的態度審視不同性格人物的人生軌跡,在其短短的十二年的創作生涯中,給后世留下了148篇小說,55篇小品文,66篇隨筆,以及大量的評論、游記、札記、詩歌等。芥川龍之介每篇作品的題材、內容和藝術構思都各有特色,這是他在創作過程中苦心孤詣地不斷進行藝術探索的結果;他的文筆典雅俏麗,技巧純熟,精深洗練,意趣盎然,別具一格,豐富了近代日本文學的歷史。為紀念芥川龍之介在文學上的成就,1935年由日本著名作家菊池寬創立了“芥川文學獎”,直至今天該獎一直是日本獎勵優秀青年作家的最高純文學獎。芥川龍之介為整個日本近現代文學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