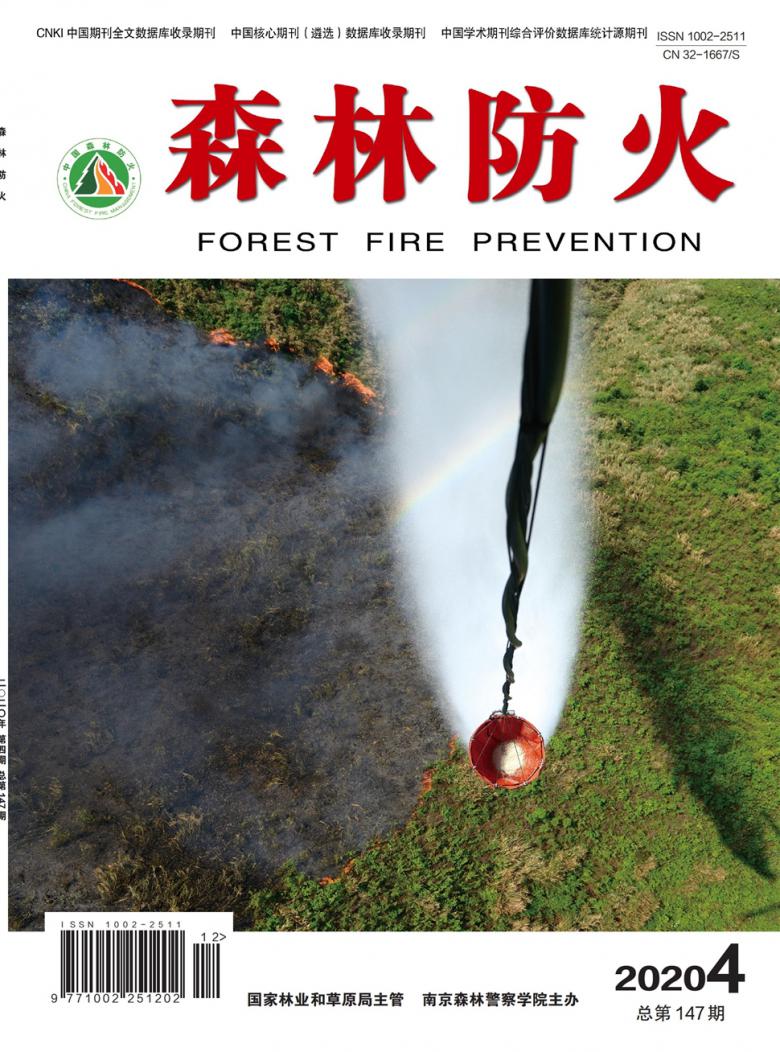1998—1999年文學各學科研究新書評介·《古典主義的終結》
關愛和
350年前,幾乎在八旗鐵騎厘定天下的司時,一個新的古文流派在安徽中部的一個山清水秀的偏遠小縣悄然崛起了。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桐城之名震于天下,桐城派古文也成為雄踞文壇的主流文派。它幾乎經歷了清王朝由亂而治,又由治而亂以至滅亡的全部過程,成為中國文學史上延續最久的一個散文流派,又是最后一個退出歷史舞臺的古典文學流派。當“五四”風暴席卷北京之后,桐城派的末代傳人又黯然返回桐城,使桐城派的發源之地戲劇性地最終成為這一流派的圓寂之處。
桐城派向以道統、文統自居,所以它不僅是一個散文流派,而且代表著程朱理學的文化祈向,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統治者的文化意志。在桐城派的幾乎與清王朝相始終的漫長發展進程中,蘊含著極其豐富的文化信息,潛藏著文學發展的豐厚底蘊。解讀這些信息,探尋這種底蘊,已經成為文化史學者和文學史學者的一項任務。
如果從1905年劉師培在《國粹學報》發表《文章源始》一文算起,桐城派研究已經走過了近百年的歷程。在近代文學的研究領域,桐城派古文一直是一個熱門話題,所謂“一文(桐城派古文)一詩(宋詩派)一社(南社)”,構筑起近代詩文研究的基本框架。但是,也許是因為近代文學研究還是一門比較年輕的學科,理論積淀還不夠豐厚,學術視野還不夠開闊,因此不少有關桐城派研究的成果,還停留在“就人論文”、“就文論文”的層面上,未能深入開掘桐城派的文化蘊含。現在,關愛和教授的《古典主義的終結——桐城派與“五四”新文學》(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一書彌補了這一學術缺憾。
脫出習慣的線性思維模式,在較深層次的歷史文化背景下分析桐城派的興衰衍變,將文學研究與文化闡釋結合起來,通過文學分析來解讀重要的歷史文化息息,是該書的一大特色,使這部學術專著在不乏精彩的同時,也擁有了堅實與凝重,代表了20世紀末桐城派研究的學術水平。該書的可貴之處,還在于作者似乎在不經意之間深入探討了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學術問題,例如,政治文化氛圍對文學流派形成的決定性作用,流派領袖人物的個人際遇和性格學養對該流派發展的主導性作用,文學與哲學之間的相互激蕩,等等,而這些問題又被此前的學者長期忽略,由此顯示了作者的敏銳縝密的學術洞察力和宏博豐厚的學養。
該書以桐城派標榜的“道統——文統”為中軸線,作縱向的學術展開。作者首先追溯了中國散文發展的歷史,認為韓愈、柳宗元的“文道合一,文以明道”的文道觀被北宋古文家所繼承,但朱熹等理學家卻輕詆韓、柳“裂道與文以為兩途”,主張“心統性情”,“文從道出”,以語錄體代替古文,導致了中唐以來思想與文學聯盟的破裂。明初,宋濂提倡“辭達而道明”,唐宋派重提文道并重與韓、歐傳統,主張古文家必須從“明道”中顯示出文章家的本色。清初,侯方域、魏禧、汪琬皆推崇韓、歐之學,批評理學家重道輕文,主張“匯文道源流而一”,在當時的文化氛圍下,遂成為古文一派的思想旗幟。而以道統、文統承繼者自認的,就是繼侯、魏、汪之后而崛起的桐城派。
在分析桐城派的源起時,作者認為,方苞“以古文義法用為制舉之文,以清真古雅為正途楷模,實際上是依古文家的宗尚在為科舉文確立一種寫作與評價的規范。當方苞有關以古文義法旁通于制舉之文的兩篇序言隨著《四書文選》、《古文約選》頒行天下時,已因它所具有的官方色彩,而在無形中大大擴展了方苞義法說的影響和覆蓋范圍”。所以,“義法說的植被地帶在古文,也在時文”。在這里,作者揭示了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即作為文學主流派的桐城古文所具有官方色彩,以及桐城古文與科舉文化的密切聯系。桐城古文之所以被譽為“文章正宗”而長盛不衰,與此大有關系。
在論述嘉道之際士風時,作者首先對明清兩代士風作出了比較,認為“明代之士言官爭競,清議講學,士風喧囂驕盛,不可一世。清代矯正明代弊端,以嚴厲之策治士,不許聚徒講學,不許清談議政,從而造成士風委靡,言路堵塞,慷慨忠義之士無所用其智慧,官場士林中則彌漫著茍且偷安、推諉因循、好諛嗜利的風氣”。作者進一步分析道,正是由于嘉道之際的變局和政府控馭力的減弱,才激活了姚門弟子被壓抑已久的政治熱情,使他們熱心于立德、立功、立言的話題,而姚門弟子對程朱義理之學的虔誠信賴,也有更加切實豐富的內涵。 作者認為,桐城派傳人特別強調道統、文統的承傳接續,注意編制傳承系統,極力維護桐城派古文的嫡傳地位與師道尊嚴,不失時機地推出新的領袖與傳人。作者寫道:“濃烈的道統、文統意識,是桐城派發展過程中的精神信仰支柱及向心力、凝聚力的所在。它使散在的作家個體,在準宗教化情緒的支配下,以準宗法制衣缽傳承的關系而結盟。這無疑是桐城派二百余年經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桐城派關于道統、文統的闡釋與論述,成為桐城派古文理論中極富個性特征的組成部分。”作者同時又指出,桐城派托道統、文統而自尊,表現出黨同伐異的宗派情緒,劃地為牢,自我封閉,形成了虛幻色彩極濃的“統系理想主義”,從而逐漸失去了理論創新的銳氣,也壓抑了作家的創作個性。至曾國藩出,主“堅車行遠”之說,于古文之學孜孜以求,“擴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于一途”,始有桐城派之中興。
關于桐城派的生存與發展,作者提出了兩個空間的觀點,認為桐城派文人設定了兩個生存空間,一個是社會空間,即桐城派以道統、文統的傳人自居,以藝術之文的作者自任,以力延古文一線作為歷史使命。這種必然而自覺的集體行為,又營造出第二個空間——藝術空間。桐城派通過對古代散文的理論成果、閱讀體悟及創作經驗的總結,形成了獨具特色、風格鮮明的古文理論體系,從而別開之境,卓然不群。
對于中興桐城派的領袖人物曾國藩,作者用功頗深,不乏精彩之處。作者認為,曾國藩是一個處在傳統與現實的夾縫之中,充滿極大思想矛盾和人格分裂的復雜人物。特殊的政治際遇,把他推上了中興名臣的地位;他又憑此煊赫的政治地位,著意強化文事辭章的社會功能,在桐城派趨于山窮水盡之時,援之以手,對桐城派予以改造,將桐城派納入其中興大業之中。曾氏的審美情趣和審美識度,是桐城派中興的基礎。他對雄奇瑰瑋風格的崇尚,他于義理、辭章、考據之外又特別標出經濟,為桐城派古文開辟了更為廣闊的天地。曾國藩主張以文見道,堅車行遠,重在講求經世要務,記敘當代掌故,鋪敘文治武功,重義而不輕詆于法,求雅而不拘泥不潔,取方姚之流暢而去其柔弱,輔以漢賦之氣體而脫其板重,義必相浦,氣不孤伸,詞必己出,簡要有序,以政治家、經世家之文取代文學家之文,由此形成了湘鄉派。
作者認為,曾氏之文,“較為全面地體現出宏大卓然的氣質和舉重若輕的才力”,最具代表性的當推《圣哲畫像記》。作者對比文有精彩的點評:曾氏“在對32賢哲心儀柱香、頂禮膜拜中,傳達出紛亂之世士儒階層文能坐而論道,武能決勝千里,從政能馭將率民,閑逸則登高能賦的人生理想,及承先啟后、全面繼承學術文化傳統的精神面貌。文中所貫穿始終的‘沙場秋點兵’的豪俠氣魄,既有書生意氣的成分,也有舍我其誰的底蘊,令讀者心馳神往”。而曾文的‘斂退氣象”,則體現在《歐陽生文集序》諸文中。與姚鼐、梅曾亮相比,曾國藩氣度過之而精微不及,但立言謹慎,措語熨貼,卻是一脈相承。但是,作者同時也指出,曾氏生古文理論上的改革倡導之功,遠遠大于他的創作實踐。
關于桐城派消亡的原因,除了桐城派自身藝術創造力的衰竭之外,作者特別強調了歷史文化因素,認為作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桐城派依附于封建政治之上,而封建政治的垮臺,使桐城派挾道統、文統自重的優勢轟然坍塌;桐城派古文自方苞起,便與科舉制有不解之緣,士人緣桐城義法而敲開仕途之門,但科舉制的廢除,使得桐城古文失去了往日功利性的誘惑;桐城派古文的盛行,與一直受到清政府的保護、提倡有關,一旦清朝滅亡,失去這種官方支持,桐城派必然要陷于窮途末路。相反地,白話文由于得到國民的認同,1920年又被北洋政府教育部頒布為法定國語,其優勢地位才得以鞏固。
當然,這部著作也給人留下了些許遺憾。從體例上看,該書的所有古籍引文都未能注明卷數,正文之后也未附主要參考文獻目錄;從全書篇章設計來看,第一章為桐城派的總論,第二、三章分別論述桐城派的古文理論及古文創作,第四章論述后期桐城派與“五四”新文學,從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匠心,其思路可謂清晰,但在具體論述時,第一、二、三章的內容偶有互相重復之處;從論證上看,曾國藩崛起與桐城派中興,除了其他因素以外,似與湘鄉的歷史人文環境及湖南理學集團有關,惜作者于此著力不多;從行文上看,出現了個別筆誤,如第357頁:“咸豐元年,已入垂暮之境的曾國藩……”。“咸豐”顯然為“同治”之誤,因為咸豐元年時,曾國藩才40歲,正當英壯之時,在北京擔任禮部右侍郎,兼署刑部左侍郎,而同治元年時曾國藩已51歲,十年后下世。所以,如果再稍加磨礪,這部學術著作也許會更加精潔完美。然而,小瑕不掩大美,《古典主義的終結》仍然不失為近年來近代文學研究領域里少見的一部力作。它是作者近20年來潛心于桐城派研究的學術結晶,展示了比較獨特的學術風格,擁有精醇的學術品位,與那些心浮氣躁、急功近利的學術復制品有質的不同。就桐城派而言,《古典主義的終結》一書可以說為20世紀的研究劃上了句號,也為21世紀的研究奠定了新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