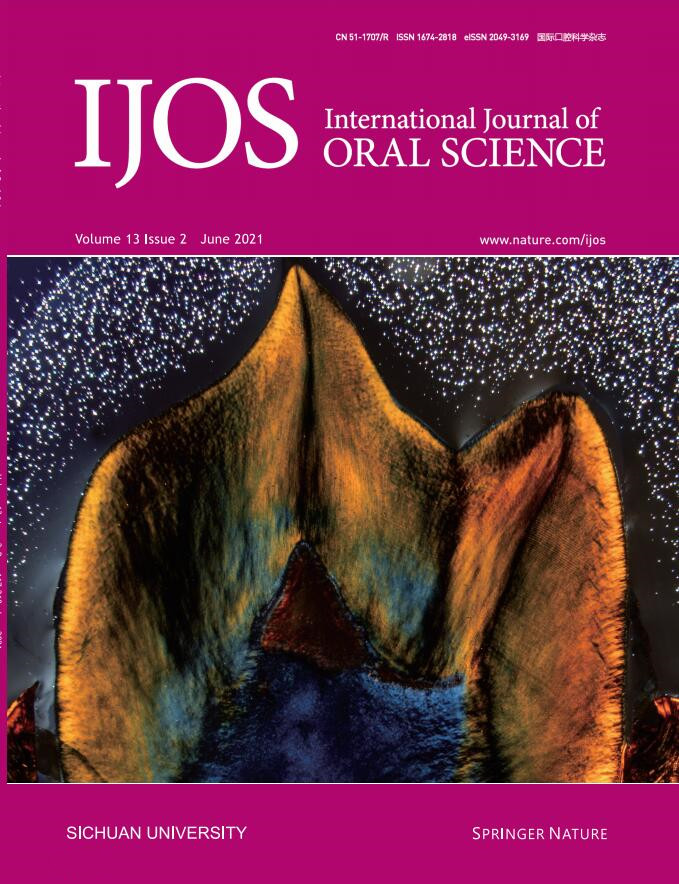第七章 藝術與技術――網絡文學創作嬗變
歐陽友權等
一般來說,舊的觀念已經取得了悅人的文字外衣,而新的觀念看上去依然表述笨拙。因而喜好優美的文字形式的審美偏好多半是與保守性聯系在一起的。……由于這種情況,那些固執優雅文字形式的人就不能不落在--經常是遠遠地落在--他們時代的最先進的思想的后面。反過來,保守的人相對于創新者在審美上則處于更有利的地位,因為隨著觀念變得陳舊,它們的形式卻變得越來越優美。
--麥卡利斯特《美與科學革命》
從藝術發展史來看, 20世紀以來是藝術形式演變最迅捷的時期,其首要因素是電子傳播技術給藝術帶來的巨大影響。從1895年法國人盧米埃爾兄弟發明電影,到1906年德國作曲家亨德爾的作品被美國費森登實驗電臺以無線電波的形式發送,再到1930年意大利作家皮蘭德婁的獨幕劇《口叼鮮花的人》由英國BBC公司作為電視信號播放,直至1959年美國伊利諾斯大學的科技人員開始利用電腦創作音樂,以及今天互聯網上五花八門、異彩紛呈的網絡藝術,媒體的革命,特別是電子媒體的一次次嬗變,一直引領著人類藝術發展的歷史潮流。
麥克盧漢說:“每一種技術都是我們最深層的心理經驗的反射”;“如今,我們開始意識到,新媒介不僅是機械性的小玩意,為我們創造了幻覺的世界:它們還是新的語言,具有嶄新而獨特的表現力量。”①在人類歷史上,還從沒出現過比互聯網更大的機器,比互聯網更大的圖書館,比互聯網引擎更為便利的檢索工具;也從沒什么媒體能比互聯網更為精細、準確、迅速地輻射出自己的社會影響。對于文學來說,一方面,有文字以來歷史上的出版“門檻”從來沒有像網絡時代這樣低,“人人都可成為作家”的前景也從來沒有像網絡時代這樣具備現實的可能性。
網絡文學的創作淵源,理論上可以追溯到羅蘭·巴特的“可寫性”文本,德里達的“互文性”;實踐上可以追溯到被稱為“超文本之父”的尼爾森。這位哈佛大學的藝術碩士、嚴重的“注意力不集中”患者,他想以超文本為基礎把電腦變成一部碩大無朋的“文學機器”,把全人類的創作聯結成一個數碼圖書館,將人類已有的藝術信息資源集成化。尼爾森為此努力了30年而沒有成功。然而他的研究卻啟發了萬維網(WWW)的構想(1989)。當網絡時代悄然來臨時,尼爾森所鑄造的“超文本”、“超媒體”不僅成為現實,而且成了后人研究網絡文學無可回避的范疇。如果說網絡文學在20世紀60年代還僅僅是尼爾森腦海中思想火花閃現的話,那么,隨著互聯網的無限延伸,今天,網絡文學已是幼苗初成。
一、電子化技術手段
1、換筆與換腦
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的根本差異在于兩者信息媒體的不同:前者屬于比特形態 ,后者屬于原子形態。信息媒體由電子化的比特取代傳統的原子形態,是社會的一場重大變革。比特具有完全不同于原子的性質:它沒有顏色、尺寸或重量;能以光速傳播,是信息的最小單位,是一種存在的狀態,是數字化計算中的基本粒子。比特可無限復制,而不會有任何改變,也不會丟棄任何信息。它像一種新的“DNA”突變基因,正迅速取代原子而成為社會發展的基本內核,并衍生出全新的觀念和社會。
網絡文學創作模式的變異表現在創作手段方面,網絡作者以機換筆,讓苦役般的“碼字兒”變成輕松的鍵盤輸入,也可以運用萬通筆或無線壓感筆手寫輸入,或是在交互式語音平臺上進行語音輸入。在語言操作上,電腦寫作使用的是以二進制 (即一連串的“0”和“1”)為代碼指令的機器語言和將字母縮寫成符號指令的匯編語言,還有通過編譯程序與計算機相連的高級語言,這就為電腦程序創作提供了機遇。有的操作軟件還能夠實現隨機創新、人機共同創作。
南朝梁·鐘嶸《詩品·齊光祿江淹》有這樣一故事:“初,淹罷宣城郡,遂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我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后為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1]此故事似乎在暗示:筆是文才的代稱。的確,書寫時代,筆是文藝家們的人格寄托。以筆為基礎的許多詞匯如筆力、筆法、筆調、筆鋒等是藝術的重要范疇,筆力萬鈞、如椽巨筆是對文人才華的贊美。然而,這歷時千年的書寫觀念,在電腦出現以后將被歷史輕輕翻過。“換筆”(以機代筆)已成為數字化時代文潮涌動的歷史洪流。
1975年,葉永烈編導了電影《電子計算機》,這是中國最早介紹計算機的科普電影。1978年7月20日出版的《參考消息》,以第四版整版篇幅譯載了美國《時代》周刊中的兩篇文章:《神奇的小硅片時代――新微型技術將改變整個社會》和《萬能鈕式生活――電子計算機革命使我們生活得更聰明、更健康、更美好》。其中有關書寫革命的部分作者寫道:早上醒來后,“在床上把他今天要辦的公事和私事口述給微型電子計算機,今天要寫的通知、備忘錄馬上就在電視屏幕上顯示出來。”這兩篇文章首次向中國人傳播了用電子計算機作為寫作工具的信息。80年代初,我國從事計算機信息研究的科學工作者和科普作家率先“換筆”。《中文信息的計算機處理》的作者們說,他們在1982年5月至8月完成了System C中文信息綜合處理系統以后,曾用這一系統非正式出版了幾本介紹該系統設計思想的論文集。“這些論文都是我們坐在計算機終端屏幕前,邊思考,邊鍵入,現編現改,由計算機進行自動排版,自動分頁,自動產生表格,最后打印輸出,裝訂成冊的。”1983年,他們實現了“從寫作、改稿、審校、發稿、編輯、排版、插圖、制版直到印刷,這樣一本書誕生的全過程都完全采用了中文計算機系統來進行中文信息的計算機自動處理。”1992年重慶出版社出版了陸宗周的《怎樣用電腦寫文章》,1995年上海文匯出版社出版了葉永烈的《電腦趣話》,其中他頗為得意的寫道:“從此,我在寫作時不再低頭,而是抬起了頭,十個指尖在鍵盤上飛舞,就像鋼琴家瀟灑地彈著鋼琴。我的文思在噼噼啪啪聲中,凝固在屏幕上,凝固在軟盤里。”至此,國內一批思想較為開通、較易接受新事物的作家相繼實現了“換筆”。王蒙說:“作家用了電腦,真是如虎添翼。我驚異地發現,那些抨擊電腦的振振有詞的道理,大致都是不用、不會用、不想學或者沒有電腦甚至壓根兒就沒有接觸過電腦的先生女士們講出來的――也就是臆造出來的。” [2]此后,換筆已成大勢所趨,用筆寫作的文學陣營在日漸萎縮。
文明的變異往往從最基本的工具開始。石器文明到銅器文明再到鐵器文明,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再到今天的信息文明都是明證。傳播媒體的遞變是文化突飛猛進的直接動因。竹簡木牘取代甲骨銘文使中國文化前進了一大步;紙、筆的出現催生中國文化再次躍遷;紙和活字印刷是歐洲文藝復興的傳播基礎。歐美使用打字機很長時間以后,我們還一直在使用老祖宗發明的毛筆,這與中國文化更新緩慢、社會發展相對滯后不無關系。今天,書寫方式再次發生巨變:筆、墨、紙等工具被鍵盤、鼠標以及諸如拼音、五筆、王碼、微軟等書寫軟件所代替。毋庸置疑,文化的巨變已在眉睫。因為換筆的意義不僅是書寫方式的改變,更標志著創作觀念的變化和主體能力的新飛躍。
況且,今日的網絡創作已非簡單的換筆所能涵蓋,網絡這一碩大無朋的媒介可能或將要包含和包孕人類所有的文化。寫作從最初的資料積累、構思動筆、反復修改,到最后的出版發行等整個過程都已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鮑德里亞認為,現今的符號制作規模已經足以讓歷史發生一次斷裂:以工業生產組織為核心的社會開始向符號社會回歸。社會的凝聚力不是源于經濟生活,而是來自傳播媒介的控制。于是,在他看來,革命不再是活躍的生產力摧毀傳統的生產關系;顛覆種族或性別的傳統符號代碼才是他真正醉心的文化革命。[3]正如我國學者所言:“傳播媒介與文化類型之間的歷史呼應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麥克盧漢認為,石頭是穿越縱向的時間、黏合許多時代的媒介,紙張卻傾向于聯結橫向的空間,建立政治帝國或娛樂帝國。的確,新舊石器時代與青銅時代的文化風格不得不追溯至傳播媒介的性質與構造。結繩記事不可能產生微積分,長篇小說不會銘寫于甲骨或者竹簡之上,機械復制技術的成熟徹底滌除了藝術周圍神秘的崇拜氣氛,互聯網對于傳統的作者等概念提出了重大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