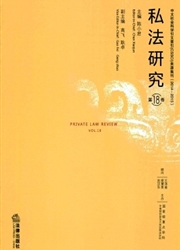三十年短篇小說藝術創作軌跡回顧
王干
1978年全國舉行第一次短篇小說評獎,我能清楚地記得那一次短篇小說得獎篇目是25篇。后來再一問,很多人都和我一樣,不僅記得得獎的篇數,還能說出大部分的篇目。如今,30年過去了,短篇小說創作經歷了風風雨雨,在發展中變化,在迷惘中追求,在起伏中成長。
“戰斗”的文體為思想解放吶喊 新時期文學孕育于1976年的天安門詩歌運動,興起于短篇小說創作。這一時期曾被一些文學史家稱之為“傷痕文學”時期,而“傷痕文學”的命名,則緣于盧新華的短篇小說《傷痕》。這篇當年發表在《文匯報》1978年8月11日的短篇小說,在今天看來,更像一篇中學生的習作,然而在當時資訊和文學都處于一個比較封閉的閱讀環境里,尤其在思想解放初期,《傷痕》一紙風行,成為全社會的關注焦點,也成為文學界爭論的熱點。雖然在《傷痕》之前,劉心武已經發表了后來成為新時期文學代表作之一的《班主任》,但由于《班主任》思想的潛藏性和人物的復雜性,并沒有引起大眾的閱讀熱情,而《傷痕》采用的親情結構和思想的淺表外露(批判時人皆痛斥的低級的血統論),迅速觸動了全民的共鳴。 圍繞《傷痕》的爭論,一時間出現了大量批判“四人幫”極左路線的小說,像張潔的《從森林里來的孩子》、陸文夫的《獻身》、王亞平的《神圣的使命》、成一的《頂凌下種》、李陀的《愿你聽到這支歌》、肖平的《墓場與鮮花》、陳世旭《小鎮上的將軍》、張抗抗的《夏》、高曉聲的《李順大造屋》、茹志鵑的《剪輯錯了的故事》、陳國凱的《我該怎么辦》、張弦的《記憶》、古華的《爬滿青藤的木屋》、方之的《內奸》、金河的《重逢》等都加入了這樣以控訴和揭露為主題的寫作。 很顯然,這是對“五四”以來魯迅文學批判精神的繼承,尤其劉心武在《班主任》結尾處直露的“救救孩子”的呼喊,更是證明新文學運動的精神在新一代作家身上“靈魂附體”。和魯迅不一樣的是,改革開放初期作家的文學觀念似乎更接近魯迅思想的繼承者胡風的“主觀戰斗精神”。 和“傷痕文學”、“反思文學”齊頭并進的是“改革小說”的出現。從一些資料看,一些人對改革文學是持有異議的,因為他們覺得傷痕還沒揭露透,對歷史的反思剛剛開始,怎么就去歌功頌德呢?現在看來,當時的改革文學其實并沒有真正影響到“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的發展,其對現實生活的描寫和介入,更是對其“戰斗”精神的延伸。就理論而言,作家的主觀戰斗精神其實也包括對現實生活的“把捉力、擁抱力、突擊力”(胡風語),作家既可以在歷史的滄桑里找到靈感,而對現實的“把捉”和“突擊”也是不可或缺的能力。雖然在今天看來,用短篇小說這樣的文體去正面“突擊”改革這樣的宏大主題有些勉為其難,但呼吁并介入改革的實踐卻很有必要。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用現在的文體觀來審視,顯然不是短篇小說,甚至不是中篇小說,如果出單行本該屬于長篇小說。然而當時不僅作為短篇小說發了,而且還被評為當年優秀短篇小說獎的頭榜。可見人們當時對短篇小說的要求,不是文體,而是內容。或者這樣說,在一個改革的年代,小說所承載的使命已經超越了文體的局限,《喬廠長上任記》真正做到了文以載道。 和蔣子龍直面切近改革過程不同的是,一些作家則使用了一些更具備短篇小說方式的敘事策略來面對現實。王蒙的《說客盈門》可以說是《喬廠長上任記》的“前傳”,而《喬廠長上任記》更像《說客盈門》的升級版。王蒙后來的《悠悠寸草心》明顯降調了,寫了改革的艱難和復雜。而鐵凝的《哦,香雪》則通過農村小姑娘的眼睛,寫出農民對變革的渴望和呼喚。趙本夫的《賣驢》在今天看來似乎有些黑色幽默的意味,賣驢的孫三老漢和香雪形成了巨大的對比。李國文在寫作長篇《花園街九號》的同時,通過短篇小說“危樓系列”對處于新舊時代的人的心態作了深刻的揭示。 雖然把這一階段的短篇小說創作比作魯迅說的“投槍”、“匕首”有些夸大其詞,但在一個文學要清算過去的思想障礙、要呼喚很多價值回歸同時又要革新、創新的年代,短篇小說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可以說在意識形態功能方面發揮了最大值,是短篇小說最輝煌的政治時代。歷史會記載這些作家行進的足跡。
旋轉的實驗發散著個性的斑斕 新時期文學,是一個吶喊呼嘯的啟蒙年代,也是一個藝術自覺和文體意識不斷強化的文本年代。隨著小說思想的不斷更新,小說家的文體意識也漸漸復蘇。短篇小說的文本自覺和藝術自覺首先體現在與中篇小說的剝離。新時期之初的短篇小說,容量普遍偏大,動輒幾萬字,《喬廠長上任記》甚至有11萬之多。80年代以后,隨著一些大型文學刊物的創刊,《當代》《十月》《鐘山》《花城》等以及《收獲》的復刊,中篇小說的概念得到了強化,短篇小說的文體也慢慢走向強化和獨立,由此誘發的小說實驗浪潮催生出對小說觀念的變革和改進,迸發出令人炫目的光彩。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短篇小說的藝術個性得到充分的張揚,作家的主體意識最大程度地得到彰顯。 a、探索短篇小說的底線。短篇小說是一個相對古老的文體,古今中外都出現了優秀的經典作家,新時期的作家在向這些大家致敬的同時,還必須超越與創新。另一個方面,當時在閉關鎖國之后的突然開放,西方文學思潮也刺激了作家的實驗熱情。王蒙那批被冠之為“意識流”的《夜的眼》《春之聲》《海的夢》一批短篇小說,以及由此引發的關于現代派的討論,在今天看來還是應視作小說文體的實驗。張承志的《綠夜》《大坂》、韓少功的《歸去來》、馬原的《岡底斯誘惑》以及后來的格非的《青黃》、孫甘露的《訪問夢境》都在嘗試短篇小說的多種可能性,極大可能地豐富這一文體的內涵。當然,這一時期整體的追求還是努力實現小說的詩化和寓言化,在部分作家那里,短篇小說成了象征主義的實驗田。 b、色彩絢爛亂花迷人。“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白居易的詩本來是用來形容西湖邊上春天的美好景物,但用來形容1985年以后的短篇小說的創作形態也是非常形象的。在經歷了80年代的小說觀念的革命之后,隨著西方文學思潮的退潮,短篇小說進入了創作的自由境地。這個自由境地,是指作家不再大呼隆地跟隨某種思潮,而是從自身的生活經歷和藝術品性出發,書寫自己熟悉的、喜歡的作品。這時候,我們既讀到了劉恒的《狗日的糧食》、阿成的《趙一曼女士》、陳世旭的《鎮長之死》,也有余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魯羊的《銀色老虎》、朱文的《傍晚光線下的一百二十個人物》。既讀到男性作家莫言的《拇指銬》、韓東的《前面的老太婆》、趙本夫的《天下無賊》,也讀到女性作家徐坤的《廣場》、陳染的《饑餓的口袋》、林白的《子彈穿過蘋果》;既有邱華棟的“時尚人系列”,也有劉慶邦的鄉村礦井系列。多種風格,多種寫法,各具特色,各呈意蘊。 c、短篇小說名家輩出。對一般作家來說,短篇小說往往是一個作家初期寫作的一個臺階,一種歷練,也是這個作家邁向更大境界的起跳板。因而很少有作家慘淡經營這樣一種文體執著而不棄的,因為靠短篇小說躋身大家行列的實在太少。孫犁是現代文學史上的名家,他在新時期主要創作短篇小說“云齋”系列,引人注目。如果說孫犁尚有《荷花淀》等作品奠基的話,那么汪曾祺、林斤瀾這兩個作家恰恰是靠短篇小說在文學史留下印記的。年輕一代也出現了劉慶邦、蘇童兩個短篇高手。有趣的是兩人一北一南,小說一土一洋,但對短篇小說的執著,卻有目共睹,且成績斐然。蘇童的《桑園留念》《傷心的舞蹈》系列和劉慶邦的《盲井》系列以其鮮明的個性和不能替代的藝術秉性讓人難以忽略。
成熟的尷尬與憂思 從短篇小說這三十年藝術風格可以看出,短篇小說在最初的十年(1978—1988年)藝術上顯得比較粗獷的時候發揮著巨大社會作用,尤其在前五年,對讀者的影響更為明顯。但后來隨著整個文學的發展變化,短篇小說慢慢地處于一種邊緣狀態,淡出了人們的閱讀視野。想靠一篇短篇或幾個短篇一鳴驚人的作家幾乎不可能出現了,曾經延續多年的短篇—中篇—長篇的小說進步模式被網絡文學徹底顛覆,很多寫作者一出手就是幾十萬字的長篇,而且效果不見得比那些循著三步走(由短而中再長)的作家差。再一個就是那些年富力強的作家,也幾乎放棄了短篇小說的寫作。就處理素材的方式而言,作家也格外地吝嗇,當初是中篇壓縮成短篇,長篇壓縮成中篇,而如今正好相反,很多中篇被注水成長篇,很多可以在短篇內解決的非拖拉成中篇。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當初把《喬廠長上任記》當作短篇發的《人民文學》雜志,如今時不時地也出個長篇專號了,可見短篇小說成了沒人疼的孩子。 讀者閱讀短篇的興趣銳減,是因為其他載體部分地取代著短篇小說的功能,短篇小說在審美上的獨特性日見其少。在短篇當中最受歡迎的帶有歐·亨利式結尾的故事化短篇,如今已經濃縮或簡化為小小說或微型小說了。小小說在現代社會里作為快餐閱讀,它成了短篇小說的殺手。小小說是從短篇小說家族派生出來的寵兒,本身的寫作就是高度汲取了短篇小說的精華,在一個高度簡捷化和濃縮化的網絡時代,一本《小小說選刊》的發行量幾乎是所有文學類月刊(不含大型文學刊物)發行量的總和,正是短篇小說的尷尬處境的如實寫照。 就小說藝術而言,毋庸置疑,短篇小說在經歷諸多的探索和實踐之后,漸漸回歸到短篇小說的出發點。這是一次回旋式的上升,說明短篇小說今天已經趨向成熟。但是在成熟的背后,也意味著某種停滯和衰退。遲子建是一個具有風格特點的作家,她寫作的短篇小說清新秀雅,很符合短篇小說的規范,而且保持穩定的藝術質量,因而她連續兩次獲得魯迅文學獎的短篇小說獎,對她個人來說,是件值得高興的事情,但對整個短篇小說創作來說,卻有一種淡淡的悲哀,說明短篇小說創作藝術不自覺地陷入了某種停滯。 這些年一直經營短篇寫作的王祥夫意識到這種困惑,他說:“短篇小說在寫作上讓作家感到尷尬的是,你寫了一個短篇小說,又寫了一個短篇小說;你寫了10個短篇小說,跟著又寫了10個短篇小說,問題就來了:看一看自己的短篇小說,你有種感覺,就仿佛自己站在波斯菊的花圃旁,你會發現所有的波斯菊花朵都是那個樣子!讓你感到不安的是,你所寫的短篇小說在寫作手法上竟然差不多!……短篇小說今天的不景氣,作家‘難辭其咎’,但短篇小說這種形式太難把握了,你把一種結構方法把握得純熟了,也就說你已經‘死亡’了,你要再生,必須再把握新的方法。一句話,我同意你的說法:短篇小說無論是思想還是藝術,對作家的要求都很高。所以,這就要求作家一次次潛到深水里去,你感到快要憋死了,你也許才會發現有一個珍珠蚌在你的眼前。”(《把短篇小說的寫作進行到底》,刊于2006年《山西日報》)。王祥夫用潛水和珍珠蚌的關系來說明短篇小說空間探索的艱難,可謂坦誠之言。 短篇小說還有多少新的空間可以開拓?這些空間在哪?如何尋找?如何開拓?是放在文學界面前的一大考題。雖然早就有人提出短篇小說已死的命題(趙毅衡《短篇小說正在死亡嗎?》, 刊于《南方周末》2007年1月25日),但似乎并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注意。果實成熟之后是衰亡,但來春還會萌芽、開花、結果,問題是我們怎么才能迎來這個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