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tǒng)禮制對現(xiàn)代中國法治的啟示——“禮”的法倫理學(xué)視角解讀
屈振輝
關(guān)鍵詞: 傳統(tǒng)禮制/現(xiàn)代法治/中華文化/本土資源/法倫理學(xué)
內(nèi)容提要: 禮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和精髓,體現(xiàn)在中華文化的各個方面,這自然也包括法律文化領(lǐng)域。中華法律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帶有“禮”的濃厚色彩,禮也成為中國法的本土資源。中國在近代后逐步邁向法治,在現(xiàn)代更步入了法治快車道。然而法治畢竟有其本土資源,我們在進行現(xiàn)代法治建設(shè)時,仍可從傳統(tǒng)禮制中獲得啟示。本文主要以法倫理學(xué)為視角,重新解讀審視傳統(tǒng)德法關(guān)系,并闡發(fā)其對現(xiàn)代法治的啟示。 禮制是中國法制史研究中的重要命題,研究中國法制的演進不能不提及禮制。正是“禮與法的相互滲透與結(jié)合,又構(gòu)成了中華法系最本質(zhì)的特征和特有的中華法文化。”[1]“禮”最初是原始社會祭神祈福的宗教儀式,在階級出現(xiàn)后才逐步蛻變?yōu)閺娭菩缘姆梢?guī)范。這意味著它不僅是中國法的起源,而且還影響著中國法發(fā)展的歷程。“從總體來說,整個中國古代法制歷史始終受禮制的支配和影響,一部中國古代法制史實是禮法合治的歷史。這是中華法系的一個重要特點。”[2]“禮”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無疑具有重要的地位,它甚至成為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內(nèi)容和精髓”。[3]中國自古就是崇尚德治卻缺乏法治的國度,道德對中國法治發(fā)展始終有著重要的影響。“中國的法治之路必須注重利用中國本土的資源,注重中國法律文化的傳統(tǒng)和實際。”[4]道德作為影響中國法發(fā)展的本土資源,主要是借助“禮”這種形式來實現(xiàn)的。盡管人們現(xiàn)在對“禮”的本質(zhì)尚還有爭論,但大多數(shù)人都認為“禮”與道德密切相關(guān)。“禮確實是反映社會道德關(guān)系的基本規(guī)范。”[5]在倫理政治化和政治倫理化的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與其說是“禮”在支配和影響中國法制的發(fā)展進程,倒不如說是潛藏在“禮”之后的道德在發(fā)揮著作用。中國歷史上從先秦到清末兩千多年的禮法之爭,實際上就是對道德與法律之間孰主孰輔的爭論,當然在這個時期內(nèi)始終是道德占據(jù)著統(tǒng)治地位。《唐律疏議》中“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的論斷就是最好的詮釋。中國從上世紀初就開始了逐步邁向法治的進程,特別是在進入現(xiàn)、當代以后這個進程迅速加快。在依法治國、建設(shè)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進程中,應(yīng)從中國法治的本土資源中尋找積極有益因素,而中國傳統(tǒng)禮制則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nèi)容。由于“禮”是反映社會道德關(guān)系最基本的規(guī)范,在發(fā)掘中國傳統(tǒng)禮制對現(xiàn)代中國法治的啟示中,作為倫理學(xué)與法學(xué)的交叉融合產(chǎn)物的法倫理學(xué),必將成為進行這方面研究最重要的路徑、方法。“法律倫理學(xué)研究對于正確評價中國傳統(tǒng)法律文化具有深刻的認識價值。”[6]它將成為對現(xiàn)代中國法治啟示研究的理論起點。本文以中國歷史上有關(guān)禮法關(guān)系的論斷為導(dǎo)引,以法倫理學(xué)的語境解讀其在現(xiàn)代法治中的涵義,以期能為現(xiàn)代中國法治建設(shè)提供某些有益啟示。
具體而言,中國傳統(tǒng)禮制對現(xiàn)代中國法治的啟示主要可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 一、“出禮入法”:合理區(qū)分道德與法律的界線 盡管人們在中外法律學(xué)說史上對法的起源問題,曾有過神意論、理性論、權(quán)力論等不同的認識,[7]但“刑起于兵”以及“法源于禮”這兩個觀點,現(xiàn)在已幾乎成為了有關(guān)中國法起源問題的通論。假如我們將“禮”的本質(zhì)歸入道德規(guī)范的范疇,那么“法源于禮”的實質(zhì)就是法律起源于道德。“法的發(fā)展可以邏輯地劃分為三大階段:首先是法律與宗教、道德渾然一體,此為‘混沌法’;其次是法律走出宗教、但仍與道德不分,故乃‘道德法’;最后是法律進一步與道德分離而獨立化,便是‘獨立法’。”[8]其中,“道德法”階段無疑占據(jù)了中國法發(fā)展歷程的主流,“獨立法”的形成則直到清末修律之后才真正開始。道德與法律的界線不清是中國古代法律的特點,“在中國古代,也有模糊道德與法律的界線,或者說以德代法的傾向。”[9]這種傳統(tǒng)對現(xiàn)代中國社會仍有著比較大的影響。但這種道德與法律界線不清的狀況也并非絕對,中國古代“出禮入法”的論斷就是最好的例證。“所謂‘出禮入法’似乎就是指違犯了‘禮’,嚴重的就要受到刑罰的制裁。”[10]有學(xué)者甚至還認為“禮”與“刑”結(jié)合在一起,以禮為體,以刑為用,出禮入法或出禮入刑,是中國封建時代法律體系的另一特征。[11]若將“禮”視為反映社會道德關(guān)系的基本規(guī)范,則我們似乎可以這樣詮釋“出禮入法”的論斷:即人們逾越了道德的界限必將受到法律的懲戒,道德與法律間必須有涇渭分明而且合理的界線。這對現(xiàn)代中國法治具有著非常重要的啟示意義。現(xiàn)代化的法治在今天的中國雖然已經(jīng)初現(xiàn)雛形,但由于歷史上“道德法”傳統(tǒng)強烈影響的存在,在很多地方仍無法合理區(qū)分道德與法律的界線,這也成為導(dǎo)致中國法治現(xiàn)代化進程緩慢的原因。且不論中國古代在這個問題上的實際狀況如何,但至少古人們在認識上早已明晰二者間的界線。中國古代至東周前雖仍保持著德法未分的狀態(tài),但德法分離的思想?yún)s在東周后就已較早出現(xiàn)了。傳統(tǒng)儒家思想雖然在總體上極力主張德法融合,但在其中也不乏德法分離思想觀點的點點火花。“禮者,治之始也”而“法者,治之端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這些論斷就是作為儒家思想代表的荀子提出的。他認為“禮”是法的總綱而法是“禮”的派生,若將“禮”視為反映社會道德關(guān)系的基本規(guī)范,按照我們今天的理解其實就是法律起源于道德,當然這其中自然就包含了法律區(qū)別于道德之義。萌芽于春秋之際的法家思想從其產(chǎn)生之時開始,就旗幟鮮明地提出了道德應(yīng)與法律分離的主張。特別是“‘不法先王,不是禮義’、‘法為天下之至道’、‘禁奸止過,莫若重刑’等偏激法治觀念的蔓延,則標志著法律與道德的分離越來越遠。”[12]韓非子甚至還提出了“不務(wù)法而務(wù)德”的主張。自兩漢起德法融合的思想雖總占據(jù)著統(tǒng)治地位,但人們對道德與法律區(qū)別的認識卻越來越清晰。“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以及“出禮則入刑”,就語出自記載東漢歷史的《后漢書·陳寵傳》。即使是在“一準乎禮”、“德主刑輔”的唐代,人們?nèi)阅茉谡J識中明晰道德與法律的不同作用。李世民更提出了“制禮以崇敬、立刑以明威”,以及“失禮之禁,著在刑書”等很多著名論斷,在后者中他更是將刑的作用歸于禁止失禮行為。[13]而這句話若用法倫理學(xué)的現(xiàn)代話語來進行注解,就是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或者說是底線道德,逾越道德這個底線也就進入了法律的調(diào)整領(lǐng)域。中國社會自宋以后進入了“以德代法”的時代,以程朱理學(xué)為代表的封建禮教取得了統(tǒng)治地位,它在對社會的調(diào)控功能上甚至取代了封建法律,德禮與刑法的界線在中國才從此開始變得模糊,而在此之前道德與法律卻依然處于分離的狀態(tài)。這意味著中國傳統(tǒng)社會盡管以德代法占據(jù)主流,但仍然具有時間較長的道德與法律分離的歷史。注重弘揚這種傳統(tǒng)、區(qū)分道德與法律間的界線,這也就是“出禮入法”對現(xiàn)代中國法治的啟示。 二、“引禮入法”:不斷推動道德的法律化進程 道德既是法律的起源同時也是立法的重要素材,同時也是現(xiàn)代法倫理學(xué)研究領(lǐng)域中的重要命題。“所謂道德法律化,主要側(cè)重于立法過程,是指立法者將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規(guī)范或道德規(guī)則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國家意志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并使之規(guī)范化、制度化。”[14]道德的法律化自古就是法律生成最主要的途徑,“引禮入法”就是其在中國傳統(tǒng)語境中的表達。“道德在中國古代被譽為‘法上之法’,法律史上所謂的‘引禮入法’,就是法律的道德化。”[15]引禮入法“即把道德原則引入法律,把道德作為立法的精神,并直接成為法律規(guī)范本身”。[16]這種思想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最早出現(xiàn)于戰(zhàn)國末期,“荀子是中國歷史上最早將禮與法結(jié)合起來,以‘法治’充實‘禮治’的思想家。他引禮入法,將體現(xiàn)貴族利益的舊禮改造成了維護封建官僚等級制的新禮”。[17]但“引禮入法”在中國的正式開始卻是在西漢,特別是漢初的董仲舒為此做出了很重要的貢獻。“董氏以儒家典籍,六經(jīng)之一的《春秋》作為判案的依據(jù),更是他為調(diào)合儒法兩種思想實際上做出的一種努力……它以一種特殊方式開啟了中國古代法律史上一個倫理重建的主要時期。在此期間,儒家以其價值重塑法律,系統(tǒng)得完成了儒家倫理的制度化與法律化,結(jié)果是在繼承先秦乃至青銅時代法律遺產(chǎn)的基礎(chǔ)上,將禮崩樂壞之后破碎了的法律經(jīng)驗補綴成一幅完整的圖景,最終成就了中國古代法律的完備體系。這一過程亦即是后人所謂的‘以禮入法’,我們名之為道德的法律化。”[18]在“引禮入法”這個道德不斷法律化的過程中,儒家傳統(tǒng)思想始終對其具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引禮入法’的過程,不但是使法典的制定貫徹儒家的基本精神和原則,還把具體的禮制規(guī)范引入法律,以確保法律的強制實施過程本身就是道德的推行過程,它不但是使法律成為所謂‘最低限度的道德’,還要使法律成為教化成俗的實現(xiàn)德化天下的至善目標的手段。它使法律與道德一體化的過程,不但在形式上消除了法律所獨具的形式和技術(shù)上的獨立意義,還從本體上消除了法與道德的爭論。”[19]在此之后中國也就進入了“禮法融合”的時代。毫無疑問,道德的法律化在現(xiàn)代中國法治中具有重要意義,它有利于社會整體文明程度的提高,有利于社會的制度文明建設(shè),也有利于人的素質(zhì)的極大提高。[20]中國自古就有“引禮入法”的道德法律化傳統(tǒng),這也對現(xiàn)代中國法治建設(shè)提供了某些有益啟示。首先,“在中國這樣一個重視禮儀、廉恥的國度里,要實現(xiàn)法治,必然需要借助于道德的力量……法律規(guī)范應(yīng)以道德準則為標準,‘引禮入法’,將符合人們道德準則的行為規(guī)范以法律形式規(guī)定下來,使道德法律化”。[21]其次,在全社會公認的道德基礎(chǔ)上所凝練而成的法律,“不但大大減少了法律運行的社會成本,最重要的是還穩(wěn)定了基層社會的秩序。”[22]中國傳統(tǒng)社會正是借助“禮”的道德教化形式,實現(xiàn)了在法制不甚發(fā)達狀況下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最后,在現(xiàn)代中國法治進程中道德應(yīng)發(fā)揮出其前瞻性。道德在某種意義上應(yīng)具有著超越現(xiàn)實的前瞻性,盡管有些倫理思想可能與現(xiàn)實的生活有些差距,但是其卻能對法律產(chǎn)生前瞻性和變革性的影響。環(huán)境倫理思想對環(huán)境法的影響就是最好的例證。“環(huán)境倫理的歷史軌跡表明,每一次環(huán)境運動都是對舊價值觀的揚棄,作為其成果的表現(xiàn),人類道德共同體范圍的不斷得到擴展。這種倫理變革為立法提供了倫理基礎(chǔ),并最終勢必會反映在法律制度中(法律反映價值觀念),引發(fā)法律生態(tài)化的趨勢。”[23] 三、“以禮統(tǒng)法”:積極促進法律的道德化完善 法律的道德化也是法倫理學(xué)領(lǐng)域中的重要命題。盡管學(xué)界對法律的道德化有著種種不同的理解,但筆者似乎更愿意在“良法”的概念上理解它。亞里士多德最先提出法律“應(yīng)該本身是制訂得良好的法律”的論斷。[24]所謂“良法”就是“具有道德合理性的法律,也是內(nèi)含著平等、正義、自由等道德價值的法律。”[25]所謂法律道德化就是使法律更具有道德合理性,更加符合平等、正義、自由等道德價值的要求。公平、正義等道德價值是現(xiàn)代法治的理念追求,也是現(xiàn)代中國法治今后要努力構(gòu)筑的價值目標。“越文明發(fā)達、法制完善健全的國家,其法律中體現(xiàn)的道德規(guī)范便越多”。[26]中國自古就有法律道德化的傳統(tǒng),而這個傳統(tǒng)又常與“禮”相結(jié)合。“在傳統(tǒng)中國,法的道德化現(xiàn)象歷來十分嚴重,甚至形成長時期的‘禮法文化’,合禮即合法,合法即合禮,道德是制定、判斷法的根本標準;法是好是壞……一個人是否遵法守法都以‘禮’為準繩。”[27]這種關(guān)系用中國傳統(tǒng)話語表達即“以禮統(tǒng)法”。“以禮統(tǒng)法”中的“統(tǒng)”字即統(tǒng)帥、統(tǒng)領(lǐng)之義,它的意思是說“禮”即道德應(yīng)貫穿法律的全部,法律應(yīng)當彰顯出道德的基本要求以及內(nèi)在精神。中華法系注重“以禮統(tǒng)法”并幾乎達到了極致,最后竟發(fā)展為“禮法不分”甚至“以禮代法”。“禮為中華法系打上了深深倫理道德的烙印。”當我們讀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等詞句時,就會強烈地感受到傳統(tǒng)法律文化中的脈脈溫情。“中國法律剛剛萌芽,倫理道德的內(nèi)容便充斥其中,為中華法系中所特有的溫情打下了基礎(chǔ)。”[28]法律中鮮明的道德色彩是中華法系的基本特征,也是現(xiàn)代中國法治建設(shè)中最為重要的本土資源。中國自清末修律以來開始大量地引進西方法制,以至現(xiàn)代中國竟被歸入了大陸法系國家的范疇,中華法系的諸多傳統(tǒng)幾乎早就已經(jīng)被蕩滌殆盡。西方自古就具有源遠流長的理性主義哲學(xué)傳統(tǒng),加之發(fā)展至近代又受到了科學(xué)主義的強烈影響,在法律中表現(xiàn)出的“重理性、輕德性”的傾向。而這種傾向隨著西方法制的移植也傳入了中國,并導(dǎo)致其竟摒棄了崇尚德性、以禮統(tǒng)法的傳統(tǒng)。因此我們在全面建設(shè)現(xiàn)代中國法治的進程當中,應(yīng)當努力地從其本土資源中發(fā)掘積極有益因素,這樣才能構(gòu)建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現(xiàn)代法治。中國自古就有“以禮統(tǒng)法”的法律道德化傳統(tǒng),這也對現(xiàn)代中國法治建設(shè)提供了某些有益啟示。這表現(xiàn)在立法時應(yīng)保證所立之法符合道德要求,即所立之法應(yīng)當是具有道德合法性的“良法”。“法律存在本身就是人類創(chuàng)造出來服務(wù)于人的生存發(fā)展的,最終有利于人的全面發(fā)展是它的終極道德依據(jù)。”“既然法律對于道德如此重要,它本身就就當是合乎道德的,應(yīng)該擁有道德的合法性。”[29]在立法時另外我們還應(yīng)注重進行道德上的考量,特別是對中華道德文化中積極有益因素的汲取,摒棄西法中的冷冰冰而融入中國式道德的溫情。“在傳統(tǒng)的中國人心目中,天理、國法、人情三者不僅相通,甚至可以理解為是‘三位一體’的。”[30]在注重理性的基礎(chǔ)上同時兼顧德性的內(nèi)在要求,相信這樣的法律才適合國人的思維方式和習(xí)慣,從而才能促成其對法律的尊重并進而自覺遵守。“法律要從根本上得到人們的尊重而不只是畏懼,它就必須符合人們的道德理念,符合人們有關(guān)何為正當?shù)睦砟睢!盵31]

濟科學(xué).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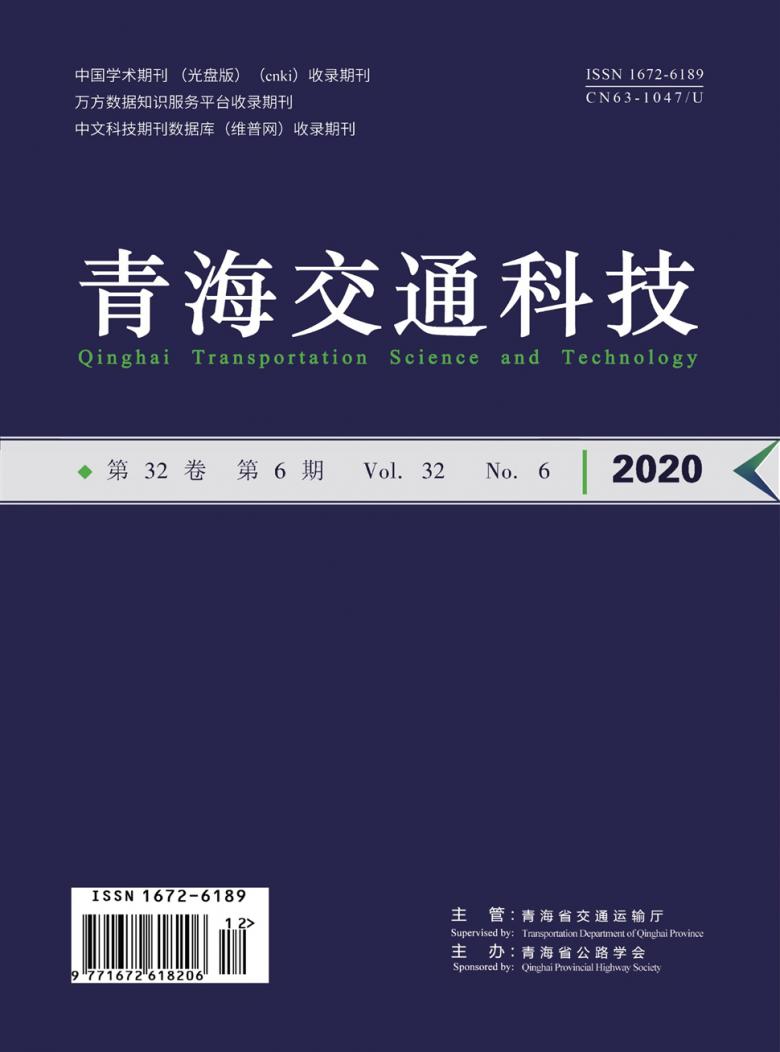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