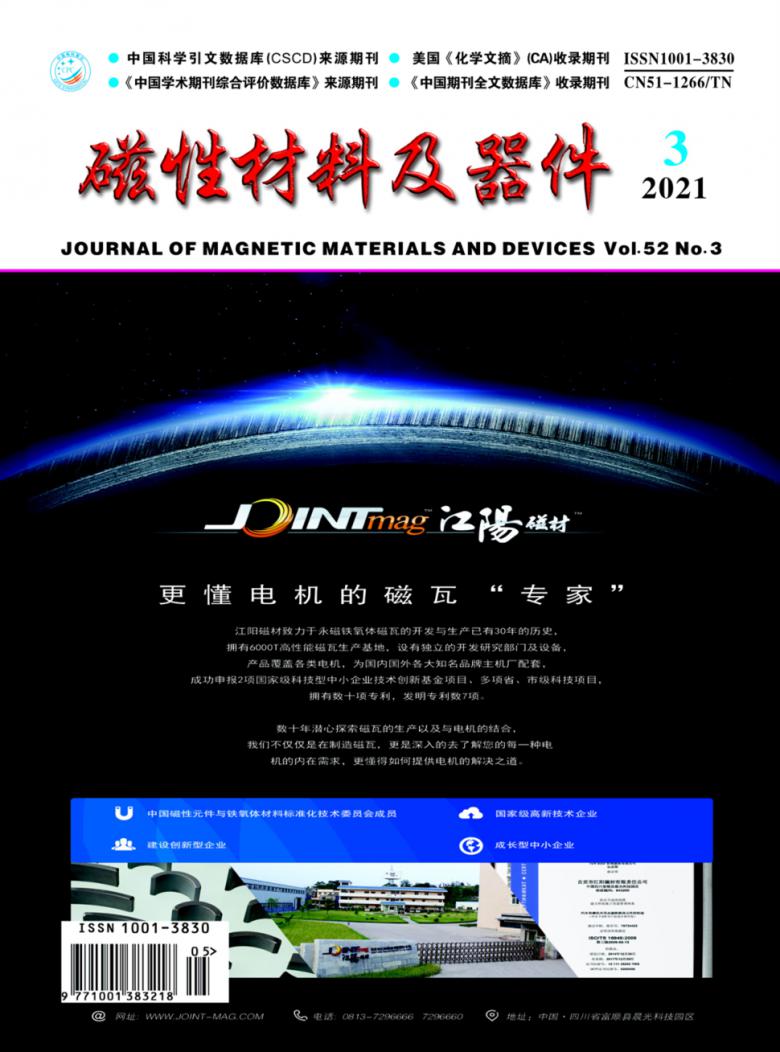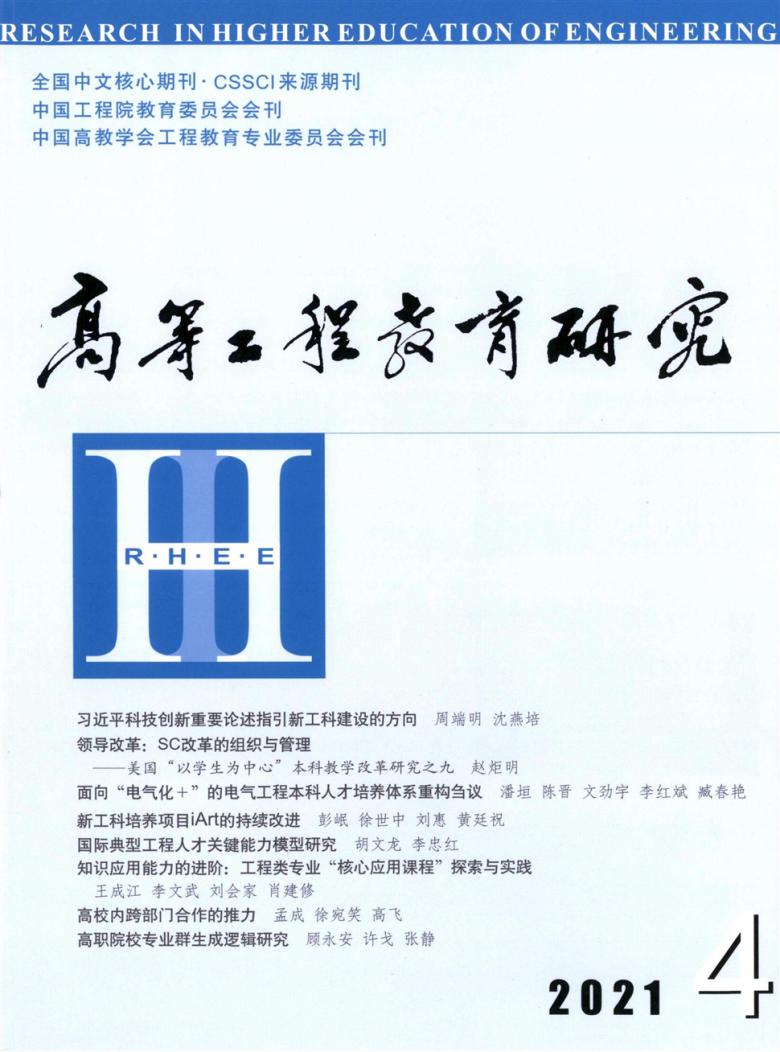關于論儒家民族主義:對批評的回應
貝淡寧等
十分感謝周濂、唐文明、杜楷廷(David ElstEin)和安靖如(Steve Angle)富有洞見的評論。事實上,我同意其中的大多數評議,但我要討論一個重要的爭辯焦點:民族主義的風險,以及儒家民族主義是否能在減輕那些風險上勝任其職。周、杜和安三位認為,我對儒家民族主義的解釋過弱,乃至不能抵御在中國和其他沒有自由—民主憲政框架的國家中的危險型民族主義,他們還認為,對諸如言論自由之類的自由權利,需要作出更為有力的捍衛。唐的觀點則相反,他認為中國“當下的”民族主義根本不是此類擔憂的原因,擔憂與其歸于現實,不如歸于西方對中國的誤識。唐更憂慮美國式霸權民族主義:當中國在全球舞臺變得更強大,就會以類似的方式做事,他由此建議,儒家民族主義也許更有利于挑戰中國和其他地方的民族主義形式。下面我嘗試回答這些批評,并希望能夠鍛造更大共識的“中間路線”得以出現。
周濂提醒我們,儒家不能僅僅由其理想來評判,而應審核理想在歷史上是如何表明自身的。而儒家的政績離完美相去甚遠。周認識到,以儒家名義所行的,并非總能歸于儒家理想,但他也警惕這樣一種回應方式:“好的全是儒家的,不好的全是別人家的”。那是難以令人信服的,所以,我們必須嘗試理解,相比自由民主的憲政體制,儒家為什么更容易被濫用。周質疑“儒家的辯護將導致自由的結果”這一觀點,他似乎更傾向于直接訴諸自由主義,并在自由民主框架下做出一些修正。
同樣,安靖如則注意到,在全球范圍內的許多社會,民族主義有可能被用作萬金油,為任何種類的錯誤治理辯護,而民族主義的建設性一面要得到揭示,就必須面對強大的抵制。而儒家尚未完成這樣的任務:安靖如同意牟宗三的觀點,即在歷史上的儒家傳統中根本找不到據理對公民或政治權利的直接辯護(盡管安靖如進一步認為,牟宗三的“自我坎陷”之辯加以修改就能提供這樣的辯護)。
對于儒家民族主義能夠支持諸如言論自由之類的自由民族主義大多數特點的觀點,杜楷廷也持批評態度。他注意到,歷史上儒家思想家從來沒有提倡自由言說的權利。孔子本人甚至建議禁止鄭之淫聲,而孟子反對這樣的自由觀點:公開辯論是得到真相的關鍵。黃宗羲,這位也許是傳統中國最激進的思想家,從來沒有建議說,農夫應該表達他們的意見。而蔣慶這樣的當代儒家思想家公開偏向禁止“壞”電影和“壞”電視節目。
也許我恰恰應該承認,比起我在原先文章中所認為的,自由主義和儒家在言論自由上的觀點有著更大的差異,而且,這樣的差異在某些情況下會導致不同的結果。但那不一定就是壞事情;在言論自由上,儒家強調政治言論的重要性,以便錯誤政策得到糾正,但不太看好面向所有人的自由的好處,這樣的觀點也許更正確。毫無疑問,儒家人士對小人作出有德判斷的能力表示憂慮,這可以為某種針對民眾的家長式道德教育提供辯護。具體說,這可能意味著,一方面有更獨立的媒體重在揭示社會問題的真相,當政府做錯事時譴責政府;另一方面,政府提供資金的媒體則會樹立道德楷模,訴諸民眾更好的人性,幫助產生對弱勢者的同情。確實,儒者一般選擇“軟實力”來傳遞儒家價值觀,但也會預備直接禁止那些被廣泛認為是不道德的事情,比如,暴力色情。杜楷廷以為,“中國哲學家一般都對已經認識的道充滿自信”,這是過于夸張的——儒家的關鍵是謙恭和對人的局限的承認,對自我修養和向別人學習有著畢生的追求,這一點與基督徒要么信要么不信的觀點構成對比——但他們對什么是壞事確實更為確定,也難以看出允許有暴力色情這樣的惡行流布的自由市場有什么好處。對言論自由的這種觀點也許遠遠不同于美國的言論自由理想——除非自由言論幾乎確然導致立即的身體傷害,自由言論不受約束。不過,其他西方國家并不采納這樣一種“原教旨主義的”言論自由觀。比如,在加拿大,對“仇恨”其他種族和性向的言論予以懲罰。
概而言之,“儒家民族主義”或許真的不能防止統治者違反社會生活諸般領域中的各種自由言論形式。但它確實可以防止那些試圖壓制批評錯誤政策的言論的統治者,這是最重要的關切點。由美國式自由民族主義所保護的言論自由之其他方面,是更值得商榷的,不一定在中國或別處合適。
杜楷廷也擔心,提倡一種制度化國家宗教的儒教徒會走得更遠,超出丹麥和英聯邦的官方宗教模式。在這方面,我原來的觀點也應該退讓。蔣慶等人確實偏向于在學校或干部培訓上進行更多儒家價值觀教育,而在有著國家宗教的一些歐洲國家,并不以如此方式直接把宗教和教育混在一起。但我們需要問一問,從道德觀點看,蔣慶的提案是否存有問題。如果兒童在學校里學習孝和仁,政府官員至少部分地受訓于儒家倫理——旨在培養公共精神和清廉作風,那有什么錯呢?我們只是擔憂,如果其他宗教和倫理體系無法表達,而儒家建立制度化宗教的提案并不對宗教寬容的理想構成根本威脅。處于儒家倫理核心的,是“和而不同”,“和”的價值肯定了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和不同信仰間的互相適應。當然,實際上,現實和理想之間存有差距。不過,我們可以說,就寬容其他宗教方面的歷史記錄而言,儒家比主導的一神論宗教來得干凈。杜楷廷現在憂慮儒家對于在曲阜建造一座42米高的教堂的反應(當地的孔廟只有25米高)。但儒家的批評也澄清了一點,他們并不反對別處的基督教教堂;他們只是反對教堂的規模,及其教堂離儒家文化之故鄉過于接近。同樣,如果有個建議,要在梵蒂岡附近樹立一座孔子紀念碑,并使得圣彼得大教堂顯得低矮,那么,天主教予以反對也完全有理。
周濂擔心,儒家對政治平等的修改,意味著保護被政府的政策所影響的外國人和子孫后代的利益,這有可能威脅到言論自由和對其他宗教的寬容。但理論上,根本不相容。言論自由最著名的倡導者——19世紀英國自由理論家密爾——也提倡對政治平等理想的修正,比如,給受過教育的人額外的選票。但在實踐上,香港是個出色的例子,這一政治共同體的領袖們不是基于一人一票選出來的,但也保護了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和其他公民權利。對此的一個反應或許是,我們應該首先實行一人一票意義上的自由民主制,然后考慮對它的修正。但選民將不會輕易放手他們的權利,而且,一旦自由民主得以實行,即使有很好的理由去改進制度,修改確實十分困難,即使并非不可能。
總之,與我原來文章中所言相比,儒家民族主義也許確實與自由民族主義有更大的差異。但這種差異可以從道德觀點得到辯護,而對儒家民族主義為損害重大公民自由作辯護的擔憂也許是夸大其詞的。
唐文明的取徑極為不同。他認為,對當下中國的民族主義,根本不用擔憂,因此也就根本不需要提出什么建議來抵制種種民族主義在中國的危險的發展。他認為,對民族主義的此類憂慮更多來自西方對中國的恐懼,而不是來自中國的現實。真正要憂慮的是美國式霸權主義,而我們應該憂慮,隨著中國在全球舞臺越來越有影響力,中國將轉向哪種民族主義。而唐建議,儒家民族主義在挑戰美國霸權主義上或許是有幫助的。
某種程度上,我同意這一批評。臨近2008北京奧運會之際,許多西方分析家擔心,該項盛事會成為中國危險型民族主義的表達渠道。當時我住在北京,我覺得這樣的擔心是夸張的,并為此撰寫了幾篇文章,旨在打消這樣的恐懼。我當時預測到,2008奧運不會像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那樣高唱“美國第一”那樣的民族主義贊歌,而是會宣傳文明禮貌,以及對外國游客和運動員的歡迎態度,包括來自與中國有過沖突歷史的那些國家的客人,這樣的取向恰恰會抑制令人反感的民族主義表現。我認為,事實已表明,當時對民族主義的擔憂確實是夸張的。
不過,我還是對當下的民族主義不太樂觀,我認為我們需要提出更好的建議。對中國民粹的和沒有道德的民族主義之極端形式表示擔憂的,不僅僅是西方人,那是中國自由知識分子(周濂就是很好的例子)的共同憂慮,一些為諸如《環球時報》這樣的“民族主義”報紙工作的朋友告訴我,報紙上越是有極端的民族主義觀點,報紙就越是好賣,而他們不得不在商業考量和倫理考量之間做出平衡。不論是好是壞,好戰的、鷹派的民族主義似乎很有市場。
上面是說理,我也另外說一點:我在北京七年半期間,很少遇到表達出危險型民族主義的人。也許這是好的跡象,因為這意味著知識分子,即與我交往的主要群體,并沒落入壞的形式的民族主義。在斯坦福大學訪學期間(就在入侵伊拉克之前一段時間),我也有同樣的印象。雖說斯坦福大學被認為是相對保守的,可我沒有遇見一位支持布什(George W. Bush)攻打伊拉克計劃的學生或教授。入侵的發生在當時確實得到堅實的民眾支持,但“人民”其實是被蒙騙了——薩達姆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一謊言最終被揭穿,而在人民心里灌輸進的基地組織與伊拉克政權存在聯系,也被認為是宣傳攻勢。這是在相對自由的媒體環境下完成的。概括說,我們——批判性知識分子——需要提防民族主義被壞政府濫用的方式,一種途徑就是提倡具有道德吸引力的民族主義形式。
唐文明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很大程度上是反應性的,我同意這個說法。民族主義是舶來品,是自19世紀以來受西方列強和日本帝國侵略而引起的議題。有將近百年時間——恥辱世紀——中國在軍事上接二連三失敗,而國家也陷入貧困和內戰。中國精英的心思牽纏于這樣的痛苦現實:在日益擴展的威斯特伐利亞國際秩序中,他們的政體處于邊緣化地位。如果中國要存續,那就不得不按照這一體系來調整。實際上,這意味著增強國家。我把這一民族主義形式稱作法家的,乃是因為它強調幾近不惜一切代價來增強國力,當然,我同意杜楷廷指出的一點,即當前的民族主義之其他方面,諸如追求民族自豪,并不屬于法家思維。
從規范立場看,確實有理由擔心那種為了國家富強而借助怨恨情感的民族主義。建立國力的道德支點是要確保政治的穩定,以便人民能夠過上有尊嚴的生活,并無需擔心物質匱乏和人身安全(這是顯然不過的觀點,但歷史上的法家思想家似乎無視這一觀點,而當今那些捍衛不顧道德來構建國力這種做法的人則根本無視這一觀點)。如果說,當中國既很窮又遭受外來勢力欺壓時,如此構建國力還可說得通,但中國現已成為一個主要的經濟大國并且有著相對安全的領土邊界,再堅持那種做法也就難以得到辯護。可以認為,在上世紀90年代初對“愛國教育”的重新強調,很大程度上出于國內對政治正當性的關切,而不是擔心外來干涉。如今,怨恨性民族主義常常被用于愛國教育,而不是其他。
總之,在美國式霸權主義的危險方面,我大致同意唐文明的看法。我和他一樣擔心,隨著中國在世界上日益強大,中國可能變成霸權國家。當然,我也同意,儒家民族主義可以并且應該挑戰霸權主義。但我還是認為,我們應該認識到,中國存在一種土生土長的“法家”民族主義,對一個不僅有能力抵御外國欺負而且有能力欺負別國的國家來說,法家民族主義不再合適。中國正在從一個生存時代走向擴張時代,而在當前和未來國際背景下,儒家民族主義是最適合這個國家的。
最后,讓我回應唐文明的一個建議,即儒家思想應該具有普遍價值;不只中國可欲,而且整個世界都可欲。在此,我也同意他的看法。正如基督徒認為基督教價值觀優于其他宗教的價值觀,自由主義者相信自由價值觀優于其他政治價值觀,儒家信徒也相信儒家價值觀優于非儒家的價值觀。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承認,就如安靖如指出的,儒家民族主義在不同語境將具有不同的特點。甚至有著共同的儒家遺存的諸社會也會有所不同——中國儒家不同于韓國儒家,諸如此類。在沒有儒家遺存的國家提倡儒家價值觀會面臨更大的挑戰。作為一個認同儒家倫理的加拿大公民,我顯然希望儒家能夠傳播到加拿大,但我也認識到,自由個人主義在那里居主導地位,更不用說語言上的差異,使得在可見的將來,這種希望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樣的話,中國能做什么?在我看來,它可以為世界其他地方確立榜樣。這需要時間,這過程將包括“進兩步,退一步”,但是,如果中國在踐行自己所宣講的儒家倫理上做得很好,其他國家會越來越被儒家倫理所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