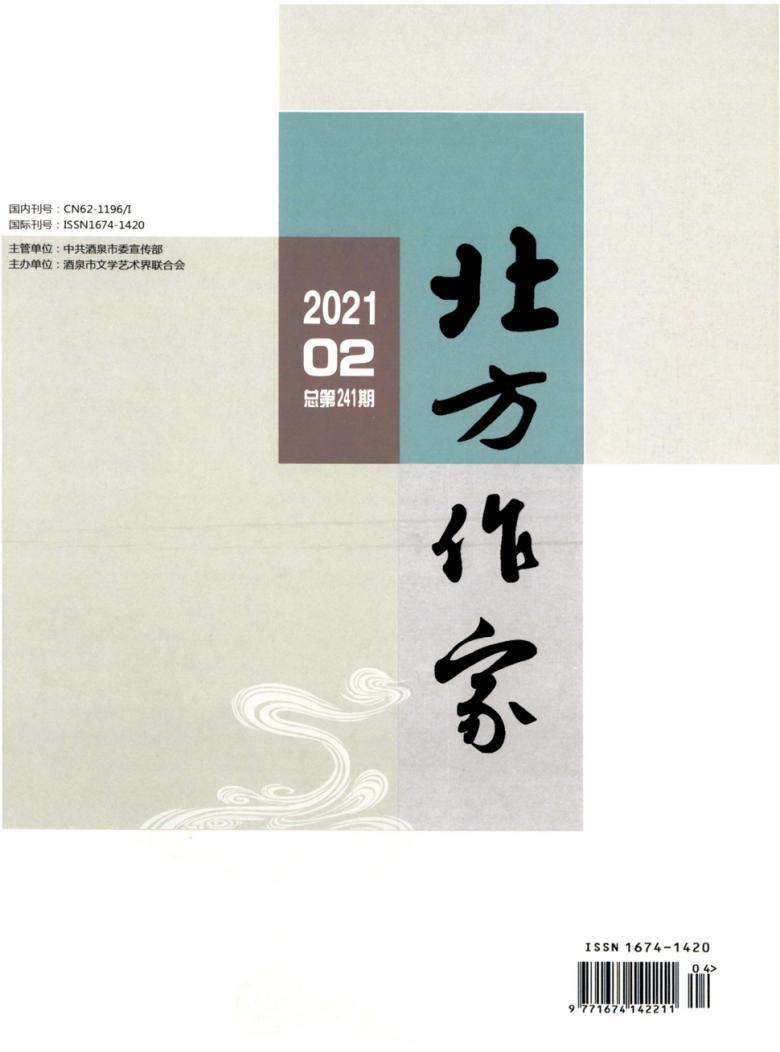關于儒家政治哲學的產生與發展
康宇
政”,天下必然大亂。因為,“小人”是遠離“道”的,他們的生活僅受動物性“欲望”的支配,而遺忘了對“精神性”的訴求。為了實現“道”,儒家將“禮”作為建構政治合法性的手段,認為人需以“禮”而“定命”,而“庇身”,而“定位”。儒家在對“禮”的意義闡釋中,將人之生命價值安頓在“名位”之上。由此,“正名”成為“為政”的根本。儒家“正名”的根本目的在于禮制秩序的重建,而秩序的建構必須要尊“道”、合“道”、護“道”。這既是一個嚴肅的倫理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關涉到社會秩序的建立和穩固,關涉到“治”、“亂”這個秩序的根本。
在解決了政治如何才能具有合法性問題后,儒家進一步構建出自身政治哲學的本體論。儒家將政治與人性相聯系,認為政治始終是人的政治,人是什么樣的,必然決定政治是什么樣的。孔子首先提出了“仁者愛人”的類概念,并且認為“性相近,習相遠也”(《論語·陽貨》)。出于建構完整明晰的思想學說的需要,戰國時期儒家不再滿足于孔子的這一說法,他們試圖對人性的善惡做出明確的判斷,于是便出現了思孟學派的性善論和荀子的性惡論。無論是性善論者,還是性惡論者,都認為人的本性是先驗的。秦漢以后,人性的善惡一直是人們爭論的主題。從兩漢至明清之際,歷代儒家關于人性問題的爭論主要出現了“善惡混說”、“性三品說”、“稟氣說”等。但毫無例外地,儒家代表人物都在邏輯上默認了人在道德品質方面先驗的等級差別,進而在本原的意義上認定了人是不平等的。人的不平等直接導致了社會政治的不平等。儒家將社會中的人進行了“君子”與“民眾”的區分。認為君子是道德品質良好的人,但是這樣的人一定不是社會底層的大眾。“君子”可以成為社會中的“圣王”,社會政治權力應該由“圣王”來掌握。儒家將對于優良的社會生活的追求完全寄托在“圣王”身上,所以“人治”便成為儒家治國方略的核心。 儒家認為,個體人格的完善具有無限可能性,只要權力主體都能做到“反求諸己”,一心向善,帶動全民從事道德實踐,就可以化解一切社會紛爭,達成整個社會秩序的完滿和諧。正是對于人性可臻完美境界的執著信仰,儒家在對權力制約的思考上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于個體內在約束機制的建構,集中于權力主體利他偏好的塑造,并由此將“人治”演化為一整套自成一體的“德治”政治哲學。“德治”不僅意味著形成了一種比外部制度規范更為有效的約束機制,而且意味著一種更高的政治境界。這樣,政治實踐的根本問題就演變成了一個道德教化問題,政治與人性道德之間出現了一種內在的關聯,“內圣外王”成為儒家政治思維的基本模式。“內圣外王”是儒家整個政治思想體系的核心,它既是一種價值信念,又是一種現實的政治實踐模式,更是儒家政治哲學的內在理路。 為了實現“內圣外王”,儒家政治哲學創造出了自己的方法論體系。首先,教民與化民。作為國家治理的模式,內圣外王之道不僅強調統治者要以德服人,不是以力服人,而且還強調將道德作為社會生存與發展的基礎。儒家認為社會中調節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原則,只能是仁與禮,而非其他。因此,儒家強調對百姓進行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其次,德化。統治者要以身作則,以道德感化天下。再次,立信。統治者取信于人民,才能贏得人民的親近,才能使臣忠于君。最后,大同社會理想設計。儒家認可的終極社會政治目標,是實現社會大同。這種大同社會,不只是百姓安居樂業和豐衣足食,更重要的是道德風俗美好、人與人關系相處和諧。 可以看到,儒家政治哲學與儒家道德學說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它將維護社會穩定、推動社會發展、促進社會完善作為政治目的;將個人的修身齊家,與治國平天下,經世緯國,德濟蒼生,為萬世開太平,作為政治任務。在天民合一、天德合一、天禮合一的基礎上,儒家政治哲學完成了自己體系的建構。 三、儒家政治哲學的當代意蘊 政治哲學的社會功能使它永遠都是現實政治的一部分,永遠承擔著性質一致卻又具體內容不同的使命——在不同政治社會,人民根本利益的性質、內容不同,人民所需要的政治的實現程度不同,需要政治哲學解決的問題也有所不同。當代中國政治賦予中國政治哲學的使命是解決政治價值問題,即提出、論證體現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價值。雖然儒家政治哲學產生于中國傳統社會,其內在體系更適用于“農業—宗法一人倫”的特殊社會結構,其自身由于產生于一定的歷史條件基礎上因而帶有某些時代的烙印與局限,但它的內在實質仍有許多內容值得現代政治文明所借鑒與吸收。其“民為邦本”的治國理想,“為政以德”的政治學說,“禮法并舉”的執政手段,“尊賢任能”的用人方法,“廉政勤政”的政治態度,至今對當代中國政治文明建設仍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然而,今天我們在對儒家政治哲學的理解與運用中需要著重注意幾個問題。首先,儒家政治哲學并非等同于政治儒學。儒家政治哲學伴隨儒學經歷了千年的發展,而政治儒學是興起于20世紀的現代新儒學的一個新形態。政治儒學具有自己的鮮明的理論特征:它具有強烈的思想批判性,直指“全盤西化”與心性儒學;它具有強烈的政治參與性,形成了一整套關于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的新構想;它具有強烈的文化保守性,從最初把儒學作為“天理”發展到今天主張在中國全面復興儒教。顯然,政治儒學已超越了儒家政治哲學純理性思維的范疇。其次,不可將儒家政治哲學簡單等同于西方社群主義。社群主義是一種與西方傳統的自由主義相抗爭并與之對立的當代西方政治哲學思潮。它從整體主義的網絡式的社群出發分析政治起點;以倫理的德性主義為其價值取向;將社會組織歸結為文化認同的產物;倡導國家和政府的積極有為。這些與同樣主張“社會本位”的儒家政治哲學思維方法有著共同之處。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儒家政治哲學只是西方社群主義在中國的變型。西方社群主義以政治上的抽象的價值取向完全替代了其現實的科學取向,使得其政治理想既缺乏一定可操作性手段又無堅強的制度保障,結果是社群主義的種種努力往往只能最終停留在一種對人類精神的不無空洞的終極關懷上,這是其自身難以逾越的理論局限性。而儒家政治哲學直面社會政治生活,并提出了切入實際的方法論。無疑這使其更易為大眾所接受。最后,儒家政治哲學需要經歷現代轉換。傳統儒家政治哲學體系基本思維模式“內圣外王”認為內圣可以直接達到外王,這事實上是將社會終極價值目標視之為達到社會終極價值目標的手段。而在強調民主政治的今天,人們日益重視實質正義而非程序正義,強調社會目標而輕視經驗方法。同時,民主政治理論邏輯順序也變為通過政治程序運作而達到社會政治終極目標。所以,傳統“內圣外王”不僅具體內涵會發生改變,而自身也應變為“外王內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