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畏兀兒的界定及其文化區(qū)域
王紅梅 楊富學
【內(nèi)容提要】元代是畏兀兒文化發(fā)展的興盛期,由于多種因素的交互影響,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區(qū)域。本文通過對分布于新疆、中亞等地畏兀兒人的界定,以及對各區(qū)域不同文化類型的分析,認為蒙元時代的畏兀兒文化大致可分為三大區(qū)域,即以喀什為中心的伊斯蘭教文化區(qū)、以吐魯番為中心的佛教文化區(qū)和異彩紛呈的內(nèi)遷文化區(qū)。
【關鍵詞】畏兀兒 文化 地域特色 元代 吐魯番
畏兀兒,是元代(包括蒙古國至元代,1206~1368年)漢人對今天維吾爾族、裕固族祖先的稱謂,又寫作畏兀、輝和爾、瑰古、偉吾爾等,如同唐宋時代漢文史書所謂的回鶻一樣,均為回鶻語Uighur的不同音譯。
畏兀兒本為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之一,于8世紀中葉,曾以鄂爾渾河流域為中心,建立了雄強一時的草原大帝國——漠北回鶻汗國。9世紀中葉,由于天災人禍的夾擊,汗國崩潰,部眾遂遷往西域、中亞及河西走廊一帶,分別建立了高昌回鶻汗國、喀喇汗王朝及甘州回鶻、沙州回鶻等民族政權(quán)。后二者因局促于河西走廊的西端,對今天維吾爾族文化的發(fā)展影響不大,故本文從略。
一、蒙元時期畏兀兒的界定
蒙元時代漢文史籍所稱的畏兀兒人指的是哪些人呢?學界長期存在著不同的意見,有的認為畏兀兒人僅指高昌回鶻人的后裔,而不包括喀喇汗王朝主體居民的后代。[1]也就是說,只有聚居于五城,即哈喇火州(亦作哈剌和卓,又稱高昌,今新疆吐魯番市)、別失八里(又稱北庭,今新疆吉木薩爾縣北)、昌八里(今新疆昌吉市)、仰吉八里(今新疆瑪納斯縣)和焉耆一帶的族人。而分布在哈密力(今新疆哈密市)、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縣)、南疆等地的族人則不屬于畏兀兒人。同時也有學者提出不同看法,認為畏兀兒人不僅分布于高昌一帶,也分散在其他地區(qū)。[2]兩種說法各有其道理,但都失之偏頗。前者強調(diào)的是畏兀兒亦都護所管轄的范圍,但忽視在亦都護政權(quán)外其它地區(qū)畏兀兒人的分布;后者強調(diào)的是畏兀兒人的分布區(qū)域,而忽視了史書上所謂畏兀兒一般指代畏兀兒亦都護政權(quán)這一史實。筆者試就這一問題略述己見。
元代民族問題比較復雜,但時人的民族知識卻不夠豐富,民族概念也較為模糊,將民族、政權(quán)、信徒之名稱混為一談是常見的事。有些概念雖然名稱相同,但實質(zhì)內(nèi)涵卻不盡相同。元人在述及西域、中亞民族時,常用“畏兀兒”、“回紇”、“回回”等稱謂。此時,高昌回鶻汗國境內(nèi)的族人大多信仰佛教,被稱為“畏兀兒”。然而,原喀喇汗王朝境內(nèi)的族人因皈依了伊斯蘭教而被稱為“回回”或“回紇”。因此,元代畏兀兒人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被劃分為兩個民族,冠以不同的稱呼。這反映出蒙古人最初是從文化的屬性出發(fā)對西域諸民族進行區(qū)分的。
宋遼之際,“回回”為“回鶻”、“回紇”之音轉(zhuǎn)誤讀,也常常被混用。成吉思汗時期,“回紇”與“回回”雖略有區(qū)分,但并不明確,而且時常混用。近代學者認為金元之際漢文史籍中的“回紇”指的是穆斯林,其實并非完全如此。
成吉思汗西征中亞,曾邀邱處機西行覲見。邱處機遂撰《長春真人西游記》2卷以記錄沿途所聞所見。據(jù)筆者統(tǒng)計,在上卷中,“回紇”出現(xiàn)18處,“畏午兒”、“鋪速滿”、“迭屑”各出現(xiàn)1處。文中的“回紇”有時指穆斯林,有時又指畏兀兒佛教徒。
在《長春真人西游記》上卷中,至少有3處講到的“回紇”應指信奉佛教的畏兀兒人,即:
抵陰山(今天山博格達峰)后,回紇(著重號為筆者所加,下同)郊迎,至小城北,酋長設蒲萄酒及名果、大餅、胡蔥。
西即鱉思馬大城(即別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薩爾縣北)。王官庶士僧道數(shù)百,具威儀遠迎……時回紇王部族供蒲萄酒,供以異花、雜果、名香。
又歷二城,重九日至回紇昌八剌城(今新疆昌吉市),其王畏午兒與鎮(zhèn)海有舊,率眾部族及回紇僧,皆遠迎。有僧來侍坐,使譯者問看何經(jīng)典,僧云“剃度受戒,禮佛為師”。[3]
這里所述地區(qū),均在別失八里和昌八里一帶,是畏兀兒人較為集中的地方,盛行佛教,同時兼有道、儒并行。可見,這四處“回紇”均指信奉佛教的畏兀兒人。當時,昌八剌城是佛教與伊斯蘭教的分界線,以東僧侶居多,但“西去無僧,回紇但禮西方耳。”[4]這里的“回紇”又指皈依了伊斯蘭教的穆斯林。需要指出的是,書中誤將“畏午兒”當作回鶻王之名來處理,顯然也是民族知識缺乏所致。
在該書下卷中,“回紇”出現(xiàn)五處,其中有2處指的是文字,即“回紇字”:
車舟農(nóng)器制度,頗異中原……市用金錢無輪孔,兩面鑿回紇字。
上悅,曰:“神仙是言,正合朕心。”敕左右記之以回紇字。
至于這里的“回紇字”指的是回鶻文還是阿拉伯字,有待進一步考證。
后來,劉祁所撰《北使記》,似乎對“回紇”有了更深入的認識。據(jù)筆者統(tǒng)計,“回紇”共出現(xiàn)10處,“瑰古”、“回鶻”各出現(xiàn)1處。瑰古、回鶻即指畏兀兒,而“回紇”似乎指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對此,學界已有專論,[5]這里不再贅述。
元代“回回”概念所涉及的民族亦很寬泛,不僅包括原阿拉伯帝國境內(nèi)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也包括中亞伊斯蘭化的突厥人、西遼故地的其他突厥人,還有來自非洲的黑回回等。蒙古統(tǒng)治者將有伊斯蘭文化背景的人稱為回回,但有時亦將非穆斯林冠以回回之稱,如稱猶太教徒為“術忽回回”,稱來自敘利亞的基督教徒為“愛薛回回”,稱信仰東正教的阿速人為“綠眼回回”。因此,“回回”并不等同于穆斯林。[6]
鑒于漢文史籍記載之混雜,在研究畏兀兒人的具體分布及其文化時,不能局限于漢文史籍的記載,而應結(jié)合近代出土的考古資料與少數(shù)民族古文獻,并應用民族學的基本原理,來深入考察其真實內(nèi)涵。
眾所周知,近代民族學界對民族進行界定時,仍依據(jù)斯大林的定義,即“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jīng)濟生活以及表現(xiàn)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zhì)的穩(wěn)定的共同體”。[7]該定義不僅適用于現(xiàn)代民族,在一定程度上也適用于古代民族。在判斷元代西域民族時,也應根據(jù)這四個標準——共同的語言、共同的經(jīng)濟生活、共同的地域、共同的民族心理——來辨別其族屬。
元代的哈密,有人認為元代不屬于畏兀兒,應是一個與畏兀兒地面并存的封建地方政權(quán)。[8]如果僅以政權(quán)(即所謂的“地面”)來觀察,這種說法似有一定道理,但哈密的居民,應該說是以畏兀兒為主的。元明漢文史籍中對哈密的記載較少,但是近代哈密的考古發(fā)現(xiàn)可以提供更真實、更具說服力的佐證。1959年在哈密縣天山公社發(fā)現(xiàn)了大型回鶻文佛經(jīng)《彌勒會見記》殘卷。回鶻文本應譯自吐火羅語,譯經(jīng)年代約在9、10世紀。哈密本《彌勒會見記》保存較為完整,字體為工整的寫經(jīng)體。[9]哈密市五堡鄉(xiāng)四堡村北還有恰普禪室,內(nèi)存少量壁畫,從藝術風格來判斷,應屬于高昌回鶻時代之遺物。[10]可見,哈密在唐末已成為高昌回鶻佛教的一個中心。
有元一代,哈密的畏兀兒文化昌盛,人才輩出,著名畏兀兒大臣塔本就是伊吾廬(即今新疆哈密)人。塔本世居伊吾廬,為高昌回鶻王國的臣民。其父是高昌國王所封“沱沱”,意即“國老”。塔本與布魯海涯一同追隨高昌王巴而術阿而忒的斤,跟從成吉思汗東征西討,立下赫赫戰(zhàn)功。元代著名畏兀兒高僧必蘭納識里也是感木魯國(即哈密)人,他奉旨跟從帝師受戒于廣寒殿,代元成宗出家,被任命為“國師”,地位僅次于帝師,并翻譯佛經(jīng)五、六種。在敦煌出土的元代回鶻文藏密佛經(jīng)《吉祥輪律儀》殘卷,回鶻文譯者即為哈密人。該抄本第46頁載:“哈密尊者阿阇黎(ārya ā?arī)遵佟巴(Istongpa)大師之令翻譯。”[11]此外,西北藩王都哇叛軍攻下火州時,高昌亦都護火赤哈兒的斤帶領回鶻民眾逃到哈密,屯兵駐守于此。《馬克波羅行記》也記載說哈密“居民皆是偶像教徒,自有其語言”。[12]可證當時哈密畏兀兒人數(shù)量當不在少數(shù),我們不能囿于政權(quán)名稱和界域來觀察當?shù)氐拿褡鍖傩詥栴}。
南部塔里木盆地周邊綠洲居民的族屬問題始終是史學界爭論的焦點之一。元明漢文史籍中在敘述西域少數(shù)民族時,常以地名稱謂族人,以籍貫代替族屬。然而,籍貫與族屬畢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不能混為一談。
于闐地區(qū)人種較為復雜,自古以來,就有漢、羌、塞人、吐蕃、維吾爾等族人先后在此定居生活。840年,漠北回鶻汗國崩潰,部眾西遷時,有一支遷往那里。宋代史籍中涉及于闐回鶻人的記載頗多。《宋史·回鶻傳》:“初,回鶻西奔,族種散處。故甘州有可汗王,西州有克韓王,新復州有黑韓王,皆其后焉”。此載說明當時有一支遷到了于闐附近的新復州(又作新福州),其首領稱為“黑韓王”。《宋史·于闐傳》載:“大中祥符二年(1009)其國黑韓王遣回鶻羅廝溫等以方物來貢。”在喀喇汗王朝攻占于闐之初,于闐國仍遣使至宋王朝進貢,而且使臣就是回鶻人。
其王雖出自尉遲氏,非回鶻族,但不可否認在晚唐五代以后就已經(jīng)回鶻化了。如于闐有王名曰李圣天。其中“圣天”一詞,就很容易使人將之與回鶻聯(lián)系起來。敦煌莫高窟第98窟為歸義軍節(jié)度使曹議金所開“功德窟”,在主室東壁南側(cè)有于闐王李圣天的畫像,題名為“大朝大寶于闐國大圣大明天子……”而在同窟同壁之北側(cè)畫有回鶻女供養(yǎng)人像,題名為“敕授汧國公主是北方大回鶻國圣天可汗……”[13]說明甘州回鶻的可汗亦被稱作“圣天”。在俄藏敦煌文獻Dx. 2148《天壽二年九月弱婢員娘祐定等牒》中,于闐有公主稱“天女公主”,[14]而在敦煌歸義軍節(jié)度使曹元忠及夫人潯陽翟氏所開“功德窟”(第61窟)主室東壁南側(cè),亦繪有回鶻女供養(yǎng)人,題名結(jié)銜為:“故母北方大回鶻國圣天的子敕授秦國天公主隴西李……”[15]說明甘州回鶻的公主亦稱“天公主”。這些因素使我們不能不想到回鶻文化對于闐王族的深刻影響。
《宋史·于闐傳》還記載:元豐四年(1081)“于闐國僂倮有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這里,于闐國主沿襲了漠北回鶻與唐王朝甥舅關系的稱謂。據(jù)此可推測,有宋一代,于闐國內(nèi)的主要民族似為回鶻人。這表明,回鶻人在于闐國中占有較優(yōu)勢的地位,在與當?shù)鼐用竦碾s居中,逐步融合了當?shù)氐钠渌褡澹蔀樵@里的主體民族,盡管漢文史籍對當?shù)孛褡宓挠浭鲱H為籠統(tǒng)、模糊。
筆者認為,畏兀兒人不僅聚居在于闐一帶,也分布在原喀喇汗王朝境內(nèi)的其他地區(qū)。據(jù)漢文史籍記載,漠北回鶻汗國崩潰時,一支回鶻人“西奔葛邏祿”,于10世紀建立了喀喇汗王朝。學術界就喀喇汗王朝的族屬有所爭議,有樣磨說、回鶻說、葛邏祿說等多種觀點。但國內(nèi)學者大多認為喀喇汗王族起源于漠北回鶻,其汗族在血統(tǒng)上與漠北回鶻可汗是一脈相承的。[16]在于闐、莎車等地,都有古回鶻文寫本發(fā)現(xiàn),其中,在于闐發(fā)現(xiàn)的有24件,在莎車發(fā)現(xiàn)的有3件。[17]這些文書表明當時在于闐、莎車等地就有回鶻人生活。伊斯蘭教的傳入和廣泛流傳,以及阿拉伯文字的使用,加速了新疆南部土著居民的回鶻化,至蒙元時期,這種趨勢更加明顯。
蒙元時期,隨著高昌亦都護歸順成吉思汗,畏兀兒人的活動范圍,已不局限在新疆,而延伸到河西和中原的廣大地區(qū)。亦都護率軍跟從蒙古軍東征西討,許多畏兀兒人陸續(xù)遷居內(nèi)地。13世紀中后期,新疆爆發(fā)海都、都哇之亂,高昌城陷落,高昌王室奉旨遷入甘肅永昌,回鶻人大批從天山東部散入甘肅河西走廊。甘肅酒泉發(fā)現(xiàn)的漢—回鶻文對照《重修文殊寺碑》(1326年立)[18]和漢—回鶻文對照《大元肅州路也可達魯花赤世襲之碑》(1361年立)[19]以及武威出土的漢—回鶻文對照《亦都護高昌王世勛碑》(1334年立)[20]即證實了這一點。
總而言之,蒙元時期,畏兀兒人不僅聚居于五城地區(qū),還分布于今新疆天山南北各個綠洲和甘肅西北地區(qū)。盡管我們不能將元代的畏兀兒人與今天的維吾爾等同看待,但不應否認他們之間存在著淵源關系,也不應將吐魯番的畏兀兒人與南疆的畏兀兒人割裂開,看作不同的民族。他們雖生活于不同區(qū)域,但都源自于漠北回鶻;雖宗教信仰有所不同,但都延續(xù)了傳統(tǒng)的漠北文化;雖使用的文字不同,存在著方言差異,但都繼承了漠北回鶻語的語音體系與語法規(guī)則。澄清畏兀兒人的界定,為研究近代維吾爾族的由來、發(fā)展及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學術價值。
由于受歷史的局限,史書對今天維吾爾族的祖先稱謂有相當大的差異。在蒙元時代,大多數(shù)情況下,畏兀兒一詞多用語指代高昌回鶻國的遺民,有時又包括高昌回鶻以外的族人,故我們不妨將畏兀兒一詞區(qū)從廣兩個層面來具體分析。從狹義上講,“畏兀兒”僅指高昌回鶻人的后裔,從廣義上講,該詞指的是高昌回鶻以及居住于原喀喇汗王朝境內(nèi)及河西走廊的回鶻遺民,同時也包括蒙元時代人遷往內(nèi)地的回鶻人。本文所論即采其廣義。
高昌回鶻國祚延續(xù)四百多年,逐漸形成了以吐魯番為中心的佛教政治文化區(qū)(河西回鶻可歸入這一文化區(qū)),而喀喇汗王朝推行伊斯蘭教,演進為以喀什為中心的伊斯蘭教政治文化區(qū)。這種南北對峙局面持續(xù)近四百年之久,直到蒙古軍隊西征,才使這一格局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其中尤為顯著的一點是,畏兀兒人的生活地域已再不局限在西域、中亞,而是延伸到了中原和蒙古等更為廣大的地區(qū),成為蒙古統(tǒng)治者的左膀右臂,在中華歷史舞臺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堪稱高昌、喀什以外的另一個獨具特色獨特的內(nèi)遷畏兀兒文化區(qū)。
二、以喀什為中心的文化區(qū)
喀什,地處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qū)的西南端,著名的絲綢之路就是由這里越過蔥嶺而進入中亞的,具有非常重要的戰(zhàn)略地位。在喀喇汗王朝時期,這里長期是新疆西南部地區(qū)的政治、經(jīng)濟與文化中心,喀喇汗王朝王朝奉行的伊斯蘭教,對這里的歷史文化都曾產(chǎn)生過極為重要的影響。
蒙元時期,伊斯蘭教勢力在新疆西南部地區(qū)非常盛行,形成了以喀什為中心的新疆西南部文化區(qū)域。這里的畏兀兒文化具有明顯的伊斯蘭教色彩,不論是當?shù)氐恼Z言文字、文學藝術、生活習俗,甚或法律制度及思想觀念等,都無不深受伊斯蘭文化的濡染。
伊斯蘭教在回鶻—畏兀兒中的傳播與喀喇汗王朝統(tǒng)治者的扶持、推行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據(jù)穆斯林作家賈瑪爾·喀爾施在13世紀末寫成的《蘇拉赫詞典補編》所保存下來的11世紀作家阿不杜·伽費爾《喀什噶爾史》的一個片斷知,察赤政權(quán)(即喀喇汗王朝前身)建立不久,就與中亞的伊斯蘭國家——薩曼王朝展開了戰(zhàn)爭。伊斯蘭歷280年(893),薩曼國王伊斯瑪依勒打敗了察赤政權(quán)的軍隊,下令將這里原有的基督教大寺院改為清真寺。[21]由于敵不過薩曼王朝的壓力,察赤政權(quán)的一些首領開始走向與薩曼王朝聯(lián)合的道路,率先皈依了伊斯蘭教。據(jù)說,第一個接受伊斯蘭教的是沙土克·布格拉汗,時在10世紀中葉。此人“以傳播伊斯蘭教有功而著名于世,他使千千萬萬的佛教徒和景教徒變成了穆斯林”。[22]其后的歷代喀喇汗王朝君主都致力于以武力傳播伊斯蘭教。
10世紀上半葉,喀喇汗王朝占領喀什,并不斷向于闐滲透,嚴重威脅到李氏王朝的生存。970年或翌年,雙方發(fā)生大戰(zhàn),于闐獲勝。以后數(shù)十年間,雙方戰(zhàn)爭時有發(fā)生,于闐雖曾得到宋、吐蕃及高昌回鶻勢力的支持,但仍以勢單力寡而敗于對手,于1006年被攻占,[23]伊斯蘭化開始。13世紀后半葉,伊斯蘭教勢力向東推進到阿克蘇、庫車和焉耆一線,與高昌回鶻佛教勢力相對峙。蒙元統(tǒng)治者奉行較為寬松的宗教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伊斯蘭教的武力東進,使其在相對和平的環(huán)境中自由發(fā)展與傳播。
蒙元時期,天山南北雖然時有蒙古諸王的叛亂發(fā)生,但是當?shù)匾了固m文化仍在持續(xù)發(fā)展。馬可波羅來華時,所見可失合兒(喀什市)地區(qū)村鎮(zhèn)不少,是當?shù)刈畲蟆⒆罘睒s的城市,居民信奉伊斯蘭教。此外,鴨兒看(即葉兒羌,今莎車)、忽炭(于闐)、培因州(播仙)、車兒城(且末)、羅卜城等地居民業(yè)都信仰該教。[24]
察合臺蒙古后裔因受當?shù)匾了固m文化的影響,逐步放棄原來所信奉的佛教而皈依該教,并且轉(zhuǎn)向農(nóng)耕定居生活。13世紀下半葉,察合臺汗國統(tǒng)治者木八剌薩率先皈依伊斯蘭教。14世紀初這種傾向更加強烈,察合臺后王篤哇之子炔伯將統(tǒng)治中心由七河流域的游牧區(qū)遷到河中農(nóng)耕區(qū),并與其追隨者一起皈依了伊斯蘭教。至14世紀中葉,察合臺汗國分裂為東、西兩部分。東察合臺汗國的大部分地區(qū)已經(jīng)伊斯蘭化,或受到伊斯蘭教的強大影響,定居于此的蒙古后裔也處于伊斯蘭教的汪洋大海之中。禿黑魯·帖木兒利用伊斯蘭宗教界的支持,籠絡突厥各部,維護其統(tǒng)治,于伊斯蘭教歷754年(1353~1354)強迫16萬民眾剪掉長發(fā),皈依伊斯蘭教。“于是,伊斯蘭教載察合臺汗國這一整個地區(qū)傳播開來。”[25]與此同時,中亞、新疆西南部地區(qū)原有的摩尼教、佛教、景教等都相繼走向衰敗,漸趨消亡。隨著宗教文化的一元化,當?shù)赝林用瘢约跋群筮w來的漢、吐蕃、契丹、蒙古等民族,走向伊斯蘭化、回鶻化的過程,逐漸融入到維吾爾人中。
伊斯蘭教的傳播,客觀上促進了塔里木盆地各地的語言文字走向一體化。伊斯蘭教的傳播與廣泛流行,自然而然地導致阿拉伯文伴隨而來。塔里木盆地原有的于闐文、龜茲—焉耆文、婆羅迷文等文字逐漸被廢棄,成為死文字。回鶻文雖在一定范圍、一定時期內(nèi)還在繼續(xù)使用,但已無法與居于統(tǒng)治地位的阿拉伯文字相提并論了。
由于伊斯蘭教的傳播,阿拉伯語和波斯語都開始在中亞、新疆的回鶻—畏兀兒人中流行。在喀喇汗王朝時期形成的具有伊斯蘭文化特色的哈喀尼亞語,在察合臺汗國時期得到進一步的發(fā)展。這種語言雖繼承了古代突厥語的語言特征,但借用了較多的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的借詞、語音及語法形式,與新疆東部地區(qū)流行的回鶻語已迥然由別。在新疆西南部地區(qū),信仰伊斯蘭教的操突厥語的民族,將其作為一種共同的書面語言來使用。由于喀什在伊斯蘭文化的傳播及哈喀尼亞語的形成中都具有特殊的地位,故13世紀以后,這種語言又被稱為“喀什噶爾語”。[26]
隨著伊斯蘭教勢力的逐步東進,哈喀尼亞語也在隨之跟進,至15世紀初,已漸及新疆天山南北和中亞地區(qū),為操突厥語的民族普遍使用,演變成察合臺語。語言文字的統(tǒng)一,客觀上加速了民族的融合,尤其在察合臺汗國時期,占統(tǒng)治地位的各蒙古部落和當?shù)匾恍┎俨ㄋ拐Z族語言的部族,大批地融合到人數(shù)眾多的突厥語諸族中,為近世維吾爾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在以喀什為中心的文化區(qū)內(nèi),與伊斯蘭教相應的風俗習慣也在逐步形成。13世紀初,烏古孫仲端赴中亞覲見成吉思汗。在其所撰《北使記》中,對當?shù)氐拿耧L是這樣記載的:
其婦人衣白,面亦衣,止外其目……其書契約束并回紇字。筆葦其管,言語不與中國通。人死不焚葬,無棺槨,比斂,必西其首。其僧皆發(fā),寺無繪塑,經(jīng)語亦不通,惟和、沙州寺像如中國,誦漢字佛書。[27]
可見,此時中亞及今新疆西南部地區(qū)的大多數(shù)居民的風俗習慣都已深深打上了伊斯蘭文化的烙印,只有和州(今新疆吐魯番市)、沙州(今甘肅敦煌市)尚有佛教繼續(xù)流行,崇拜偶像,誦漢文佛教經(jīng)典。
三、以高昌為中心的文化區(qū)
高昌(今新疆吐魯番市)自古為東西交通的要道,是絲綢之路必經(jīng)之地。該地區(qū)具有優(yōu)越的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農(nóng)業(yè)發(fā)達、人口眾多、文化昌盛。高昌文化突出地體現(xiàn)了一種十字路口文化的特征,因而這里的畏兀兒文化具有多元合成之特色。
西州回鶻繼承融合了當?shù)匚幕?jīng)過四、五百年的發(fā)展,到元代已經(jīng)形成獨特、成熟的封建文明。蒙元時期,高昌地區(qū)的農(nóng)業(yè)得到進一步發(fā)展,畏兀兒人完成了從草原游牧經(jīng)濟向綠洲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的轉(zhuǎn)變,以綠洲文明為主,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中具有較為濃厚的商業(yè)與牧業(yè)色彩。
吐魯番地區(qū)種植業(yè)發(fā)達,葡萄、棉花的種植和加工占據(jù)重要地位。葡萄園是畏兀兒人的主要財產(chǎn),葡萄園經(jīng)營的好壞與其生活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已刊布的元代回鶻文書中有關葡萄園的文書至少有十幾件,其內(nèi)容涉及到葡萄園的租用、買賣、稅收等方面。[28]葡萄酒是畏兀兒的特產(chǎn),為朝廷的主要貢品。這種進奉葡萄酒的制度一直延續(xù)到元朝末年。《經(jīng)世大典·站赤》還記載,元至正七年(1347)十月“西蕃盜起,凡二百余所,陷哈剌火州,劫供葡萄酒,殺使臣。”棉花的種植和棉布的生產(chǎn)、銷售也占有一定的經(jīng)濟地位。而且,元初棉花的種植技術隨著大批內(nèi)遷的畏兀兒人,傳播到陜西等地。《農(nóng)桑輯要》載:“木棉種于陜右,滋茂繁盛,與本土無異。”此處木棉似乎指棉花。
回鶻所處的西域與河西走廊一帶,自古以來就是中西交通的要道——絲綢之路的咽喉要地。在回鶻未西遷以前,這里就是經(jīng)濟繁榮、貿(mào)易發(fā)達之地,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產(chǎn)、供、銷體系,東西方各種民族穿梭往來,不斷地遷徙、流動,于是,各種風格不同的文化也在這里傳播、交流。回鶻人遷入這里后,繼承并發(fā)展了這一優(yōu)良的文化傳統(tǒng),積極發(fā)展與周邊民族的經(jīng)濟文化交流,不僅與中原、西藏、西夏及東北的契丹、女真交往頻繁,而且也與西方的波斯、印度、大秦保持著直接或間接的商業(yè)交往。[29]其中史書記載最多的當為回鶻與中原王朝的關系。五代至宋,回鶻與中原各王朝都保持著密切的關系,經(jīng)常派遣使者朝貢,并接受中原王朝的冊封和回賜,同時也是通過“朝貢”的名義和方式,進行貿(mào)易活動。洪皓在《松漠紀聞》中記載說:
回鶻自唐末浸微……甘、涼、瓜、沙舊皆有族帳,后悉羈縻于西夏……多為商賈于燕,載以橐它,過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賈人苦之……[其人]尤能別珍寶,番漢為市者,非其人為儈,則不能售價。[30]
從中可以看出,回鶻商人數(shù)量是相當多的,利之所在,無遠弗至,而且善識珍寶,少數(shù)民族商人與漢人經(jīng)商,如果沒有回鶻商人的從中撮合,就很難成交,可見回鶻商人的能力之強。他們的活動對溝通中西商業(yè)貿(mào)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畏兀兒人商業(yè)的發(fā)展,又直接帶動了回鶻商品貨幣經(jīng)濟的繁榮。元朝在高昌回鶻境內(nèi)設立“交鈔提舉司”、“交鈔庫”,用以主管紙幣的發(fā)行事宜。1928年,黃文弼在吐魯番收集到兩件“至元通行寶鈔”。近年來,在吐魯番地區(qū)又發(fā)現(xiàn)1件“至元通行寶鈔”,藏于吐魯番博物館。在畏兀兒境內(nèi)還使用金、銀和實物貨幣。在回鶻文書中有一些貨幣名稱,如:Yastuq意為“錠”;?ao,即“鈔”;Sat?r,為重量單位;?ungtung Pao?ao,即“中統(tǒng)寶鈔”;altun yastuq,意為“金幣”;kümü? yastuq意為“銀幣”。[31]
當時,回鶻社會中還流行一種特殊的貨幣——b?z,即粗棉布。在回鶻文書中常提到“蓋有汗王印章的粗棉布”等,在回鶻文契約文書中常見到因為需要通行的棉布,而出售土地、葡萄園、女人等。在此粗棉布并非單純的布,而是具有貨幣的職能。[32]11世紀維吾爾族著名學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在其所著《突厥語大詞典》對這種貨幣的流通使用情況作了如下記載:
qamdu,長四擋子(擋子??z,舊時用的長度單位,合0.71米——引者),寬一拃的一塊粗棉布(b?z),其上蓋有回鶻汗王之印,在商業(yè)流通中起貨幣作用。如果用舊了,七年洗一次,重蓋新印。[33]
粗棉布作為一種貨幣,在吐魯番地區(qū)很普遍,在回鶻文契約文書中頻繁出現(xiàn)。有人未注意到粗棉布所充當?shù)呢泿胖荒埽皇亲⒁獾交佞X文書中頻繁的粗棉布交易,故而誤將其看作簡單的貨物,以此來論定高昌回鶻手工業(yè)的發(fā)達,所有欠妥。
高昌自古即為佛教文化昌盛之地。高昌回鶻時期,佛教進一步發(fā)展,上自王公,下迄子民,信奉者甚眾。然而,佛教并非處于獨尊地位。中亞原有的許多宗教,如薩滿教、摩尼教、基督教之別派景教、祆教,甚至伊斯蘭教,還有中國傳統(tǒng)的道教都曾在此流行,形成了以佛為尊,各教并行的局面。[34]回鶻統(tǒng)治者,不管是高昌回鶻,還是甘州回鶻、沙州回鶻,其統(tǒng)治者都奉行比較寬容的宗教政策,都對任何宗教都不抱什么偏見,聽任流行。他們“對于基督教顯然加以優(yōu)容,對佛教也加以獎掖”,而汗室貴族則繼承蒙古高原時代的傳統(tǒng),仍然“信仰摩尼教。佛教是多數(shù)人民信奉的宗教,景教則為少數(shù)人信奉”。[35]
畏兀兒首領亦都護主動歸順成吉思汗,高昌成為蒙古大汗的直接統(tǒng)轄之地。因此,高昌地區(qū)沒有受到蒙古軍隊的征討,也沒有受到伊斯蘭教勢力的武力征服。高昌地區(qū)的文化保持原有特色,尤其是佛教文化得到了快速的發(fā)展,在蒙元時代,因受到藏傳佛教的影響,密宗色彩逐步加重,由原來的以漢傳佛教為主轉(zhuǎn)型為以漢藏兼重。
公元9~15世紀,眾多佛教經(jīng)典先后被譯成回鶻文。從吐魯番、敦煌、哈密等地出土的回鶻文文獻來看,《大藏經(jīng)》中的經(jīng)、論兩部分的主要經(jīng)典都先后被譯成回鶻文。至元代,回鶻文佛典已經(jīng)相當完備,又有一些藏文佛經(jīng)被譯成回鶻文。其中的大乘經(jīng)典有《金光明最勝王經(jīng)》、《觀身心經(jīng)》、《妙法蓮華經(jīng)》、《觀無量壽經(jīng)》、《阿彌陀經(jīng)》、《華嚴經(jīng)》、《佛說溫室洗浴眾僧經(jīng)》、《地藏菩薩本愿經(jīng)》、《大乘大般涅槃經(jīng)》、《佛名經(jīng)》、《金剛經(jīng)》、《說心性經(jīng)》、《大般若波羅蜜多心經(jīng)》、《圓覺經(jīng)》、《首楞嚴經(jīng)》等,毗曇部著作有《阿毗達磨俱舍論》、《俱舍論實義疏》、《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入阿毗達磨論注》、《俱舍論頌疏》、《入菩提行疏》等。還有一些中原高僧的傳記也被譯入回鶻文,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慧遠傳》等。譯自漢文的密教部著作不多,主要有《圣妙吉祥真實名經(jīng)》(回鶻文注音本)、《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jīng)》等。小乘部經(jīng)典較少,可見者有《長阿含經(jīng)》、《中阿含經(jīng)》、《雜阿含經(jīng)》、《增一阿含經(jīng)》和尚待甄別的《Insadi 經(jīng)》等。[36]
元代是畏兀兒佛教處于鼎盛階段。佛教的興盛推動了印刷業(yè)的發(fā)展。元代出現(xiàn)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技術,也應用到畏兀兒文佛經(jīng)的印刷中。[37]吐魯番一帶出現(xiàn)了高度發(fā)達而且分布較廣的印刷手工業(yè),這里出土的為數(shù)豐富的木刻印刷品,有回鶻、漢、梵、西夏、蒙古、突厥等各種文字。元代的敦煌、吐魯番、大都(今北京市)、杭州、甘州(今甘肅張掖市)等地都成為回鶻文佛經(jīng)的印刷中心。在吐魯番出土的回鶻文佛經(jīng)殘卷中,木刻本佛經(jīng)占有相當大的比例。敦煌還發(fā)現(xiàn)有屬于元代的回鶻文木活字1152枚。[38]另外在庫車、于闐也出土了漢文、八思巴文和古于闐文的木活字印刷品。這表明印刷術經(jīng)過西域傳入波斯、阿拉伯,再從那里傳入歐洲。
元代畏兀兒佛教具有濃厚的密教色彩,高昌石窟壁畫對此有具體明顯,入伯孜克里克石窟中,繪有密教題材壁畫的石窟約占四分之一,有些石窟完全以密教題材為主。[39]敦煌莫高窟的回鶻繪畫重,密教內(nèi)容也為數(shù)不少。
元代高昌地區(qū)畏兀兒仍然使用回鶻文,其語言發(fā)展演變較為緩慢,變化較小。高昌回鶻語基本上完整地保留了古代突厥語的語音特點和規(guī)則,其語法規(guī)則更加完善,繼承了古代突厥語中的許多基本詞匯。但是,由于受到佛學文化的影響,回鶻語中吸收了許多梵語、漢語、粟特語、藏語借詞。高昌回鶻語中量詞的使用逐漸增多,有的量詞是直接借自漢語、梵語,有的量詞為回鶻語派生詞,還出現(xiàn)了動量詞。元代高昌回鶻語已經(jīng)相當發(fā)達,造詞能力很強。不僅借用外來詞匯,還能利用原有詞匯,按照回鶻語的構(gòu)詞規(guī)律,創(chuàng)造許多新詞,來表達佛教術語。[40]
四、內(nèi)遷畏兀兒文化區(qū)
元代西北地區(qū)戰(zhàn)亂較多,再加上內(nèi)地的統(tǒng)一與開放,大批畏兀兒人陸續(xù)東遷,進入內(nèi)地。內(nèi)遷畏兀兒積極弘揚佛教文化,主動接受西藏佛教,使其在內(nèi)地傳播。而且,他們還熱心吸收漢儒文化,積極推行仁政思想,主張“以儒治國、以佛治心”。這反映出傳統(tǒng)儒學與佛教的相互滲透融合。宋元儒學,有理學或道學之一派,摻雜禪宗、道教某些理論,已呈現(xiàn)異化端倪。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國后,首先征服了西北地區(qū)和中亞。1206年,降伏了游牧于金山延續(xù)回鶻文化的乃蠻部,得塔塔統(tǒng)阿,使之傳授回鶻文。1209年,高昌王亦都護巴而術阿而忒的斤率先歸附蒙古,大批回鶻貴族跟隨成吉思汗征戰(zhàn)疆場,并入朝為官。許多回鶻知識分子也受到重用,形成凡“有一材一藝者,畢效于朝”的局面。[41]畏兀兒人的東遷,使畏兀兒文化、佛教得以傳人內(nèi)地和蒙古地區(qū),促進了當?shù)匚幕c佛教的發(fā)展。
元朝建立伊始,西藏薩迦派高僧八思巴被封為國師。1253 年忽必烈召見八思巴,并接受其密宗灌頂。1260年,忽必烈登基為大汗,立即敕封八思巴為國師,賜玉印統(tǒng)領佛教。1269年,加封八思巴為大元帝師。自此,薩迦派高僧連續(xù)擔任元朝帝師,在全國范圍內(nèi)傳播藏傳佛教。
蒙古貴族信奉喇嘛教,但由于語言文字的隔閡,無法直接與西藏高僧交流。回鶻人由于文化水平較為發(fā)達,信仰佛教由來已久,并早已熟悉蒙古語,很快就學會了藏文并領悟喇嘛教,擔負起溝通蒙古統(tǒng)治者和西藏高僧的任務。因而,畏兀兒貴族和學者也皈依藏傳佛教,成為喇嘛僧。
漢文史籍《元史》、《新元史》及《佛祖歷代通載》中記載了阿魯渾薩里、必蘭納識里、舍藍藍和迦魯納答思等幾位著名畏兀兒高僧。其中阿魯渾薩里和迦魯納答思為元朝帝師八思巴的高足,跟隨其學習藏文和藏密。阿魯渾薩里還跟從八思巴去過西藏。畏兀兒高僧還將大量藏文、梵文佛教譯成畏兀兒式蒙古文,供蒙古貴族學習、誦讀。必蘭納識里將5、6種漢文、梵文、藏文佛教譯成畏兀兒式蒙古文。迦魯納答思以畏兀兒式蒙古文翻譯了《西天西番經(jīng)論》,元成宗將其譯著刻板印刷,賜諸王大臣,廣頒天下。吐魯番出土大量的回鶻文木刻本《文殊所說最勝名義經(jīng)》殘卷,可能也是他的譯本。[42]著名的《西夏文大藏經(jīng)》,據(jù)考也是在回鶻高僧白法信、白智光的主持下譯成的,先后歷時53年,選譯經(jīng)典820部,3579卷,分裝入362帙中。[43]
元代是畏兀兒佛教發(fā)展的鼎盛時期。一些畏兀兒高僧陸續(xù)遷居到中原,推動了漢地佛教和蒙古佛教的興盛。蒙古統(tǒng)治者推崇佛教,經(jīng)常舉辦佛事活動。畏兀兒佛僧素養(yǎng)較高,受到統(tǒng)治者的重用。據(jù)《元史·文宗紀》記載,天歷元年(1328)九月,“命高昌僧作佛事于延春閣”,十二月,“命高昌僧作佛事于寶慈殿”;翌年十月,“畏兀僧百八人作佛事于興圣殿”。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春至二十四年(1285~1287),元朝對漢藏大藏經(jīng)進行了整理對堪工作,編定了《至元法寶堪同總錄》。這次校勘的經(jīng)典包括漢、梵、藏、畏兀兒四種文字的佛經(jīng),主要以漢藏兩種文字經(jīng)典為主,但也以梵文和回鶻文佛經(jīng)來校勘佐證。最后整理出漢文《大藏經(jīng)》的總目錄。參加該項工作的畏兀兒學者有迦魯納答思、脫印都統(tǒng)、齋牙答思、安藏、合臺薩里等五人。[44]
佛教對畏兀兒的思想觀念、價值觀、文學藝術也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畏兀兒僧人不僅翻譯佛學經(jīng)典,還創(chuàng)作佛學哲學著作,現(xiàn)刊布的回鶻文《說心性經(jīng)》就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畏兀兒佛教哲學著作。[45]畏兀兒創(chuàng)作的佛教詩歌更多,著名的元代著畏兀兒翻譯家安藏作品豐富,載他去世時,元世祖下詔“收其家遺書,得歌、詩、贊、頌、雜文數(shù)十卷,命刻梓傳世”。[46]惜上述著作均未流傳下來。今天所能見到的安藏詩歌已經(jīng)不多,主要有敦煌發(fā)現(xiàn)的《贊十種善行》和吐魯番出土的《普賢行愿贊》,均押頭韻,是對《華嚴經(jīng)》的歌頌。[47]
元代,許多畏兀兒人既是虔誠的佛教徒,又是儒家文化的倡導者。安藏不僅用漢文翻譯《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種禮贊經(jīng)》,隨后又譯為回鶻文本,[48]并用回鶻文翻譯了八十卷本《大方廣佛華嚴經(jīng)》。[49]據(jù)史書記載,他還曾用回鶻式蒙古文翻譯了《尚書·無逸篇》、《貞觀政要》、《申鑒》、《難經(jīng)》、《本草》等著作其目的在于勸皇上“親經(jīng)史以知古今之亂,正心術以示天下之向”。[50]合剌普華曾上言忽必烈,要以儒家思想治理天下。阿魯渾薩里曾建議元世祖以儒家思想治國,訪求天下有才之士,無論是亡宋遺臣還是出澤隱逸之人,凡有用之才聘以重用。在他的建議下,設置了集賢館,以招納賢士,“征辟四方,宿儒群集闕下,隨其所長而用之”。[51]此后,又在阿魯渾薩里的奏請下,設立了國子學,以儒學培養(yǎng)蒙古貴族子弟。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元朝官吏的文化素質(zhì),也促進了元代儒學的發(fā)展。
蒙元初期,蒙古統(tǒng)治者重用畏兀兒人。他們的漢文化素養(yǎng)較高,對蒙古統(tǒng)治者采用以“漢法治漢地”起到了推動作用。畏兀兒人中,堪稱理學名臣者,應以廉希憲為首。他的父親布魯海牙隨成吉思汗征戰(zhàn),后任燕南諸路廉訪使,遂“以官為姓”,對其后代實行儒家教育。廉希憲,自幼“篤好經(jīng)史、手不釋卷”,元世祖稱其為“廉孟子”。廉希憲尊崇儒學,優(yōu)待儒士,重視人才的培養(yǎng)。他輔助忽必烈,推行漢法,革新政治,建立各級檢察機構(gòu),本著仁政思想,關心民間疾苦,安定民生,恢復發(fā)展生產(chǎn)。[52]
有些畏兀兒人世代篤好儒學,積極弘揚儒學,創(chuàng)辦學校,撰寫文章,發(fā)展教育。高昌偰氏家族具有較高的漢文化,以“屢世簪纓,一門科第”而名聞當時。[53]一門兄弟五人同登進士第,“時人榮之”。[54]偰玉立為泉州路達魯花赤時,“興學校,賑貧乏,考求圖志,搜訪舊聞,聘寓公三山吳鑒,成《清源續(xù)志》二十卷,以補一郡故事。郡人皆勸于文學。”[55]也先脫因任休寧縣達魯花赤時,主張“興建學校,暇則就學宮,進學者,談經(jīng)論史,以明為治之本。”[56]畏兀兒仕宦以仁政治理地方,明教化,厚農(nóng)桑,輕徭役,省刑罰,具有良好的聲譽,在當時對澄清吏治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許多內(nèi)遷畏兀兒逐漸漢化,放棄原有的生活方式,入鄉(xiāng)隨俗,學習漢文經(jīng)典,使用漢文著書立說。元代中后期,涌現(xiàn)了一批造詣頗深、出類拔萃的維吾兒學者。貫云石的散曲、詩、詞、文章和書法在元代負有盛名,廣為流傳。貫云石擅于寫詩,有《酸齋集》傳世,存詩38首。馬祖常的散文功底頗深,《元文類》收其文20篇。他參與編修《英宗實錄》,翻譯《皇圖大訓》、《承華事略》等書,并編輯《列后金鑒》、《千秋紀略》等書。高克恭自幼聰慧,早習父訓,對漢文識悟精深,所畫山水墨竹,在有元一代頗負盛名。盛熙明曾編《法書考》,進獻皇帝。他又善頌佛經(jīng),深究梵語,并著《補陀洛迦考》,收入《普陀山考》。
元朝末期,在蒙古族丞相脫脫監(jiān)修下,各民族史學家通力合作完成了三部正史——《遼史》、《宋史》及《金史》。參與修史的除漢族學者外,還有畏兀兒學者,擔任《宋史》撰修官的岳柱與全普庵撒里,擔任《遼史》撰修官的廉惠山海牙與偰哲篤,擔任《金史》撰修官的沙剌班。畏兀兒農(nóng)學家魯明善系著名喇嘛僧、翰林學士承旨迦魯納答思之子。后因世蔭及其賢廉被授以奉議大夫,延佑初年又被授予中順大夫、安豐路達魯花赤。任職期間,他“修學校,親率弟子,為之講明修農(nóng)書,親勸耕稼。”于1314年著成《農(nóng)桑衣食撮要》。魯明善還好鼓琴,又親定《琴譜》8卷。[57]
內(nèi)遷畏兀兒用漢文創(chuàng)作文學作品,在語言文字、史書編撰、繪畫、書法、音樂等領域取得了卓越成就,促進了元代文學藝術的發(fā)展。
元代是一個開明寬容的時代。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道教,西來的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在開放自由的社會環(huán)境中,自由傳播,相互融合。在交流融合中,它們不可避免地失去原有的一些特色,添加一些異質(zhì)成分。畏兀兒人以其寬容開闊的胸懷,廣泛吸收外來文化,形成獨特的多元融合型文化。在多元文化的融合過程中,不斷吸收其他民族成員,增添新的血液,逐步發(fā)展、壯大,最終形成為統(tǒng)一的維吾爾族。
[1]陳高華:《元代新疆史事雜考》,《新疆歷史論文續(xù)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4~294頁;田衛(wèi)疆:《論元代畏兀兒人對中華文化的歷史貢獻》,《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第216~227頁,等。
[2]楊志玖:《薩都剌的族別及其相關問題》,《元史三論》,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4頁;楊鐮:《元西域詩人群體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0頁,等。
[3]楊建新主編:《古西行記選注》,寧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1~202頁。
[4]同上注,第202頁。
[5]黃時鑒:《釋〈北使記〉所載的“回紇國”及其種類》,《中國史論集》(祝賀楊志玖教授八十壽辰),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93~303頁。
[6]尚衍斌:《元代色目人史事雜考》,《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第93頁。
[7]《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斯大林選集》,上卷,第64頁。
[8]陳高華:《元代新疆史事雜考》,《新疆歷史論文續(xù)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6頁。
[9]楊富學:《回鶻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4頁。
[10]《哈密文物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4~86頁。
[11]莊垣內(nèi)正弘,“ゥイグル語寫本·大英博物館藏Or. 8212(109)について”,《東洋學報》第56卷,1974年,第44頁。
[12]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記》,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1年,第118頁。
[13]敦煌研究院編:《敦煌莫高窟供養(yǎng)人題記》,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32頁。
[14]《俄藏敦煌文獻》第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45頁。
[15]敦煌研究院編:《敦煌莫高窟供養(yǎng)人題記》,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1頁。
[16]魏良弢:《關于喀拉汗王朝起源的幾個問題》,《民族研究》2000年第4期,第58~63頁。
[17]林梅村:《有關莎車發(fā)現(xiàn)的喀喇汗王朝文獻的幾個問題》,《西域研究》1992年第2期,第95~106頁。
[18]耿世民、張寶璽《元回鶻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釋》,《考古學報》1980年第2期,第253~264頁。
[19]耿世民《回鶻文〈大元肅州路也可達魯花赤世襲之碑〉譯釋》,《向達先生紀念論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40~454頁。
[20]耿世民《回鶻文亦都護高昌王世勛碑研究》,《考古學報》1980年第4期,第515~529頁; Geng Simin - J. Hamilton, L’Inscription ou?goure de la stèle commémrorative des Iduq Qut de Qo?o, Turcica 13, 1981, pp. 10-54.
[21]華濤:《賈瑪爾·喀爾施和他的〈蘇拉赫詞典補編〉》,《元史與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0集,1986年,第65頁。
[22] A. Vambéry, History of Bokhara, London 1873, p. 82.
[23]關于喀剌汗王朝占領于闐的時間,學界存在著多種說法。據(jù)敦煌出土的于闐文寫本《于闐文尉遲徐拉與沙州大王曹元忠書》(P. 5538a) 及阿拉伯文《薩圖克·博格拉汗的傳說》,于闐陷落的年代應在1006年。參見黃盛璋:《〈于闐文尉遲徐拉與沙州大王曹元忠書〉與西北史地問題》,《歷史地理》第3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14頁;M. F. Grenard, La légende de Satok Boghra Khan et l’histoire, Journal Asiatique Series 9, t. xv, Jan. Fév., 1900, p. 64.
[24]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1年,第88~107頁。
[25]米爾咱·馬黑麻·海答兒:《中亞蒙兀兒史——剌失德史》第1編,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5頁。
[26]吐爾遜·阿尤甫:《“喀什噶爾”語初探》,《耿世民先生70壽辰紀念文集》,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118~127頁。
[27] [元]烏古孫仲端:《北使記》,見劉祁:《歸潛志》,中華書局,1983年,第169頁。
[28]楊富學:《元代畏兀兒稅役考略》,《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第120~126頁。
[29]樊保良:《回鶻與絲綢之路》,《蘭州大學學報》1985年第4期,第19~21頁;樊保良:《中國少數(shù)民族與絲綢之路》,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9~223頁。
[30] [宋]洪皓:《松漠紀聞》卷上,《遼海叢書》第1冊,沈陽:遼沈書社,1985年,第204頁。
[31]楊富學:《回鶻文書所見高昌回鶻王國的紙鈔與鑄幣》,《中國社會經(jīng)濟史研究》1992年第1期,第8~14頁;蔣其祥:《高昌回鶻的貨幣與貨幣經(jīng)濟》,《吐魯番學研究》2000年第2期,第110~112頁。
[32]楊富學:《古代新疆實物貨幣——粗棉布》,《中國錢幣》1989年第3期,第15~17頁。
[33]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語大詞典》(現(xiàn)代維吾爾文版)第1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46頁。
[34]楊鐮:《元西域詩人群體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2頁。
[35] A. von Le Coq, 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1928, p. 24.
[36]楊富學:《回鶻文獻與回鶻文化》,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76頁。
[37] [美]卡特著,吳澤炎譯:《中國印刷術的發(fā)明和它的西傳》,商務印書館,1991年,第122頁。
[38]楊富學:《敦煌研究院藏回鶻文木活字》,《敦煌研究》1990年第2期,第34~37頁;史金波、雅森·吾守爾:《中國活字印刷術的發(fā)明和早期傳播——西夏和回鶻活字印刷術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87~91頁;彭金章、王建軍《敦煌莫高窟北區(qū)洞窟所出多種民族文字文獻和回鶻文木活字綜述》,《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第154~159頁;Yang Fuxue, Uighur Wooden Movable-Types from Dunhuang and Related Problems, 《敦煌學與中國史研究論集——紀念孫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甘肅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46~350頁。
[39]孟凡人:《略論高昌回鶻的佛教》,《新疆社會科學》1982年第1期,第68頁。
[40]王紅梅:《元代高昌回鶻語概略》,《民族語文》2001年第4期,第55~61頁。
[41] [元]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22《敕賜乞臺薩理神道碑》,《大正藏》第49冊,第727頁下。
[42] P. Zieme, 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 der Uiguren, Berlin, 1985, S. 179; [日]森安孝夫著,楊富學、黃建華譯:《敦煌出土元代回鶻文佛教徒書簡》,《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第44頁。
[43]楊富學:《回鶻僧與〈西夏文大藏經(jīng)〉的翻譯》,《敦煌吐魯番研究》第7卷,中華書局,2004年,第338~344頁。
[44] [元]慶吉祥:《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卷1“奉詔旨編修執(zhí)筆校勘譯語證義諸師名銜”。
[45]莊垣內(nèi)正弘,“ウイグル語寫本·大英博物館藏Or. 8212 (108)について”,《東洋學報》第58卷第1~2期,第01~037頁;張鐵山《回鶻文佛教文獻〈說心性經(jīng)〉譯釋》,《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與文獻論集》,遼寧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341~371頁。
[46] [元]程鉅夫:《程雪樓文集》卷9《秦國文靖公神道碑》。
[47]耿世民:《古代維吾爾語詩歌選》,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7~68頁。
[48] Geng Shimin, Qadimqi Uygurca buddhistikasar “ārya-Tārā-buddha-mātrikarim-sati-pūga-stotra” din fragmentlar, TUBA 3, 1979, pp. 295-306; 耿世民《回鶻文〈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種禮贊經(jīng)〉殘卷研究》,《民族語文》1990年,第3期,第26~31頁。
[49]百濟康義、小田壽典,“ウイグル譯八十華嚴殘簡”,《佛教文化研究所紀要》第22集,1983年,第176~205頁。
[50]《新元史》卷192《安藏傳》。
[51]《元史》卷128《阿魯渾薩里傳》。
[52]匡裕徹:《元代維吾爾政治家廉希憲》,《元史論叢》第2輯,中華書局,1983年,第241~250頁。
[53][元]黃溍:《金華黃先生文集》卷25《合剌普華神道碑》。
[54][元]孔齊:《至正直記》卷3《高昌偰氏》。
[55]《閩書》卷53《文苑志》。
[56]鄭玉:《師山先生文集》卷6《休寧縣達魯花赤也先脫因公去思碑》。
[57]尚衍斌:《元代色目人史事雜考》,《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第84~85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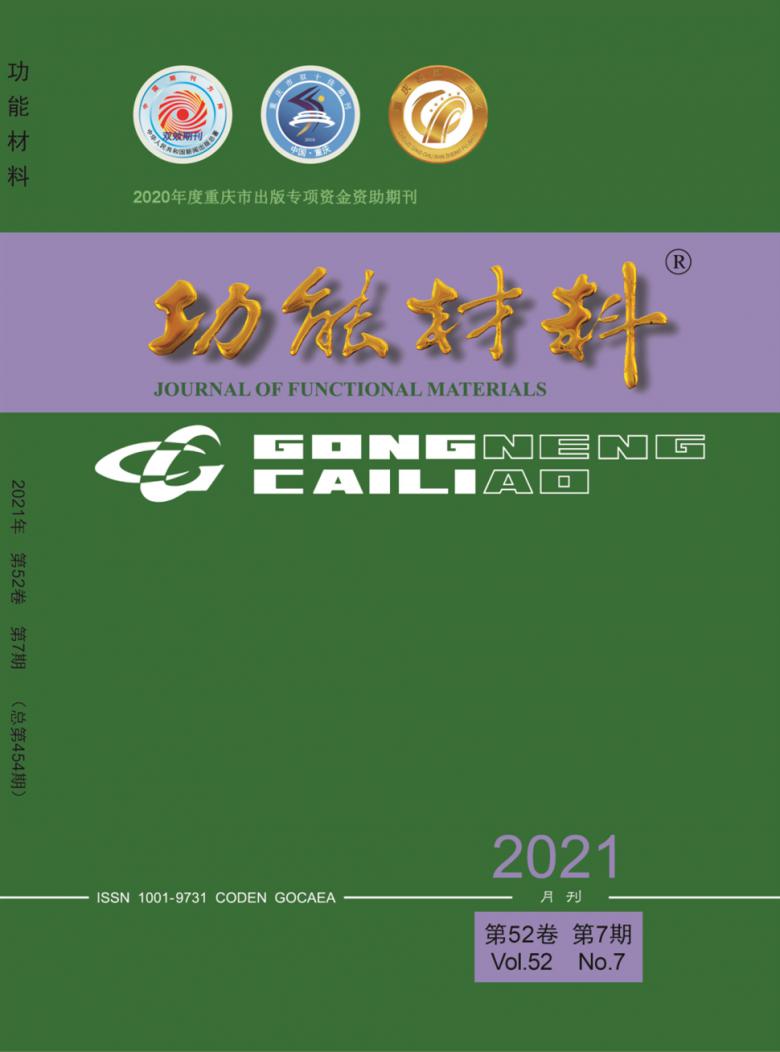
量.jpg)


界.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