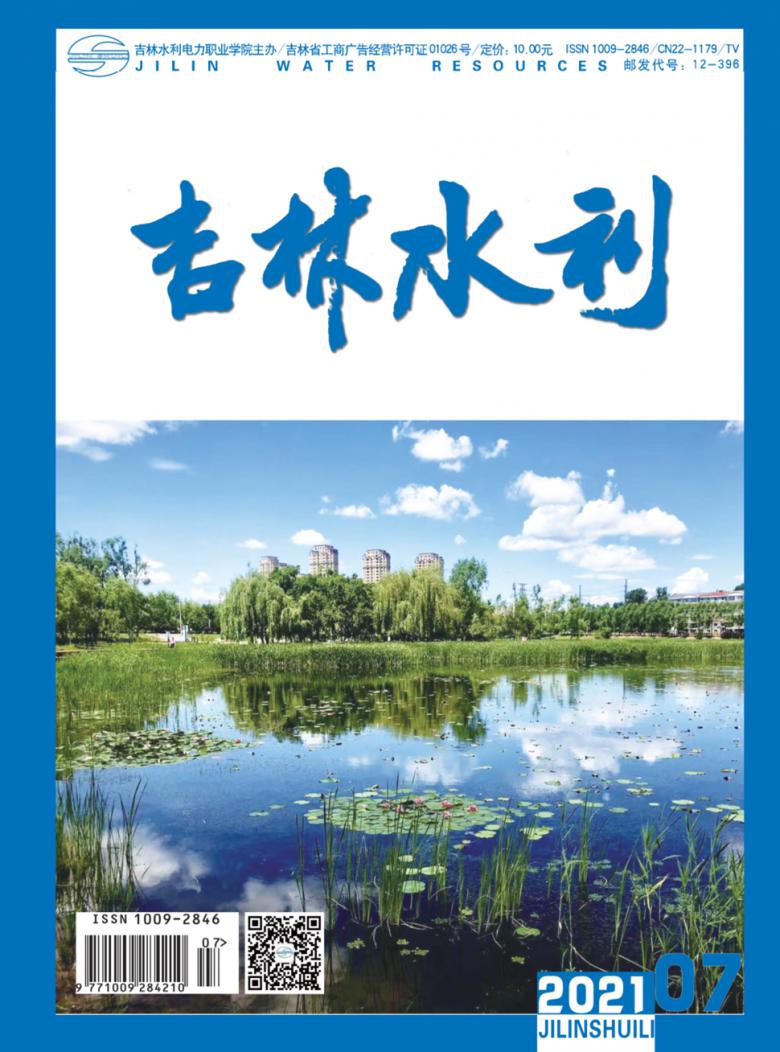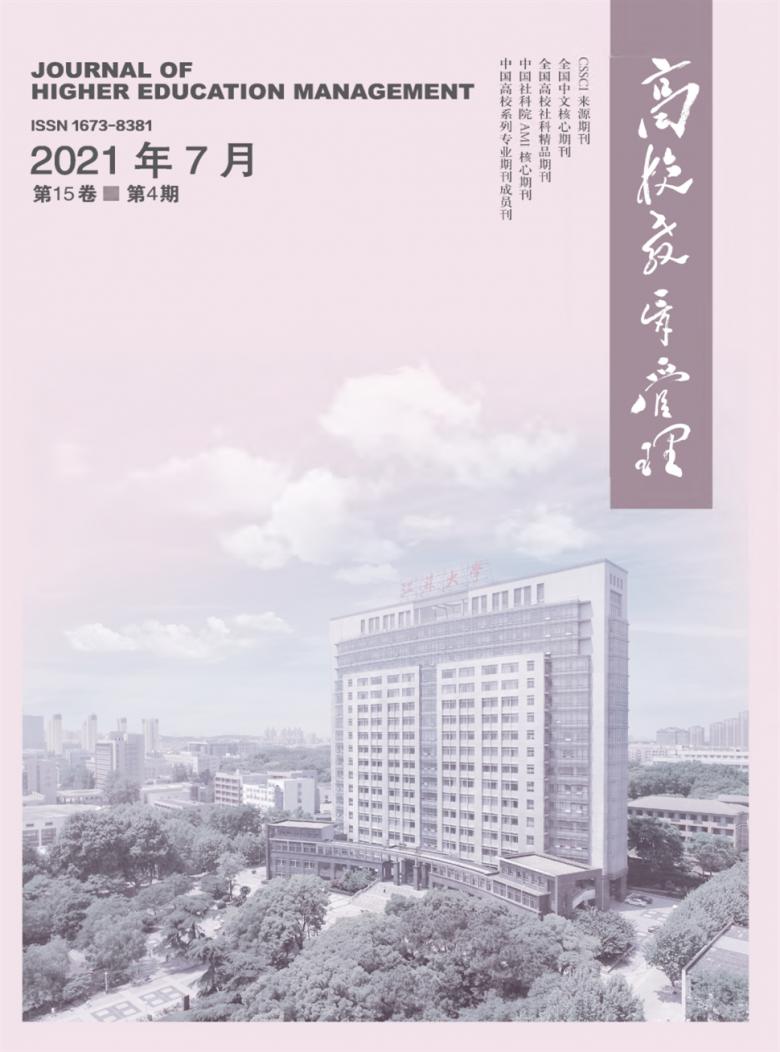遼沈戰爭與清代通俗小說的寶物崇拜
劉衛英
[摘 要] 明代國人對先進兵器的需求,有了事關國運家運的迫切性。外來火器,在明末遼沈戰場上發揮了舉國震驚的威力,也受到具體操作者素質、技術等方面的制約。清代通俗小說的描寫卻依舊承襲道教和民間秘密宗教中的法術,敘事偏重在以輝煌的結局強調寶物的威力,缺少一種戰爭工具本身的技術性展示。小農經濟下的平民心理,考慮的依舊是眼前易于操作,并不真正關注具體操作過程和操作者素質,把事情簡單化和理想化了。同時,將寶貝兵器視為百試不爽的萬能法寶,也極為形象地狀寫出人們受到時代、觀念積習的限制,在先進兵器期盼方面的局限性。
[關鍵詞] 明末戰爭;清代小說;寶物崇拜;文化反思
Abstract:The demand for advanced weapons in the Ming dynasty became urgent as to the nation’s destiny. The weapon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gave astonishing play to power in Liaoshen Wars in the Ming dynasty, but it was confined to the capability and technology of manipulater. Novels of the Qing Dynasty paid more attention to displaying the magician of the Taoism and that of folk secret religion, and emphasized the power of sacred weapons with magnificent fighting scene, but their description lacked the display of weapon’s technology. Commoners’ concern under peasant economy was more on easy operation than operation process or manipulater’s capability. Worship of sacred weapons as all-mighty power manifests commoners’ limit of the times, tradition as well as their restriction in expectation of advanced weapons.
Key words:wars in late Ming Dynasty; novels in the Qing dynasty; sacred weapon worship; cultural introspection 中國古代戰爭與兵器的關系,乃至兵器改進同小說這一文學樣式產生了較為直接的聯系,這一命題到了明末才開始明顯和突出,影響到清代小說的相關想象和文學描寫。對于這樣一個社會民俗心理與文學關系的課題,似乎探討得還很不夠,本文試就此略陳淺見。 一、明清戰爭的具體進程與兵器的改進要求 在中國古代軍事史上,明代尤其明末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國人改進兵器的視野關注外域,而且對于先進兵器的需求,有了事關國運家運的迫切性、普遍性和實際操作的措施。 史稱嘉靖八年(1529年),右都御史汪鋐言造佛郎機炮,謂之“大將軍”,發諸邊鎮。佛郎機,即今葡萄牙國名。正德末年,其船隊來到廣東。地方官員開始效法制炮,其后,“大西洋船至,復得巨炮,曰‘紅夷’。長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數十里。天啟中,錫以大將軍號,遣官祀之。……明置兵仗、軍器二局,分造火器。號將軍者自大至五。又有奪門將軍大小二樣、神機炮、襄陽炮、盞口炮、碗口炮、旋風炮、流星炮、虎尾炮、石榴炮、龍虎炮、毒火飛炮、連珠佛郎機炮、信炮、神炮、炮里炮、十眼銅炮、三出連珠炮、百出先鋒炮、鐵捧雷飛炮、火獸布地雷炮、碗口銅鐵銃、手把銅鐵銃、神銃、斬馬銃、一窩鋒神機箭銃、大中小佛郎機銅銃、佛郎機鐵銃、木廂銅銃、筋繳樺皮鐵銃、無敵手銃、鳥嘴銃、七眼銅銃、千里銃、四眼鐵槍、各號雙頭鐵槍、夾把鐵手槍、快槍以及火車、火傘、九龍筒之屬,凡數十種。正德、嘉靖間造最多。又各邊自造,自正統十四年(1449年)四川始。”[1]而實際上,歐洲先進火器的東傳,喚醒了一個軍事技術的巨大變革時代,如果上升到一定的文化層面上認識,就如研究者所言:“在明朝時期,中國原有的火器沒有準星,命中目標的準確率不大,威力也有限,而歐洲的火器已有準星,命中率大有提高,威力遠比中國的為大。因此,明朝時期西方火器及其技術之傳入中國,對中國軍事技術的提高,是個促進。當時傳入中國的西方火器,有槍,還有炮。……炮有多種,主要的是來自葡萄牙的‘佛郎機’和來自荷蘭的‘紅夷炮’兩種。”[2] 火炮這一代表性的先進兵器,是由明代對外開放的一個窗口——澳門傳入的。《熹宗實錄》卷三十三載:“(天啟三年夏四月辛未)兵部尚書董漢儒等言:‘澳夷不辭八千里之程遠赴神京,臣心竊嘉其忠順。又一一閱其火器刀劍等械,俱精利,其大炮尤稱猛烈神器,若一一仿其式樣精造,仍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分列行五卒,與賊遇于原,當應手糜爛矣。今其來者夷目七人,通事一人,傔伴十六人,應仿貢夷例賜之朝見,犒之酒食,賚以相應銀幣,用示優厚。臣等盡試其技,制造火藥擇人教演,稍俟精熟,分發山海聽輔臣收用。’上俱允行。”《熹宗實錄》卷三十四:“(天啟三年五月乙未)浙江道御史彭鯤化上言:‘……中國長技火炮為上,今澳夷遠來,已有點放之人,宜敕當事者速如式制造,預先演熟,安置關外,庶幾有備無患……’得旨:‘所奏修邊諸事著內外各衙門著實料理……’”[3] 這些外來的最新式兵器——紅衣大炮等遠距離作戰的火器,在明末遼沈戰場上,發揮了舉國震驚的威力。這里說的“遼沈”當時多稱之為“遼東”,其有廣義狹義之分:狹義的是“遼東城”,明末指的是遼陽,是明代人們從中原視點上看所說的;廣義則是以今日遼寧為中心的關外之地。而實際上。當時“遼東”的關鍵之點主要指的是今日的遼西,焦點在寧遠——今日興城至山海關一帶。天啟六年(1626年,天命十一年)正月二十三,努爾哈赤率軍進攻寧遠城,袁崇煥命家人羅立等人向城北后金大營發射西洋大炮,“殲虜數百”。據統計,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至天啟元年(1621年)僅僅三年之間,明朝發往廣寧前線的將軍炮、滅虜炮、虎蹲炮、旋風炮、威遠炮、佛郎機等共有22 144位(門),其中,天啟三年至五年,從澳門購進的26門紅夷大炮,調往山海關的就有11門,袁崇煥接受了著名兵器專家茅元儀和王喇嘛等人的意見,在城墻上建臺,制作炮車,設置在寧遠城上,這種外來火炮,設計優、瞄得準、射程遠、威力大[4]159-160。 這里的概括,其史料當主要出自《明熹宗實錄》卷十五,其記載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至天啟元年(1621年),明朝廷發往廣寧(今遼寧北鎮,即北寧市)前線的火器即有:“天威大將軍十位、神武二將軍十位、轟雷三將軍三百三十位、虎蹲炮六百位、旋風炮五百位、神炮二百位、神槍一萬四千四十桿、威遠炮十九位、涌珠炮三千二百八位、連珠炮三千七百九十三位、翼虎炮一百一十位、鐵銃五百四十位、烏銃六千四百二十門、三四眼槍六千七百九十桿、大小銅鐵佛郎機四千九十架……”還有各種戰車等軍用物資。如此投入,其在制造、運輸和訓練操作人員等方面,所帶來的整體社會效應,是不可低估的。 在袁崇煥獲得首次寧遠大捷之后,次年即明熹宗天啟七年(1627年)六月,建州女真兵又攻寧遠:“守兵出城逆擊之,連戰數十合,發火炮矢石擊之,積尸布地。四王子駐教場黃帳房,著黃衣督兵攻城,抵暮死者益眾,乃撤兵歸,終夜東行。至五鼓,營于小凌河,留精騎殿后。時十年來,盡天下之兵,未嘗敢與建州一戰,袁崇煥寧遠之捷,亦止憑城拒卻之。”[5] 對此,史家有論:“明軍獲得寧遠大捷,以上四項因素,都是相當重要的,但最關鍵的因素有兩條——指揮正確與武器先進。這個先進武器就是紅夷大炮。紅夷大炮是中國軍事史上出現的最新武器,也是明軍裝備中的最新因素。明軍首次在寧遠之戰中使用紅夷大炮,并獲得成功。明軍寧遠之戰的勝利,是袁崇煥憑堅城、用洋炮的勝利。這里有兩個因素:一是用紅夷大炮,二是使城炮結合。他從撫、清、開、鐵、沈、遼、廣、義等諸城失陷中認識到:曠野廝殺,明軍所短;憑城用炮,明軍所長。所以,‘憑堅城、用大炮’是明軍以長擊短、克敵制勝的法寶。”[4]182按,這段論述,明顯地來自早年遼寧學者的研究成果,說是后金以戰車步騎相結合的“結陣”方法來對付明軍的火器:“戰斗開始,騎兵并不出擊,往往用循車抵擋一陣,等明兵發完第一次火器,未及續發第二次,它就突然奔騎而出,如一股狂風刮過來,分開兩翼,向明兵猛沖,霎時間,就把明兵沖得七零八落。后金進入遼沈以來,多采取這種‘結陣’法,屢屢奏效。現在……它的猛烈進攻卻失去往日的效果。因為明兵憑堅城護衛,既不怕騎兵猛沖,又能躲避箭矢的攻擊。還有,它以城護炮,又以炮護城,就使明兵處于完全有利的地位。”[6]200-201可見,先進的武器,還需要與操縱它的人的素質結合,和靈活變通的恰當的戰術輔助,才能發出應有的效力。 然而,反面的教訓則更是巨大,那就是實際上不成功的火器運用,還是占據明兵遼沈戰場上的大部分情況。對此,美籍華人學者黃仁宇《中國近五百年歷史為一元論》一文也指出:“……我自己研究明末1619年的遼東戰役,內中有一個明軍指揮官放棄火器而以步兵倉促應戰。明軍分為四路,在一個弧形上展開逾一百五十英里,給努爾哈赤以各個擊破的機會。明軍用火器時,其效率之低,使滿軍膽敢以騎兵密集隊形沖入陣地,終致明軍全軍覆沒。”以下指出成因,認為這與甲午海戰等中國軍隊失利的原因是一致的:“一個國家的軍事組織,應當和它的社會結合為一,有如以骨骼、血脈、筋肉和神經系統相牽連。這就是說要使海陸軍發生效率,不僅人員裝備的供應須經常不斷,即軍事技術及軍事思想也要和支持它們之社會的水準不相上下,這樣才算是成為一個有機體。” [7]并非是兵器本身不先進,而是在戰術運用上的失誤。先進的兵器不是空的,要切實地運用到實戰中去,才能發揮兵器本身的威效。 然而,這也需要從多方面尋找原因。火炮為代表的遠距離作戰兵器,靈活機動具有實戰效驗。然而由于本身未盡完善,或還要受到下雨等天氣和外在環境的影響,尤其是具體操作者的素質、技術等方面的制約,未必火器就要勝于冷兵器。《海角遺編》第七回十八騎清兵截擊明人官船,如風似火:“船上所恃惟銃,較其來近,正要發時,也是天數,風色又不順,正下著一陣大雨,藥線俱濕,炮不得發,岸上箭似飛蝗,船上雖有弓箭,已著了忙,就有好漢,不比平地可以立住腳頭,須臾,騎鼓中軍顧三爺、伏波營總兵沈俱用鐵鞭四十余斤者,幾籌好漢,俱中箭而死矣。” 后金(清)軍仿制紅衣大炮。皇太極在寧遠、寧錦戰役失敗后,認真總結經驗,由于忌諱“夷”字,故諧音為衣,稱為“紅衣大炮”。天聰五年(1631年)正月,后金仿制的第一批紅衣大炮40門在沈陽建造而成,定名曰“天佑助威大將軍”,皇太極在八旗軍內設置新營“重軍”,是以火炮等火器裝備的新兵種。這是在遼西戰爭中得到的一個慘痛教訓之后,開始刻不容緩建造的,因此,其實戰的意義殊為巨大。 相比之下,火器運用上最初處于明顯劣勢的后金方面,卻是迅速學習,及時趕上軍事史上的這一重大變革。就在這上述40門大炮造成的半年之后,天聰五年七月末,祖大壽修筑大凌河城,尚未完工,八月初皇太極就把這四十門大炮運往大凌河戰場,用紅衣大炮轟擊大凌河城,摧毀了城上的雉堞、敵樓,而祖大壽組織的四次突圍均遭失敗。援軍吳襄大營也被佟養性所發的大炮轟擊而毀[4]120-122。 這體現了女真貴族在歷史挑戰面前及時而有效的“應戰”。與明朝拼人口實力,滿族是拼不起的。《滿文老檔》卷二十一載努爾哈赤慨嘆:“我方以民少為恨。”而諸如沈陽、遼陽等相繼落入后金之手,當地的漢族居民卻往往逃亡關內或避居海島,甚至逃往朝鮮。《滿文老檔》卷二十四載錄努爾哈赤在天命六年給朝鮮國王書信中就說:“聞吾所獲遼東之人,多往爾處。”因此,在人力上后金是大大遜于明朝的,其出動的兵力也不是以人多取勝,如天啟六年(天命十一年)正月努爾哈赤親率諸貝勒統八旗大軍進攻寧遠,許多研究者根據袁崇煥回答努爾哈赤的話,是十三萬,而據專家仔細考證,不過五六萬人,但已經是“傾注全力”了[6]195-197。其采取了很多辦法,然而,改進戰爭工具的迫切性,卻是首要和直接的。 二、火器崇拜及憧憬在清代小說中的多重藝術表現 文學是現實的折光反映,也往往曲折地折射出一定的社會心理。清代敘事文學尤其是通俗小說,對于戰爭武器及其效果的刻畫,集中體現了清初以降人們對于先進武器的重視、憧憬、期盼等民俗心理。 首先,也不排除一定程度上的寫實。如清代七峰樵道人小說《海角遺編》第二回就描寫了揚州已破,鎮江遭到進攻首先從炮擊開始:“清兵列陣于半江,發大炮直打到北岸,于是百姓家家戶戶拈香頂祝,望其死守……”(第686頁)小說第四十九回又寫清兵進攻江陰:“豫王大怒,特調貝勒王統大兵,又將江船裝載火藥、銃炮無數,期在必克。一到,……把城池圍得鐵桶,四面俱布置大炮,于廿一日子時攻城,城上亦將銃箭打下,自子時至辰時,百里內外惟聞炮聲如萬雷俱發,兩邊人馬死傷無數……城內火藥及長兵已竭,城上人立腳不住,憑外邊火炮打到,午后城垣俱已傾塌,四面鼓噪,一涌上城……”[8]可見,到這時清兵已迅速學習了明兵遼沈戰場上的長處,重視火器的運用,而且在火炮裝備上勝過明兵和地方武裝,因為惶惶不可終日的南明王朝已顧不上發展兵器了。 其次,作為平民意識表現的清代通俗小說,是現實和民俗期盼的折光反映,其所描寫的未必就與戰爭實踐中的兵器同步,更多的還依舊承襲著道教和民間秘密宗教中的法術。當然這也離不開明末清初戰爭的震撼和刺激,但是小農經濟條件下的平民心理,考慮的依舊是眼前的易于操作,當下見效。于是,火器描寫在小說中,由神怪題材轉移到歷史演義的神怪式狀寫刻畫上。即使神怪大隊人馬作戰,展示的卻只是單兵作戰的近景場面。 《說唐三傳》第十二回寫蘇寶同“背上插一個葫蘆,他把葫蘆蓋開了,口內念動真言,飛出兩口柳葉刀,長有三寸,闊如蒜葉,倒有一丈青光簸滿”,將尉遲兄弟亂刀砍死。第二十七回寫番后蘇錦蓮的葫蘆能放出無數火鵲,把周青等八個總兵燒得焦頭爛額,一萬兵折了八千。第三十二回寫朱頂仙的紅葫蘆打開蓋,“放出無數烈火,頃刻之間,滿陣大火。兵馬三千,偏將十員,俱皆燒死。只有薛丁山陷在陣中,幸得身上穿著天王甲,縱有烈火不能上身。”第三十三回寫仙人謝應登解下葫蘆,“揭開水晶蓋,放出雪白一道亮光,變成四條白龍,張牙舞爪,頓見滿天烏云,落下傾盆大雨,立刻將烈火消滅。”第三十六回寫扭頭祖師的兩個葫蘆,一個藏北海之水,一個藏南山之火,名為水火葫蘆。第四十六回寫樊梨花揭開葫蘆蓋子,放出無數火鴉,把楊藩的陰兵燒得無影無蹤。第六十九回寫謝應登仙翁把葫蘆供在桌上,請寶貝轉身,“只見一道紅光,從葫蘆里飛出,變成剪刀,雙翅奔來,野熊(仙人)一見大驚,轉瞬頭已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