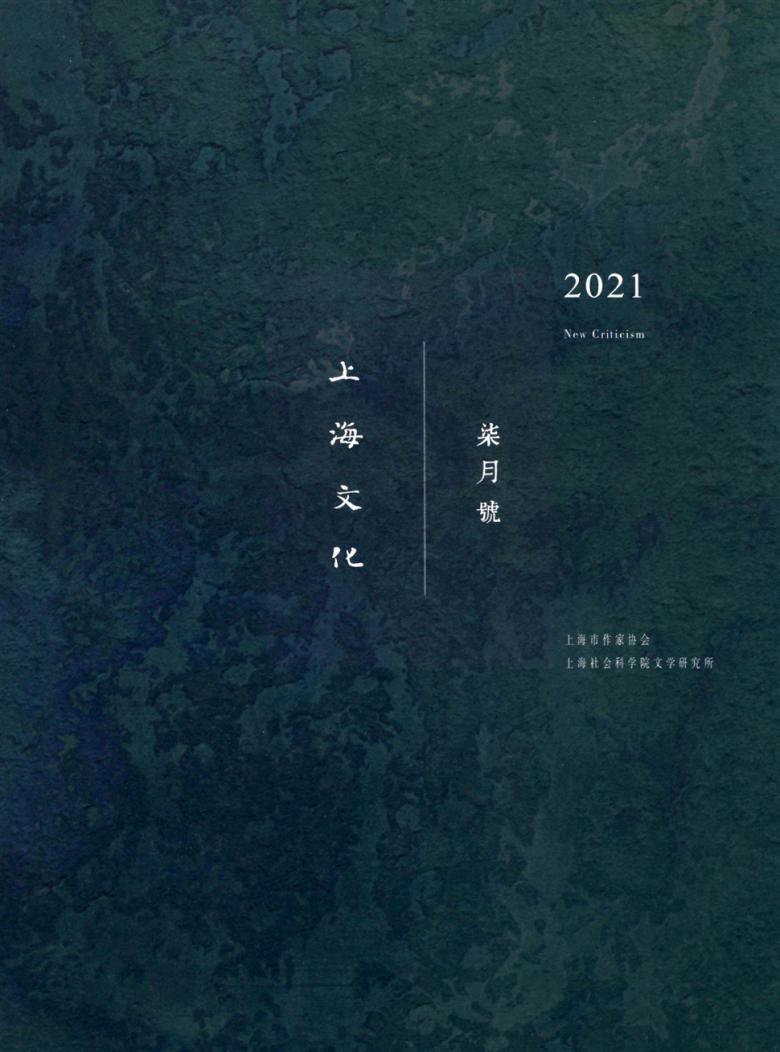民國初年法律沖突中的定婚問題
汪雄濤
【摘要】民初大理院在新舊法律沖突中具有明顯的西化傾向,其對“舊法”的保留并非是出于立場的折衷,而是由于它們正好契合了“新法”的法律原則。大理院在法律移植主觀立場下的作為卻昭示出中西法意共通的客觀事實。傳統法律對中西共有法則的表達提醒我們:對于轉型中的中國法律而言,挖掘傳統規則中的合理性因素可能比進行法律移植更為重要。
【英文摘要】The supreme judicial organ held to westernization when confliction arose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western law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But, traditional rules were still kept partly, because they were accorded with western law, and that the supreme judicial organ compromised to Li and reality reasons was more unimportant. The fact of common principles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western law suggested that researching the reasonable ingredient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ranslating western law extremely to leg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關鍵詞】法律沖突;定婚;解釋例;民初;大理院
【正文】
在清末修律的浪潮中,西方法制被大規模的引進,由此開啟了中國法律轉型的進程。如果我們對這一法律移植的過程采取與當事者同樣的視角,則我們的研究很難具有反思意識。本文擬對民初大理院處理新舊法律沖突的法律解釋過程進行解析,[1]希望能夠超越以往法律移植的理論模式,對大理院處理中西法律沖突的解釋邏輯及其背后的根由進行重新認識。
一、民初的司法背景與大理院解釋例
民國元年(1912年),參議院并未批準援用參酌西方法制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而是確定“嗣后凡有關民事案件,應仍照前清現行律中規定各條辦理”,[2]即適用所謂的“現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現行律”即《大清現行刑律》,它是清末修律過程中的一部過渡法,只是對《大清刑律》作了一些技術上的處理,并未改變“舊法”的立法精神。[3]民初的中國社會,“在西潮的沖擊下,一方面,法律制度既早在新舊嬗蛻的時期中,整個司法界的人員結構已流動變遷;而在他方面,社會種種制度與人們思想,又方在劇烈的發酵時期內。”[4]可以說,民初新舊法律的沖突已不可避免,只是一部民事“舊”法在“新”時期的援用,更加凸顯了此種法律沖突。
在政治紊亂的民國初年,立法機關很少在實際意義上存在,更遑論有效地發揮作用,惟有“司法機關比較特殊,從上到下的聯系相當緊密,直接受到政潮的影響很小”。[5]所以,盡管民初法律沖突的處理在立法上不能有效地進行,仍可依賴于司法機制。民國之初,大理院為全國最高審判機關,“院長有權對于統一解釋法令作出必應的處置”。[6]于是,大理院因法律解釋之責首當其沖地面對實際社會生活中發生的法律沖突問題。由于1928-1929年仿照德國民法典的正式民法頒布后,民國時期的法律沖突又呈現出不同的特點,本文僅把討論的時間限定在民初,即1912-1927年。
在當時的新舊法律沖突中,最為典型的是婚姻領域。因為傳統律條和習俗在婚姻領域的影響非常堅韌,本土色彩濃厚的定婚制度尤其如此。在中西法律交匯的當口,法律沖突在定婚制度中的表現值得我們深究。民國時期的解釋例反映了當時法律生活的生動場景,材料保留也相當完整,但是到目前為止,學術界對它的研究仍然十分有限。[7]民國時代的法律家郭衛曾將1912-1946年所有的解釋例進行匯編,其中1912-1927年的解釋例編為《大理院解釋例全文》(全一冊),收錄民國元年到民國十六年的大理院全部解釋例(惟缺漏統字第1888號),由統字第1號至統字第2012號止。[8]“現行律”雖然是一部舊律,但的確是當時辦理民事案件的法律淵源。下面以“現行律”為,通過分析大理院眾推事對其的遵循或背離,來觀察民初司法當局對新舊法律沖突(或曰中西法律沖突)的立場,以及大理院解釋立場背后的理論意義。
二、解釋例中的定婚問題
大理院涉及定婚問題的解釋例,大致可分為婚約、犯奸盜悔婚、無故悔婚、患疾悔婚和再許他人五個問題,下文將對它們進行分類解析。[9]
(一)婚約問題
關于婚約問題,“現行律”并無明確規定。依照“現行律”《男女婚姻》條:“若許嫁女已報婚書,及有私約,(謂先已知夫身殘疾、老幼、庶出之類。)而輒悔者,(女家主婚人)處五等罰;(其女歸本夫。)雖無婚書,但曾受聘財者,亦是。”[10]僅就律文觀之,婚書和聘財具有法律約束力,不得輒悔;律文并未明言凡結婚者須先定婚。然而,結婚在儒家禮義中須遵循“六禮”始能算完備,至少必須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11]否則便“名不正,言不順”。而“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就是定婚的核心內容,其最基本的表現形式就是婚書和聘財。
應該說,在民國以前,關于婚約的問題并無疑義。惟民國以后,西風東漸,婚約似乎成了“不合時宜”的產物。統字第1353號解釋例有案:某男走失多年,其未婚之妻后來為了避亂,移住其家近十年,除所住房屋外,衣食皆由母家供給。未婚夫無父母,與弟早分炊,臨走時口頭囑托他人代管家產。該女不愿改嫁,盼未婚夫歸家成婚或為其守志立嗣,請求兼管遺產被拒絕而涉訴。大理院答復:其既定有正式婚約,移住夫家后又愿為守志之婦,自應準其為夫擇繼,并代夫或其嗣子保管遺產。[12]又有統字第1900號解釋例也稱:“民訴條例所稱‘婚姻’應包括婚約在內。”[13]很明顯,這兩條解釋例是依照“現行律”所作的歷史解釋。因為在儒家禮義中,定婚(或婚約)當然屬于婚姻的范疇,而且結婚必須先定婚。這是無須明言的題中之義,所以律文沒有言明。此外,統字第1357號解釋例中,大理院復司法部有關結婚法律:婚姻須先有定婚契約(但以妾改正為妻者不在此限),定婚以交換婚書或依禮交納聘財為要件,但婚書與聘財并不拘形式及種類。[14]這除了對婚約的法律地位予以明確外,還賦予相關婚俗以廣泛的生存空間和法律效力。
(二)犯奸盜悔婚問題
“現行律”禁止悔婚,但規定:“其未成婚男女,有犯奸盜者,(男子有犯,聽女別嫁。女子有犯,聽男別娶。如定婚未曾過門私下奸通,男女各處十等罰,免其離異。)不用此律。”[15]很明顯,犯奸盜悔婚,律有明文,本無疑義,也屬民國時代的“新問題”。
解釋例所涉案情,也基本在律文規定的范圍之內。比如,統字第483號解釋例:有未成婚男子犯竊盜被處刑,女家悔婚另嫁被訴,問應如何辦理。大理院答復:現行律“男女婚姻”條本有禁止悔婚明文,但未成婚男子犯奸盜聽女別嫁。此案應準許悔婚。[16]很明顯,第483號解釋例依據“現行律”直接適用。又有統字第1744號解釋例:未婚男子犯殺人罪被處徒刑,女方因刑期極長不能久待,請求解除婚約,問是否合法。大理院答復:現行律載,未成婚男女犯奸盜者,男子有犯聽女別嫁,女子有犯聽男別娶;又期約五年無過不娶及夫逃亡三年不還者,聽經官給照別行改嫁。凡有破廉恥之罪與奸盜相似或被處刑三年以上依類推解釋,均應許一造請求解除婚約。[17]此案中雖是未婚男子犯罪,但并非奸盜,而是殺人罪,“現行律”并無直接條款可以適用。從解釋例來看,大理院并沒有直接依照犯奸盜律文類推,而是將犯殺人罪并刑期極長兩種因素都考慮進來,犯殺人罪比照犯奸盜,緊扣該條之立法精神——“破廉恥”,將刑期極長比照定婚男子過期不娶和夫逃亡三年不還,也甚符合“現行律”救濟受不實夫妻名分拖累之女子的立法本意。
(三)無故悔婚問題
無故悔婚,“現行律”也有明文:“若許嫁女已報婚書,及有私約,(謂先已知夫身殘疾、老幼、庶養之類。)而輒悔者,(女家主婚人)處五等罰;(其女歸本夫。)雖無婚書但曾受聘財者,亦是。”[18]女子定婚而悔,除女家主婚人受刑罰之外,仍要強制結婚——“其女歸本夫”。
統字第510號解釋例涉及定婚之女以死抗婚,請求裁決。大理院答復:既定婚則有結婚之義務,惟外國法理認為此種義務不能強制履行,即使強制執行亦未必能達判決之目的,我國國情雖有不同而事理則不無一致。現行律婚姻條雖然有效但刑罰條文已經失效,所以只能和平勸諭,別無他法。[19]統字第723號解釋例也表示,無故悔婚雖然不法,但婚姻不得強制執行。[20]這兩條解釋例所反映的問題依當時當然的民事規則——“現行律民事有效部分”,明顯有法可循。大理院在處理此案時,一方面確認定婚便有“結婚之義務”,另一方面卻援引外國法理認為此種義務“不能強制履行”。
又有統字第1934號解釋例:未婚夫以聘妻之父為被告(聲明不告聘妻),以婚約成立為理由訴令被告履行婚約,高等法院請示是否準理。大理院答復可以審理。[21]此解釋例問及聘妻之父可否為履行婚約之訴的被告,這大致包含三個問題:甲、聘妻之父可否為被告;乙、履行婚約之責任人是否在聘妻之父;丙、履行婚約可否被訴。關于甲問題,告聘妻之父屬儒家之干名犯義,今大理院準許以聘妻之父為被告,乃有以西方平等之風修正儒家“尊尊”之意。再說乙問題,“現行律”《男女婚姻》條規定,如果無故悔婚,女家主婚人要受責罰,由此而論,此案中聘妻之父負有履行婚姻之責任。再說丙問題,履行婚約可否被訴在古代似乎不成其為問題,一是因悔婚涉訴并不鮮見,且律有明文;二是因為古代婚姻履行可強制執行,訴訟可以有補于實際。但是民國以來,大理院已經確認定婚雖有結婚之義務,但婚姻履行不可強制執行。那么,此時(民國十四年)是否仍然可訴?大理院仍準許審理。這其中的邏輯應該是聘妻之父負有履行婚約之義務,雖婚姻履行不能強制執行,但其應當為此承擔民事責任。
(四)患疾悔婚問題
患疾悔婚,“現行律”《男女婚姻》條有文:“凡男女定婚之初,若(或)有殘(或廢)、疾(病)、老、幼、庶出、過房(同宗)、乞養(異姓)者。務要兩家明白通知,各從所愿,(不愿即止,愿者同媒妁)寫立婚書,依禮聘嫁。”[22]同時亦有:“若為婚而女家枉冒者,(主婚人)處八等罰,(謂如女殘疾,卻令姊妹相見,后卻以殘疾女成婚之類。)追還財禮。男家枉冒者,加一等,(謂如與親男定婚,卻與義男成婚。又如男有殘疾,卻令兄弟枉冒相見,后卻以殘疾男成婚之類。)不追財禮。未成婚者,仍依原定。(所枉冒相見之無疾兄弟、姊妹及親生子為婚,如枉冒相見男女先已聘許他人,或已經配有家室者,不在仍依原定之限。)已成婚者,離異。”[23]根據律文可知,定婚時若男女患疾必須明白通知,各從所愿,隱瞞實情枉冒為婚,應予離異。但對定婚后患疾并無規定。
先說定婚時患疾。統字第232號解釋例,某男系天閹,某女不知與其結婚,發現后得請離異否。大理院答復:依現行律男女定婚,若有殘疾務必明白通知,枉冒已成婚者,應準離異。[24]類似的解釋例還有一條,統字第1031號解釋例,定婚后,得知男為天閹,女方欲悔婚。大理院答復:此情形為殘廢,按現行律“男女婚姻”各條辦理。[25]這兩條解釋例皆是一方在定婚時隱瞞患疾事實,大理院依照“現行律”進行處理。
定婚后患疾的解釋例有三條。統字第588號解釋例問及:定婚后,女子患癲癇屢醫不治,未婚夫能否據以撤銷婚約。大理院答復:查癲癇程度如系重大可撤銷。[26]另有統字第1248號解釋例,提請解釋者二:一是“現行律”《男女婚姻》條載,“若許嫁女已報婚書及有私約而輒悔者,其女歸本服”,文中“及”作“并”字解抑作“或”字解。二是定婚后若一方出現殘疾是否允許悔婚。大理院答復:查定婚需憑媒妁,寫立婚書或依禮收受聘財始為有效,不得僅有私約。律文所言私約是指對于特別事項之約定而言,即殘疾老幼庶養之類須特別告之,經雙方合意并立婚書或受聘財之后不許翻悔。若事故在前,定婚時未經特別告知經其同意,則雖已立婚書交聘財并已成婚亦準撤銷;若定婚后成婚前一造身體確已發生重大變故,應令其再行通知,如有不愿應準解除婚約;若已成婚則應適用一般無效撤銷及離婚之法則。[27]類似的解釋例還有統字第1584號解釋例:定婚后,男患瘋癲程度頗重,并未通知相對人,相對人聞知后將女另許被訴。大理院答復:查男女一造于定婚后若罹殘疾,當各從相對人所愿,不得強令繼續。來函罹疾一造既違背通知之義務,自不能以他造未經聲明解除仍請履行婚約而禁其別字。[28]
以上三條解釋例都涉及定婚后患疾的問題,此種情形“現行律”并無明確規定。大理院認為若定婚后成婚前一造身體確已發生重大變故,應令其再行通知,如有不愿應準解除婚約;若已成婚則應適用一般無效撤銷及離婚之法則。這種解釋背后的邏輯應當是體察“現行律”相關律文的立法本意,認為是否愿意同已知患疾之人為婚應尊重男女兩家的意愿。因此,即使定婚后患疾,亦應與定婚之前相同,使對方明白易知。大理院引入西方法學話語,以“通知之義務”表述此種行為,相當貼切。
(五)再許他人問題
再許他人,“現行律”有明文規定:“若再許他人,未成婚者,(女家主婚人)處七等罰;已成婚者處八等罰。后定娶者(男家)知情,(主婚人)與(女家)同罪,財禮入官;不知者,不坐,追還財禮。(給后定娶之人。)女歸前夫。前夫不愿者,倍追財禮給還,其女仍從后夫。男家悔(而再聘)者,罪亦如之,(仍令娶前女,后聘聽其別嫁。)不追財禮。”[29]由此看來,再許他人也本不成為問題。
有關再許他人的解釋例共有五條,其中有兩條涉及搶婚。比如統字第471號解釋例:一女兩聘,男方率眾搶回完娶,他日該女之父搶女未果,為泄憤率眾燒毀柴薪被訴。大理院答復:男方搶婚不得謂無罪,以略誘論。女家之父僅負民事責任。[30]又有統字第906號解釋例,某童養媳不堪虐待而逃,未婚夫家長自愿退婚。該女改聘待嫁之際,前夫歸家反對其父先前退婚主張而搶婚,后夫聞訊也退婚,問前婚是否有效。大理院答復:子若成年,其父母之退婚未得其同意者,其退婚不為有效。搶婚雖有干禁例,但依律尚難據為撤銷婚約之原因;若有強奸行為,應準離異。[31]這兩條解釋例,前一條解釋例并未討論搶婚對婚姻效力的影響,后一條解釋例則認為搶婚雖有干禁例,“但依律尚難據為撤銷婚約之原因”。很明顯,這一解釋是嚴格依照現行律作出的。
再來看其余三條有關再許他人的解釋例。統字第914號,某人外出,其童養之妻被另聘他人,已成婚十月,前夫歸家后控訴到案。由于前夫堅持追還完聚,而該婦成婚既久,恐強制執行有意外之虞,問如何處斷。大理院答復:女子再許他人,按律應歸前夫。然該女愿歸后夫,因婚姻案件不能強制執行,若勸諭前夫不成,可倍追財禮,令女從后夫。[32]另有統字第986號,某父悔婚,敗訴后為聘財將女另嫁,是否構成欺詐罪,維持前婚約之判決是否有效。大理院答復:父悔婚將女另嫁,雖志在得財,但不得為詐欺罪;婚姻案件雖不得強制執行,但效力尤在。受確定判決之人本得對于違背判決另定之婚約,請求撤銷或另求賠償以代原約之履行。如果提起撤銷重定婚約之訴,審判衙門可適用現行律“前夫不愿者,倍追財禮給還,其女歸后夫”條妥善辦理。[33]還有統字第1188號,祖父將孫女兩聘,先聘之夫兼祧三房已娶兩房,問如何處斷。大理院答復:先聘之夫既不能重為婚姻,應準撤銷,將女斷歸后夫,其給付之聘金依不法給付原則不能請求返還。若女初愿為妾,可認為前約為聘妾之約并非定婚,尚屬有效;若后聘之婚并未征得該女同意,亦準其撤銷。[34]
第1188號解釋例雖涉及再許他人,但先聘之夫兼祧三房已娶兩房,大理院以不能重為婚姻為由否定其定婚效力,同時認為后聘之婚未經該女自愿亦可撤銷。同樣,第914號和第986號解釋例也依據“現行律”認為,再許他人,女歸前夫。但是,按照西法認為婚姻案件不能強制執行,惟有勸諭前夫依現行律追償,只是后例解釋更為詳細。大理院在第986號解釋例的處理中,認可了“婚姻案件不能強制執行”的西方法理,在這個問題上修正了“現行律”的立場。大理院沿著西方法的邏輯,認為該案件雖不能強制執行,但是判決依然具有效力,“受確定判決之人,本得對于違背判決另定之婚約請求撤銷,或另求賠償以代原約履行”。前夫可以請求撤銷后婚,也可以另求賠償以代原約履,這實際上是“現行律”對再許他人問題的處理。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大致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五類定婚問題中,“現行律”除了對婚約問題無需規定,且對犯疾悔婚中定婚后犯疾這一情形并未明確之外,對于其余問題基本上都有法律明文。大理院在作出解釋的過程中,不僅承認婚約的效力,而且對各類悔婚問題都依照“現行律”予以禁止,惟依據西方法理認為婚姻義務“不能強制履行”。
三、會通中西——立場折衷還是法意使然?
前文梳理了有關定婚問題的所有解釋例,對大理院如何處理定婚有了基本的認識。在此基礎上,本文將進一步描述大理院面對中西法律沖突時的基本立場,并試圖對大理院處理中西法律沖突背后的根由進行重新認識。
先看大理院的基本立場。如前所述,本文所涉定婚問題中,“現行律” 除了對婚約問題無需規定,且對犯疾悔婚中定婚后犯疾這一情形并未明確之外,對于其余問題基本上都有明確規定。既然這些問題大多在傳統禮法上并無疑義,卻仍然被提請解釋,大理院也并沒有駁回,這本身就說明傳統禮法在民國建立以后遭到了司法階層的普遍質疑。在大理院的解釋過程中,西方法被大量的接引,這主要表現在兩個層面:其一,在用語方面,“義務”、“強制履行”、“不法給付”、“無效撤銷”等西方法學術語被陸續引入,逐漸替代傳統判語,顯示出西方法滲透的明顯表征。其二,西方法的原則被直接引入作為大理院解釋的理論前提。在處理悔婚問題時大理院解釋說,既定婚則有“結婚之義務”,惟外國法理認為此種義務“不能強制履行”。這條西方法律原則成為處理傳統定婚案件的重要法律依據。不難想象,在革舊鼎新的民國初年,中國舊法早已成為眾矢之的,而大理院諸君大多游學國外,浸潤西法,站在時代潮流的當口,他們以締造新法的熱忱,引進西方法的術語和原則改造中國傳統禮法的行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35]
雖然大理院力圖用新法改造舊法,但是,大理院在法律解釋的過程中實際上保留了大部分傳統禮法。在無故悔婚和再許他人的問題上,大理院認為“現行律”有禁止悔婚明文,認為既定婚則有結婚之義務;在犯奸盜悔婚問題上,大理院依照“現行律”準許犯奸盜的相對方悔婚;在患疾悔婚問題上,大理院依照“現行律”明白通知,各從所愿的法意,準許隱瞞患疾的相對方離異。雖然在悔婚問題上,大理院始終堅持婚姻案件不能強制執行的西法原則,但在個案中也明確表示原約“效力尤在”,“受確定判決之人,本得對于違背判決另定之婚約請求撤銷,或另求賠償以代原約履行”。可以說,在定婚問題上,大理院的處理與現行律的規定差別不大。
一方面,西方的法律術語和法律原則廣泛滲透到大理院的解釋之中。而另一方面,大理院處理定婚問題時卻保留了大部分舊法。為何會如此?當我們回頭檢視與大理院處理結果基本一致的“現行律”條文,或許會趨近事實本身。“現行律”《男女婚姻》條有文:“凡男女定婚之初,若(或)有殘(或廢)、疾(病)、老幼、庶出、過房(同宗)、乞養(異姓)者,務要兩家明白通知,各從所愿,(不愿即止,愿者同媒妁)寫立婚書,依禮聘嫁。若許嫁女已報婚書及有私約(謂先已知夫身殘疾、老幼、庶養之類)而輒悔者,(女家主婚人)處五等罰,(其女歸本夫);雖無婚書但受聘財者,亦是。”“若再許他人,未成婚者,(女家主婚人)處七等罰;已成婚者處八等罰。后定娶者(男家)知情,(主婚人)與(女家)同罪,財禮入官;不知者,不坐,追還財禮。(給后定娶之人。)女歸前夫。前夫不愿者,倍追財禮給還,其女仍從后夫。男家悔(而再聘)者,罪亦如之,(仍令娶前女,后聘聽其別嫁。)不追財禮。”“其未成婚男女有犯奸盜者,(男子有犯,聽女別嫁。女子有犯,聽男別娶。如定婚未曾過門私下奸通,男女各處十等罰,免其離異。)不用此律。”細繹律文,我們發現,在定婚之初,“現行律”奉行的原則是明白通知,各從所愿——西方法可以表述為誠實信用原則和自愿原則;對輒悔和再許他人者進行處罰,對知情而娶者財禮入官,不知者追還財禮則是出于樸素的報償觀念——西方法可以表述為過錯責任原則;對于女歸前夫而前夫不愿者,“倍追財禮給還,其女仍從后夫”——這與大理院準許另求賠償的西式處理更是如出一轍,可以理解為公平原則。如此看來,大理院在定婚問題上保留部分舊法,與其說是基于禮俗和現實而采取的立場折衷,還不如說是基于西方法而做出的價值選擇。
【注釋】
[1] 法律沖突本為國際私法上的概念,原指在國際民商事交往中,由于不同國家對同一問題的規則不同,因而產生的有關國家對同一民商事問題的法律規則之間相互沖突。但在當前的法學界中,“法律沖突”這個概念經常被用來討論同一國家內部不同規則之間的相互沖突。如蔡定劍:《法律沖突及其解決的途徑》,載《中外法學》1999年第3期;范忠信、侯猛:《法律沖突問題的法理認識》,載《江蘇社會科學》2000年第4期。本文的“法律沖突”是從中西法律整體上的異質而言的,并不意味著中西法律之間所有具體制度的對立和矛盾。另外,本文所稱“新法”指的是清末以來力圖引入的西方法;“舊法”指的是中國固有的傳統法律。“新法”、“舊法”與“西法”、“中法”意義相同,可以互換。“新”、“舊”僅指稱時間上的先后順序,并不包含價值上的優劣。
[2] 羅志淵:《近代中國法制演變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76年版,第252頁。
[3] “現行律”的舊法性質,學界一再申說,江庸先生曾一語道破:“是書僅刪繁就簡,除消除六曹舊目而外,與《大清律》根本主義無甚出入”,見謝振民:《中華民國立法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882頁。
[4] 黃源盛:《民初大理院(1912-1928)》,載《政大法學評論》第六十期, 第139頁。
[5] 錢實甫:《北洋政府時期的政治制度》,中華書局1984年版,上冊“例言”。
[6] 詳見民國四年六月公布的《修正法院編制法》第三十三條,載《大清法規大全》,“法律部”,卷4,憲政編查館輯。
[7] 目前學界尚無以解釋例為主要材料的研究,臺灣學者黃源盛先生在這方面的研究最為充分,代表成果參見《民初法律變遷與裁判(1912-1928),(臺北)政治大學法學叢書編輯委員會2000年版;引用少量解釋例為材料的研究有黃宗智:《法典 習俗與司法實踐:清代與民國的比較》,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版;盧靜儀:《民初立嗣問題的法律與裁判》,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張生:《民國初期民法的近代化——以固有法與繼受法的整合為中心》,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李衛東:《民初民法中的民事習慣與習慣法——觀念 文本和實踐》,中國知網“中國優秀博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趙曉耕、馬曉莉:《于激變中求穩實之法——民國最高法院關于女子財產繼承權的解釋例研究》,載《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05年5月。
[8] 郭氏畢業于北洋大學法科,獲哥倫比亞大學法學博士,曾任大理院推事。郭氏所編解釋例由上海法學編譯社分次出版,會文堂新記書局發行。本文所據之解釋例皆引自此《大理院解釋例全文》(民國二十一年七月版)。
[9] 文中所據之材料皆為筆者對原文的整理,但在用語上力求保持原貌。由于實際案件復雜多樣,為了分析的方便,案件分類并不遵循嚴格的邏輯,各子類可能并不構成周延的總類。
[10] 《大清現行刑律按語》,“婚姻門”,第3頁。本文所據“現行律”律文皆出自《大清現行刑律按語》,《按語》為武漢大學圖書館所藏版本,無著者、出版地和出版日期。
[11] 語出《孟子·滕文公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鉆穴隙相窺,逾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后成為中國婚姻相沿數千年之禮俗。
[12] 《大理院解釋例全文》,第195頁。
[13] 《大理院解釋例全文》,第1100頁。
[14] 《大理院解釋例全文》,第797-798頁。
[15] 同前引《大清現行刑律按語》。
[16] 《大理院解釋例全文》,第271頁。
[17] 《大理院解釋例全文》,第1007-1008頁。
[18] 同前引《大清現行刑律按語》。
[19] 《大理院解釋例全文》,第285-286頁。
[20] 《大理院解釋例全文》,第397頁。
[21] 《大理院解釋例全文》,第1123-1124頁。
[22] 見前引《大清現行刑律按語》。
[23] 同前引《大清現行刑律按語》。
[24] 《大理院解釋例全文》,第152-153頁。
[25] 《大理院解釋例全文》,第584頁。
[26] 《大理院解釋例全文》,第326頁。
[27] 《大理院解釋例全文》,第722頁。
[28] 《大理院解釋例全文》,第920-921頁。
[29] 同前引《大清現行刑律按語》。
[30] 《大理院解釋例全文》,第264-265頁。
[31] 《大理院解釋例全文》,第498-499頁。
[32] 《大理院解釋例全文》,第506-507頁。
[33] 《大理院解釋例全文》,第550-551頁。
[34] 《大理院解釋例全文》,第679-680頁。
[35] 從黃源盛先生整理的《民國大理院歷任院長及推事略歷一覽表》可以看到,在有學歷記錄的49人之中,就有38人有過留學的經歷,大理院推事的西學背景可見一斑。該表為前引黃源盛文所附,數據為筆者統計。
[36] 同前引黃宗智著,“導論”。
[37] 對馬克斯·韋伯“類型學”方法的反思,參見陳景良:《反思法律史研究中的“類型學”方法》,載《法商研究》2004年第5期。
[38] 斯格特在《農民的倫理經濟》一書中將小農經濟下農民的生存狀態描述為“水淹至頸”,即“像一個男子不得不長久地站在深至脖頸的水中,即使只是小小的風浪也可能使他溺死。”參見J·C·Scott ,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
[39] “價值合理性”是韋伯提出的經典概念,“經驗合理性”的表述則可參見李澤厚的《實用理性與樂感文化》,限于篇幅,關于“合理性”的問題另文深入討論。
[40] 關于中國以及日韓諸國在法律演進的過程中執著于法典的形式,卻忽略法意培植的現象,蘇亦工先生貼切地稱之為“得形忘意”,精彩論述詳見蘇亦工:《得形忘意:從唐律情結到民法典情結》,載《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