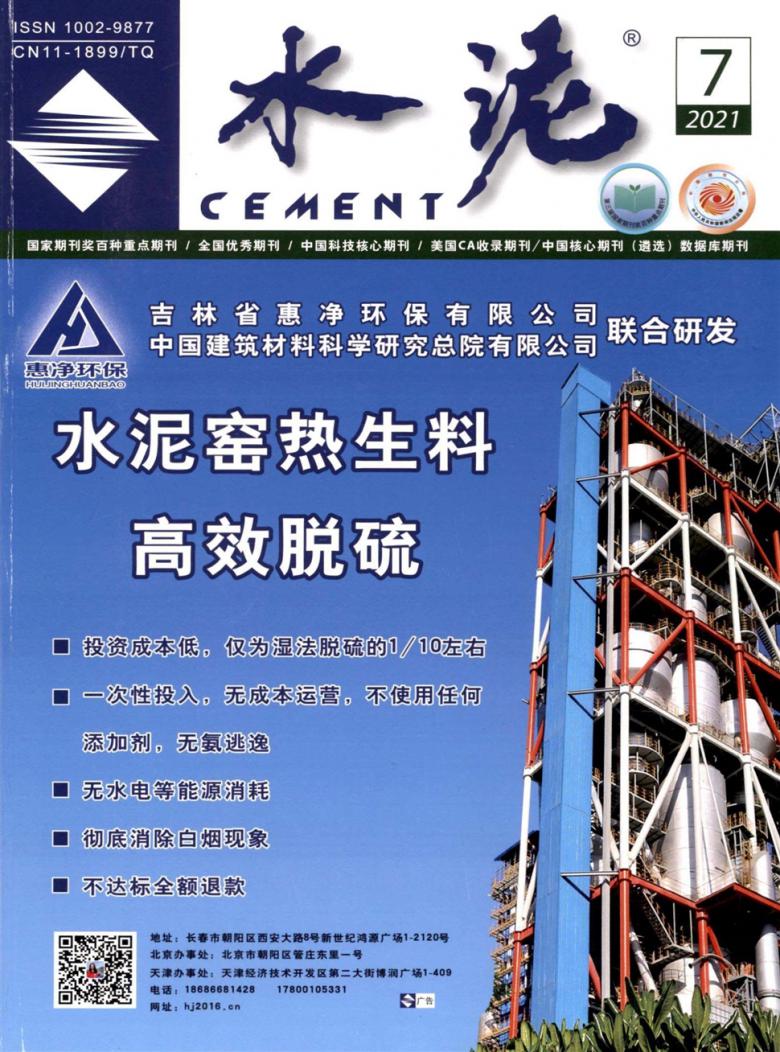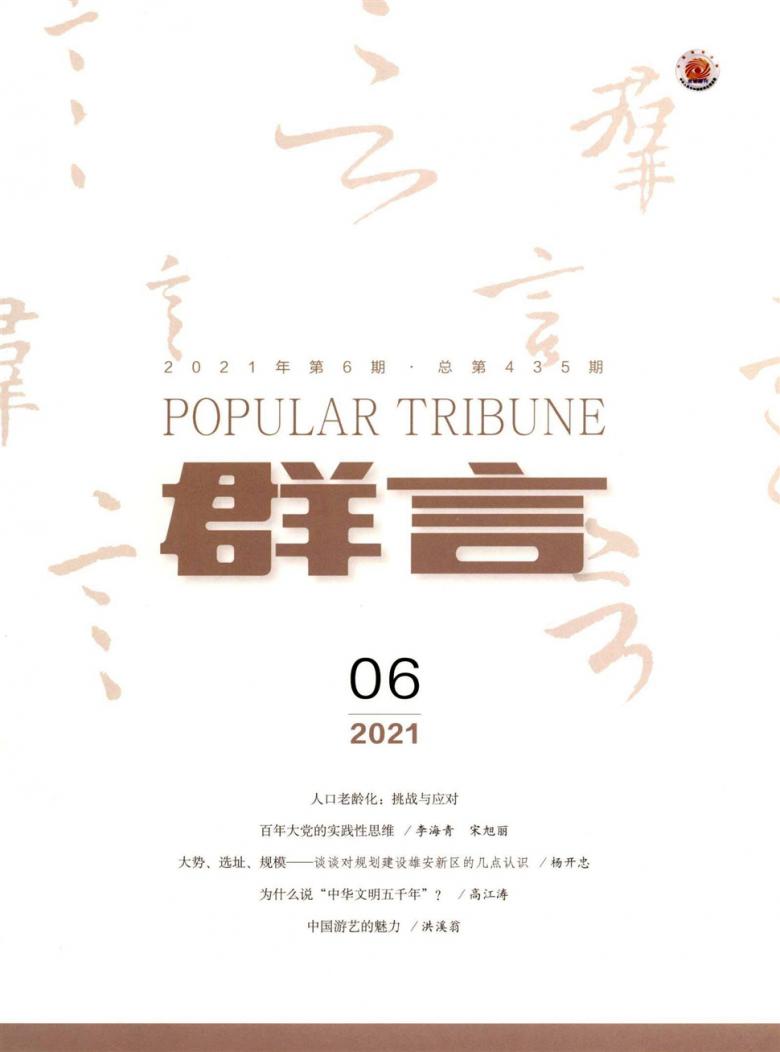關于民國《良友》畫報封面與女性身體空間的現代性建構
吳果中
論文關鍵詞: 《良友》畫報 封面 女性 身體空間 現代性
論文摘要:封面是報刊的解釋透鏡。良友》畫報封面刊登女性身體圖像,建構了上海都市文化的摩登與時尚、現代性的生活空間,從而引出了大眾傳播媒介與女性身體空間建構及媒介與社會想像性營建關系的思考。
語言和身體是大眾傳播媒介,尤其是印刷文化媒體建構女性空問的重要表達方式。大眾媒介以及圖像等視覺文化時代的到來,“身體”漸漸脫離物質性存在的單一,接受社會特定觀念的規范,而成為重要的視覺符號,體現社會的文化特征,組成社會身體的內在要素。正如人類學家道格拉斯(MarryDouglas)所認為:“社會的身體構成了感受生理的身體的方式。身體的生理的經驗總是受到社會范疇的修正,正是通過這些社會范疇,身體才得以被認知,所以,對身體的生理的經驗就含有社會的特定觀念。在兩種身體經驗之間存在著持續不斷的多種意義的交換,目的在于彼此加強。”馬克思曾說:“人按照美的規律來塑造物體。”對于身體的塑造也是如此。然而,不同時代、不同文化,甚至不同階級各有自己的審美觀念和審美趣味,因而被塑造的身體便接受了當代美的理念與標準的影響,經由大眾媒介的傳播,把關于身體的文化標準以及理想的形象話語推演成為“一個超越地區局限的跨文化的普遍觀念和范式”,形成受眾身體的“理想自我”,主導身體流行文化的符號意義。因此,大眾媒介在社會文化語境下塑造身體的同時,身體也以對當代社會文化的體驗映射社會,“正像社會本身創造著作為人的人一樣,人也創造著社會。”身體是對一個社會文化場域的反映,卻也在生產著這個社會的文化。“身體傾向于越來越成為現代人自我認同感的核心”。
女性身體是社會變遷的晴雨表,它的權力話語演變以及在社會空間的形象變化,均為觀察社會進步提供了極佳窗口。大眾媒介的介入,建構女性身體形象的標準范式,引誘更大量群體參與“理想自我”的虛擬想像。同時,從更深層面,它為現代性生活方式的解讀提供了歷史意義的文本。《良友》畫報利用圖像表現的文化優勢,自然以女性身體的圖像畫面建構女性空間以及在此空間里所生產著的身份認同、價值觀念和現代性的思想譜系。
一、民國《良友》封面:女性身體空間整體概觀的現代性含義
《良友》畫報1926年2月15日創刊于上海,至1945年1O月10日停刊,是2O世紀20至4O年代上海摩登女性展現其公共空間的理想園地。它大膽突破了中國女性不出閨閣而只有妓女照片才準許在刊物上刊登的歷史慣例,把現實真人的照片、圖像刊登在畫報的封面上或內頁的版面里,供大眾閱讀和欣賞。它將女性從一室閨閣拉向廣闊的社會人間,開拓了中上層女性的公共空間,并創造了上海消費社會里豐富多彩的都市文化。
封面對于刊物具有無可替代的文化效應。封面猶如解讀刊物的一面鏡子,宣告“雜志的個性特征、對讀者的承諾,同時也宣告了它的目標讀者”;封面又是一種促銷的工具,幫助雜志出版達到兩種生意,“把雜志賣給讀者和把讀者賣給廣告主”。因此,大眾媒介最樂于思考封面的藝術創造,以實現經濟和社會的雙贏目標。
封面刊登女性畫像是《良友》建構上海都市摩登女性公共空間的最主要手段。《良友》封面的初始狀態是:頂端是創辦人伍聯德親手創意的、“金不換”的兩個美術字“良友”,被置于版面的正中,占據近三分之一的版面空間,下面是閨閣名媛的摩登圖像,約占三分之二的版面,在“良友”兩字和美女照片之間從右至左依次刊載“每月一冊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五日出版第一期”,下行是英文注釋:THEYOUNG COMPANION,再下行是:N0.1February15,1926。美女圖像的下端標注:上海北四川路良友印刷公司印行。直至第l3期起,《良友》改變了封面的設計。封面的右端出現了白色的“雙鵝”圖,作為《良友》的符號標志和理念識別,表征追求體貼、關愛的刊物文化理念。右端第一次出現了“本期要目”,在第一時間里告知受眾關于本期的重要信息,體現了畫報的人文關懷。這種版面模式保持到第24期。從第25期始,《良友》徹底改革封面。美女圖片擴大到整個頁面,有時啟用特寫女性肖像圖片為封面。從29期起,封面用人像著色,這一來真人的姿態比較生動,二來人像閱者覺得“世上真有這個人”,否則雖畫得美麗,恐怕“人間趣味”到底不大濃厚。這樣,重彩著色、光彩逼真的摩登美女肖像占用整個版面,傳播的信息形成一股巨大的視覺沖擊力,成為大眾駐足觀看的文化娛樂“場所”,體現了其封面設計藝術的成熟。同時,《良友》封面構成要素,如刊名、日期、期號、印行地址均以中英文的雙重身份,出現在顯要位置。一方面,體現了它的受眾對象、出版發行以海外僑胞為主的影響趨勢,這在趙家璧與魯迅的對話中便可找到佐證。當魯迅問及“良友”的營業情況時,趙家璧告訴他:“這是廣東商人開的,《良友》畫報等各種畫冊,主要讀者是海外僑胞,所以業務很發達。”刊物的商業利益與受眾的群體要求催生了《良友》兩種語言的表達方式。另一方面,體現了其國際化的文化視野和現代性的思想架構。封面采用中英文標注,在中英文兩種完全不同的話語體制里,實現思維、慣習、語境的交往與融通,直入跨國界、跨文化傳播的現代性路徑。因此,從封面便可感知《良友》的國際化理念和現代性氣息,獨領時代風騷,成為中國出版園地里一朵獨特的玫瑰。
民國《良友》共辦172期,便有172張封面圖像。在172張封面圖像中,有161張女性圖像,l1張男性圖像,女性所占比例達到94.3%,男性所占比例僅5.7%。“《良友》封面,從創刊開始,一直是以年輕閨秀或著名女演員、電影女明星、女體育家等的肖像作封面的。遷港出版以后的各期中,配合戰時需要,都改為以抗日將士或與抗戰有關的婦女為封面了。”[](刪一般說來,男性封面是重大新聞事件中重要人物的圖片介紹,組成《良友》男性封面的人物是:第l31期為盧溝橋事變后視察前方陣地的蔣委員長照片;第132—135期依次為:馮玉祥副委員長近影、“中國之新軍人”、朱德將軍、李宗仁將軍、第137期的白崇禧將軍、第138期的張發奎將軍、第150期百齡壽翁馬相伯、第161期塞北的青年、第172期蔣主席畫像。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國進人全民抗戰的歷史時期,《良友》以高度的新聞敏感,及時報道這個時期的歷史狀況,因此,抗戰及其相關題材成為其從封面至內頁的刊物主題。第150期刊登百齡壽翁馬相伯的照片,蘊涵《良友》生命永駐的象征意味。《良友》停刊時過四年之后,力圖重整旗鼓,于是便出版了第172期。本期內容定位在八年抗戰的歷史總結,刊載抗日八年后的勝利成果、敵軍的受降情況等等,因而,封面便以蔣介石的畫像。為導引,突出刊物版面的信息內涵。由于封面形象具有重大的新聞價值,是與新聞事件緊密相聯的要人,也是大眾想知要知的公眾人物,盡管違背雜志封面以時尚摩登美女為文本符號信息載體的慣例,卻不因男性的登場而減少受眾。
《良友》172張封面圖像中,l44張是有名的,28張是匿名的(注:完全沒有姓氏的才被算人匿名,而標有姓的圖像,如吳女士、莫女士等均被算為有名。),匿名人數占總人數的16.3%,而有名人數占83.7%,約為匿名人數的5倍。《良友》的封面人物都是現實生活中的知名人物,統計起來,共得到119個名字,除去重復和男性的名字,女性的名字為111個,其中嚴月嫻、陳云裳、李綺年均出現三次,紫羅蘭、黃柳霜、胡蝶、羅羅少女、黎明暉、阮玲玉、胡萍、梁玉珍、白楊均兩次出現,因此,《良友》真正有名字可考的封面女郎共97個。初步探究其身份發現,體育健將或體育家2名,美術家1名,學生9名,閨閣名嬡6名,電影明星或演員占據絕大部分比例。第l期封面“胡蝶戀花圖”,刊登的是一幅套色照片——一個手持鮮花、笑靨迎人的美女,那就是后來紅極一時的電影明星胡蝶,其在《姐妹花》一片中,“一人分飾兩角,全國以至南洋各國紛紛上映,創造了總計三十四萬元的最高票房價值,單在上海就聯映了六十天,外國觀眾將之與好萊塢明星格麗泰、嘉寶相提并論。”并于1933年當選為電影皇后。第16期的封面人物黃柳霜也是電影明星,自幼在美國長大,是美國電影界有史以來最著名的中國女演員。據《申報》報道:“本埠北四川路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總經理伍聯德,于本年四月赴美,研究印刷事業,遂經好萊塢,獲遇華籍之美國電影女明星黃柳霜,備蒙招待,及問家世,始知本有戚誼,黃遂不呼之為伍先生而日叔叔,后又得其居間紹介,與名震一時之范朋克氏晤談……”本期的封面照片就是黃柳霜贈送給伍聯德的。徐志摩夫人陸小曼、電影明星王漢倫、楊依依、楊愛立、李旦旦、林楚楚、唐瑛、黎灼灼、唐雪卿、左肇芬等紛紛亮相《良友》封面。 《良友》在近2O年的漫長歷史中,其封面設計幾經變遷,體現出傳統與現代融為一體的內在架構。第2--4期、10期等圖像周邊鑲有西式花紋圖案,而相片里的封面女郎卻衣中國古典時裝,表情也是中國式的,嬌媚和做作。如第27期封面女郎,披著摩登的毛皮圍巾,腳穿流行的高跟鞋,然而,發夾盤起的發型以及額頭正中的劉海和圖片背景里的風光卻是傳統的。到第84期的封面設計,可說是徹底的現代性了。穿著西式長裙、手指經過顏色潤飾的女郎擺著舞女的姿勢,右手指向充滿未來派風格的背景畫面,1934和一只巨大的鐘,“明顯地意味著現代性”。英文標注“THEMOSTATTRACTIvE AND P0PIⅡ,AR MAGA ZINE IN CmNA”,意為:中國最流行最有吸引力的雜志。封面中英文兩種話語表達,表征刊物對現代性受眾群體、國際化空間架構以及跨文化傳播視野的合理想象,是刊物理念的現代性承載。
二、《良友》封面與摩登時尚女性空間的現代性
《良友》封面所營造的明星名媛形象,無疑為大眾提供了摩登女郎樣板。出色的才華、悅目的姿色、時尚的生活品味、高雅的藝術姿態,與其說是他們的客觀存在,不如說是《良友》精心打造出來的符號文本。《良友》利用手中的技術工具——一攝影機、著色版、光影儀,創造了源于現實真人卻高于真人的多種想象性文本。除了刊登大幅美人頭部或迷人身段以表達天生麗質的美,,《良友》還注意刊登健美流行色。如第69期是一幅手握網球拍、身穿運動裝的青春健美女士圖像,第77期是衣簡單輕便的運動裝、極富力與美的游泳健將、在當時有“美人魚”之稱的楊秀瓊女士,第86期是“春郊試馬圖”的胡蝶女士,第118期是揚帆啟航的健美女士,第139期“新時代中國女性”封面,是身穿軍裝、手持鋼槍、溫柔中蘊涵陽剛之氣的女性照片,第148期是彎弓射箭的新女性等等。《良友》營造的是一種力與健康的女性美,而:不是養在深閨、三寸金蓮的病態美,“真正的美觀,還是在康健的身體,和豐滿的肌肉。《良友》的女性審美觀念是現代性的必然產物。
《良友》畫報封面還營造了一種都市生活方式的理想狀態。從1927年開始,它便開始刊登“夢幻”女性照片或敘述女性的夢幻生活情景。如第13期封面女郎,華麗的圍巾隨意搭在右肩,左肩和胸背因西式吊帶時裝而基本裸露,背景是翩翩起舞的芭蕾舞女隊列和西式屋柱,然而,女郎的齊額劉海、腦后的發髻及其柳葉眉、朱唇粉腮的臉部妝容卻又表現出東方美女的傳統標準。第28期封面女郎,穿著大短袖時裝、帶著孔雀帽子,安然地伏案而坐,背景里是花草,猶如翩翩而至的花仙子。她們所打造的圖像文本,生產出年輕貌美、富有時尚的符號意義。打著太陽傘悠閑著的俏麗女性(第68期)、沐浴明媚春光,生一燦爛笑容的女士(第65期)、郊游的女士(第154期)、對著生日蠟燭許下心愿的女士(第162期)、母親與小孩嬉戲圖(第167期)、銀波泛棹的女士(第l71期),這都是如夢如幻的理想生活。《良友》以具體可感的圖像向受眾演示摩登女郎的美麗,“推薦一種摩登的生活方式,灌輸一種全新的價值觀念,掀動一輪又一輪的時尚潮流”。因此,封面的美麗與摩登被賦予了中產階級的符號意義,表征財富和身份在消費社會里的時尚創造。相對于文字的抽象,畫報的閱讀在輕松休閑的方式中完成,并可以滲透到不識字的大眾階層,圖片的全新含義和現代倫理價值在更廣闊的影響空間傳播。
整體看來,《良友》畫報的封面空間全面想像了“現代性”、“摩登與時尚”、“夢幻女性身體”等寓含于上海20世紀二三十年代都市文化生產場域的關鍵詞語,《良友》封面圖像對女性身體的話語表達和視覺文化再現,再次見證了大眾傳播媒介對受眾意識形態及其現代性消費空間建構的社會效用。
三、一個延伸的話題:大眾傳播媒介與女性的刻板印象
李普曼指出:“婦女刻板形象的體系可能是我們個人傳統的核心,是我們社會地位的維護。”大眾傳播媒介利用信息建構和符號意義的文化資本,生產出消費主義的權力等級差異和性別意識,表征媒介與社會的想像性營建關系。
畫報封面發揮視覺沖擊力巨大的圖像形式,以直觀的可辨認性的傳播優勢創造與廣太受眾共享的文化意義空間。《良友》畫報封面刻畫的是美麗、時尚、具有現代性消費理念的女性形象,每一張溫雅的現代女性肖像和圖像的現代性背景,都表征年輕、富有、魅人的夢幻女性形象,折射出女性對摩登都市生活的追求。后來隨抗戰主題而出現的將軍男性封面,作為會透析的文化身份,闡釋著現代性社會里刻板的性別差異。在《良友》所營造的空間中,男性是權力、戰爭的主角,而女性是消費主義和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物化、性感的消費群體,受著消費主義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規約,形成男性視野期待的“女性氣質”。應該說,《良友》將這些“夢幻”、“詩意”、“健美”的理想中的女性美視為高雅藝術的表達或時尚生活的塑造,同時預期了兩種觀看主體及其觀看模式:一方面,女性圖像提供自己的女性特質作為男性的觀看對象,盡管“他”是一位“缺席觀者”,但只要接觸《良友》等表現和消費女性圖像的媒介,“他”就存在并與之主動交流。另一方面,這種刊登時尚、摩登、健康女性照片的畫報又在培養以女性為預期的主要讀者,“提供觀看女性身體新的視角和新的象征意義”,“通過參與建構這一新的話語和視像,《良友》敏銳地捕獲3O年代有關中國女性身體的新品味和新理想”。
然而,由于男性和社會對女性的固定成見,最受大眾傳播媒介關注的不是男性,而是女性身體。“現代中國畫報中的女性身體既被建構成提供視覺享受的奇觀,又是文化消費和話語形成的場域,也是表達私人幻想、公眾焦慮、難解壓力和矛盾的文本空間”。作為追求文化理想的《良友》也未能脫離這種經營。封面上著泳裝的楊秀瓊、著馬裝的胡蝶,還有許多不知名姓的迷人女子,在《良友》“IsSheCharming?”的評價中款款登場,女性總被賦予了不同于男性的文化符碼,在提供女性美的視覺呈現和性誘惑的力量時,女性身體又被作為了商品的生產與復制,為《良友》贏得了更多的視覺青睞和發行,這也許正是大眾傳播媒介追求的終極目的。
大眾傳播媒介的信息傳播力能形成社會認知的共同體,并以文化霸權的優勢將其主體地位自然演變為社會主流權力控制意識形態的手段之一。因此,透過《良友》封面對女性圖像的表現與消費,我們勢必又會發現:《良友》進一步再生產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社會的男權意識和資本主義價值觀,從而凸顯了父權制社會的想象性建構。當然,這是探究《良友》與現代性建構視角的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