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明清浙東學(xué)術(shù)對(duì)儒家和諧文化的傳承和創(chuàng)新
佚名
論文關(guān)鍵詞 儒家和諧文化 浙東學(xué)術(shù) 王陽(yáng)明 黃宗羲 傳承和創(chuàng)新 論文內(nèi)容提要 “經(jīng)世致用”是浙東學(xué)術(shù)的基本學(xué)術(shù)精神,而追求“和諧”則是浙東學(xué)術(shù)的基本價(jià)值觀念。尤其是王守仁和黃宗羲,他們立足于自己所處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為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和諧,終身孜孜不倦地作探索:王陽(yáng)明把自己的“致良知”學(xué)說(shuō)最終歸結(jié)為“萬(wàn)物一體之仁”的思想,提出所謂“萬(wàn)物一體”、“天下一家”、“中國(guó)一人”的思想,其思想的出發(fā)點(diǎn)是試圖通過(guò)道德教化的新途徑,在多災(zāi)多難的明代社會(huì)推行和創(chuàng)新儒家的“和諧”理念。黃宗羲學(xué)說(shuō)的根雖然是儒家文化,但他在對(duì)封建專制制度的深刻反思尖銳批判中,既對(duì)儒家文化所宣揚(yáng)的社會(huì)價(jià)值觀作了全面的檢討,又著眼民生對(duì)儒家的社會(huì)學(xué)說(shuō)作了重新的設(shè)計(jì),從而形成了一個(gè)具有啟蒙意義的、試圖引導(dǎo)社會(huì)重新走向和諧的思想體系。他們的學(xué)術(shù)思想,豐富和發(fā)展了中國(guó)的和諧文化,從而也使以他們?yōu)榇淼拿髑逭銝|學(xué)術(shù)在中華民族的“和諧文化”史上具有獨(dú)特的地位。 追求、崇尚和諧,是中國(guó)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也是中國(guó)古代重要的社會(huì)、政治理念。“和諧”的思想貫穿于中國(guó)思想發(fā)展史的各個(gè)時(shí)期及儒、墨、道、法、兵等主要思想學(xué)派之中,尤其是儒家文化之中,成為中華民族普遍的信念。在中國(guó)悠久歷史中,這種信念對(duì)保持社會(huì)穩(wěn)定和發(fā)展,維護(hù)多民族國(guó)家的統(tǒng)一發(fā)揮了巨大作用。浙東學(xué)術(shù)文化作為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中的精華部分,更是包含著豐富而深刻的和諧文化的內(nèi)容,是我們今天構(gòu)建社會(huì)主義和諧社會(huì)、建設(shè)和諧文化寶貴的歷史文化資源。 從梁?jiǎn)⒊疆?dāng)代學(xué)者,都認(rèn)為經(jīng)世致用是浙東學(xué)術(shù)文化的基本精神,那么這個(gè)“經(jīng)世致用”的“用”落實(shí)在哪里?我們?nèi)粢浴昂椭C”的觀點(diǎn)來(lái)看,就可以別見(jiàn)境界:南宋以后,浙東學(xué)術(shù)走向繁榮,從楊簡(jiǎn)經(jīng)王陽(yáng)明、再?gòu)膭⒆谥芙?jīng)黃宗羲,下傳萬(wàn)斯同、全祖望、章學(xué)誠(chéng),他們經(jīng)世致用的學(xué)術(shù)雖各有所專,但都可以用追求“和諧”將他們貫通起來(lái),或是為了尋求心靈的和諧、或是為了尋求社會(huì)的和諧、或是為了尋求宇宙萬(wàn)物的和諧。可以說(shuō),“經(jīng)世致用”是浙東學(xué)術(shù)的基本學(xué)術(shù)精神,而追求“和諧”則是浙東學(xué)術(shù)的基本價(jià)值觀念。 用“和諧文化”的觀點(diǎn)來(lái)解讀浙東學(xué)術(shù)文化,可以看到浙東學(xué)術(shù)文化在傳承中華和諧文化中同樣具有豐富多彩的學(xué)術(shù)內(nèi)涵。尤其是明清時(shí)期的王守仁和黃宗羲,他們立足于自己所處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以中國(guó)歷代知識(shí)分子“在萬(wàn)民之憂樂(lè)”的道德良心,體恤民生,為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和諧,終身孜孜不倦地作探索,他們的學(xué)術(shù)思想,豐富和發(fā)展了中國(guó)的和諧文化,從而也使以他們?yōu)榇淼拿髑逭銝|學(xué)術(shù)在中華民族的“和諧文化”史上具有獨(dú)特的地位。 一、王陽(yáng)明對(duì)于儒家和諧文化的傳承和革新 以往,人們以唯物唯心的觀點(diǎn)來(lái)評(píng)判王陽(yáng)明的學(xué)術(shù)思想,將其歸之于唯心主義而加以否定。所以,陽(yáng)明心學(xué)在當(dāng)代人的視野中是變了型的。其實(shí),陽(yáng)明心學(xué)作為儒家文化在明代的重要學(xué)術(shù)文化的流派,其最大的成就在是豐富和發(fā)展中國(guó)儒家文化的“和諧文化”上。 “致良知”是陽(yáng)明心學(xué)的核心思想。王陽(yáng)明曾把自己的“致良知”學(xué)說(shuō)最終歸結(jié)為“萬(wàn)物一體之仁”的思想。而“萬(wàn)物一體之仁”是最能表現(xiàn)其學(xué)說(shuō)的儒家“和諧”文化特色的。王陽(yáng)明在其闡述“萬(wàn)物一體之仁”思想的《大學(xué)問(wèn)》中,開(kāi)篇即說(shuō): 大人者,以天地萬(wàn)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就一家,中國(guó)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① 《大學(xué)》作為儒家政治倫理學(xué)說(shuō)的一部經(jīng)典,陽(yáng)明之前的論者常以“大人之學(xué)”為解,把“大”解釋為“正”,即標(biāo)準(zhǔn)、楷模之意;“大人”即為人們的楷模。王陽(yáng)明則解《大學(xué)》的“大人”為“以天地萬(wàn)物為一體”之人,以為“大人”即圣人,圣人以萬(wàn)物為一體,天下為一家,國(guó)家為一身,而不“間形骸”、“分爾我”。他這種解釋,表達(dá)的正是儒家自孔子以來(lái)以“仁”為核心的社會(huì)“和諧”理念。王陽(yáng)明生活于社會(huì)矛盾日趨尖銳的明代中葉,提出所謂“萬(wàn)物一體”、“天下一家”、“中國(guó)一人”的思想,是儒家“大同”思想在當(dāng)時(shí)的一種新說(shuō)法,其指導(dǎo)思想的出發(fā)點(diǎn)是:試圖通過(guò)尋找道德教化的新途徑,不僅要“破山中賊”,而且更要“破心中賊”,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和諧,意欲在多災(zāi)多難的明代社會(huì)推行和創(chuàng)新儒家的“和諧”理念。 王陽(yáng)明的所謂“天地萬(wàn)物一體”之仁,就是視天地萬(wàn)物為一生命整體,將自然界的萬(wàn)物視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象愛(ài)護(hù)自己的生命一樣去愛(ài)護(hù)它,保護(hù)它,不要使它受到傷害。因?yàn)槊恳晃锒俭w現(xiàn)了天地之“生意”、“生理”,每一物都有自身的價(jià)值,因而應(yīng)當(dāng)受到尊重,受到愛(ài)護(hù)。人類自身不僅要生存,而且要使物物“各遂其生”、“各順其性”,這才是仁的真正實(shí)現(xiàn),才是“天地萬(wàn)物一體”境界。 王陽(yáng)明“萬(wàn)物一體之仁”的說(shuō)法雖然是從宋代理學(xué)家這里接受過(guò)來(lái)的,但他要把它來(lái)作為自己推進(jìn)“社會(huì)和諧”的指導(dǎo)工具,是需要對(duì)它作理論改造的,因?yàn)樗麄兯鎸?duì)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和歷史使命是大不相同的。宋儒所面對(duì)的是如何維護(hù)既定的封建等級(jí)制度的長(zhǎng)存久安,所以他們的學(xué)說(shuō)重心是在說(shuō)明統(tǒng)治者和被統(tǒng)治者如何的不同,論證社會(huì)階級(jí)分層的合理性,從而保持所謂的“社會(huì)和諧”;而王陽(yáng)明面對(duì)的則是明代社會(huì)各階層對(duì)立日趨激烈、社會(huì)動(dòng)蕩的嚴(yán)酷現(xiàn)實(shí),在這種歷史背景下他要倡導(dǎo)社會(huì)和諧,就不能把自己學(xué)說(shuō)的重點(diǎn)放在論證階層等級(jí)差距的合理性上,而是恰好相反,要竭力說(shuō)明統(tǒng)治者和被統(tǒng)治者如何的相同,從而淡化這種區(qū)隔,調(diào)和這種對(duì)立,實(shí)現(xiàn)所謂的“社會(huì)和諧”。 正因?yàn)橛猩鲜鏊f(shuō)的差別,所以,王陽(yáng)明作為中國(guó)封建社會(huì)后期最富創(chuàng)造力的思想家,針對(duì)程朱理學(xué)在維護(hù)封建“和諧”秩序上的失效,為了重建封建統(tǒng)治秩序,他對(duì)“天地萬(wàn)物一體之仁”思想作了新的詮釋,在“天人合一”、“人我合一”、“身心合一”等儒學(xué)“和”文化的基本觀念上,形成了和程朱理學(xué)絕然不同的思想學(xué)說(shuō),在傳承儒家以“仁”為核心的和諧文化中創(chuàng)建了以“致良知”為核心概念的心學(xué)理論體系。 首先,王陽(yáng)明以“致良知”來(lái)闡發(fā)體現(xiàn)“萬(wàn)物一體之仁”精神的“人我”關(guān)系,對(duì)什么是理想社會(huì)“和諧”的治理模式提出了新見(jiàn)解。 程朱理學(xué)和陽(yáng)明心學(xué)對(duì)于理想社會(huì)“人我”關(guān)系的基本看法,都是以先秦儒家的“天下為公”的“大同”思想作藍(lán)本的,但如何達(dá)到這種美好的境界呢?王陽(yáng)明和宋儒有不同的解答。 宋代理學(xué)認(rèn)為,理想社會(huì)的人際關(guān)系是這樣的: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zhǎng)其長(zhǎng);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dú)埣病莫?dú)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wú)告者也。② 他們把天地比作父母,認(rèn)為人生于天地之間,自應(yīng)把萬(wàn)民看作同胞兄弟,把萬(wàn)物視為同伴和朋友。在這樣的社會(huì)里,人人都尊長(zhǎng)慈幼,同情、愛(ài)護(hù)病苦、殘疾、鰥寡、孤獨(dú)者;人與人之間相親相愛(ài),沒(méi)有矛盾和爭(zhēng)訟。顯然,在宋儒們看來(lái),人類社會(huì)和諧的根據(jù)不在人自己身上,而在外在的“乾坤”即“天理”這里,因此,和諧的社會(huì)是依靠君主和大臣按照“天理”來(lái)精心治理的結(jié)果,所以,要實(shí)現(xiàn)太平盛世,就要“存天理、滅人欲”。 王陽(yáng)明對(duì)理想社會(huì)的“人我關(guān)系”是這樣描繪的: 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親如一家之親。其才質(zhì)之下者,則安其農(nóng)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yè),以相生相養(yǎng),而無(wú)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皋蘷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③ 在王陽(yáng)明看來(lái),天下要“親如一家”,人們能“各效其能”,雖然需要“大人”的有效統(tǒng)治,但“大人”(圣人)之所以能視天下如一家,并不是由于外在的“理”對(duì)他提出這種要求,而是他的內(nèi)心具有“仁”的本質(zhì),“大人”具有視人如己的崇高情懷和“博施濟(jì)眾”的社會(huì)責(zé)任感,是出于他的“良知”。而這樣的良知不只“大人”之心有,即使平民百姓也有這樣的良知;天下人都有良知,所以心是息息相通的。這就是“萬(wàn)物一體之仁”的根據(jù)。這樣,就在道德人格,或者說(shuō)在人倫關(guān)系的根本問(wèn)題上,縮小了圣人與平民也即統(tǒng)治者和被統(tǒng)治者的差距。從而在如何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和諧的著眼點(diǎn)上,王陽(yáng)明從宋儒的訴諸于君臣的善治轉(zhuǎn)變?yōu)樵V諸于人們良知的發(fā)現(xiàn)。 王陽(yáng)明是位富有憂患意識(shí)的思想家。本來(lái),封建道德以“三綱”“五常”來(lái)維系社會(huì)統(tǒng)治秩序,區(qū)分人的身份貴賤是封建宗法制度的命根子,也是封建社會(huì)不能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廣泛和諧的要害所在。而王陽(yáng)明認(rèn)為,不同等級(jí)、不同地域、不同時(shí)代的人都有共同的“本然良知”。“良知”的顯露發(fā)用,就是“天道”的貫徹流行。由于人人都有共同的“良知”,因此人與人,不論是富貴貧賤,也不論是古今遠(yuǎn)近,以“良知”為融匯點(diǎn),就可以凝成一體。他的“良知”學(xué)說(shuō),正好抓住了這個(gè)要害,以“致良知”學(xué)說(shuō)突破了封建等級(jí)制度對(duì)于社會(huì)各階層的阻隔,在人倫觀念上為實(shí)現(xiàn)封建社會(huì)上層與下層之間的和諧開(kāi)拓了渠道。這是陽(yáng)明心學(xué)在傳承儒家社會(huì)和諧文化中既能超越前人,又能啟迪后人的重大貢獻(xiàn)。陽(yáng)明學(xué)說(shuō)之所以在東亞國(guó)家的資產(chǎn)階級(jí)民主啟蒙中能發(fā)生影響,原因也在于此。 其次,王陽(yáng)明以“致良知”為核心的“萬(wàn)物一體”的心學(xué)體系,在儒家“天人合一”的世界和諧觀念方面開(kāi)辟了一個(gè)新境界。 王陽(yáng)明認(rèn)為,不僅世上不同的人都有共同的“良知”,而且宇宙天地、世間萬(wàn)物也具有人的“良知”。人與天地、萬(wàn)物的共同發(fā)源處都是“良知”,“良知”又把人與天地、萬(wàn)物凝為一體。他論證道:“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天地?zé)o人的良知,亦不可為天地”,因此“天地、萬(wàn)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fā)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diǎn)靈明。風(fēng)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只一體。”④從而把宋明理學(xué)中的本體論哲學(xué)推向頂峰。“心之靈覺(jué)”,即“良知”,既是“造化的精靈”、“萬(wàn)物的主宰”,又是“天理”、“至善”和學(xué)問(wèn)。在這里,本體論、認(rèn)識(shí)論、價(jià)值論都以“良知”即“吾心”為源頭、為基點(diǎn)統(tǒng)一起來(lái)、同一起來(lái),融為一體。也就是說(shuō),人及宇宙中的萬(wàn)事、萬(wàn)物以及關(guān)于萬(wàn)事、萬(wàn)物之理,都統(tǒng)一到、同一到我的心中。王陽(yáng)明從“良知”是宇宙本體出發(fā),在人與人、人與社會(huì)、人與天地、人與萬(wàn)物的關(guān)系問(wèn)題上,形成“萬(wàn)物一體”、“天下一家”、“中國(guó)一人”的整體觀,把先秦以來(lái)儒家“天人合一”的世界和諧觀念發(fā)展到一個(gè)新的高度。 再次,必須看到,在王陽(yáng)明“萬(wàn)物一體”的和諧觀中,人與人之間的愛(ài)是有厚薄親疏的,物與物之間也是有等差的。 王陽(yáng)明認(rèn)為愛(ài)之所以有厚薄,這不是人為刻意要這樣,而是先天注定的“道理合該如此”。他舉例說(shuō):“禽獸與草木同是愛(ài)的,把草木去養(yǎng)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ài)的,宰禽獸以養(yǎng)親與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ài)的,如簞食豆羹,得則生、不得則死,不能兩全,救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這是道理合該如此。”⑤而這個(gè)“合該如此”的“道理”也就是封建倫理道德義禮智信。按照這個(gè)“條理”,得不到愛(ài),甚至作出犧牲的人或物,就要“忍得”,以維護(hù)封建宗法等級(jí)制度和封建倫理綱常。王陽(yáng)明的“萬(wàn)物一體”論對(duì)此從哲理的高度上比其前輩作了更完整、更嚴(yán)密、更巧妙的回答。他確信,只要貫徹“以萬(wàn)物為一體”,就可以把整個(gè)社會(huì)凝聚成既有秩序、有等差,又相親相愛(ài)、不分彼此的和諧的整體。在這個(gè)整體中,由于人人都能做到“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guó)猶家,而以天地萬(wàn)物為一體”⑥,因此便可實(shí)現(xiàn)天下大治。當(dāng)然,王陽(yáng)明倡導(dǎo)“天下一家,中國(guó)一人”的和諧觀念,根本的目的是為了維護(hù)當(dāng)時(shí)的封建統(tǒng)治,其所憧憬的這種美好的和諧社會(huì)在當(dāng)時(shí)的歷史條件下也是不可能實(shí)現(xiàn)的。但作為一種思想體系,一種思維方式,他的心學(xué)是有其歷史必然性和時(shí)代進(jìn)步性的。特別是他的“萬(wàn)物一體”論把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的整體和諧觀念提高到一個(gè)新的哲理高度,更加具有重要意義。 二、黃宗羲對(duì)儒家和諧文化的終結(jié)及創(chuàng)新 黃宗羲生活于“天崩地解”的明清之際,中國(guó)封建社會(huì)已處于窮途末路。雖然這時(shí)滿清王朝入主中原,漢人在國(guó)家政治生活不占主導(dǎo)地位,但是儒家文化在這時(shí)還是作為主流文化存在著,儒家文化中以“仁”為基本價(jià)值取向的“和諧文化”為凝聚中華民族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黃宗羲作為當(dāng)時(shí)的大思想家和大學(xué)問(wèn)家,在當(dāng)時(shí)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為傳承儒家和諧文化作出了特殊的貢獻(xiàn)。
注釋: ①《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六《大學(xué)問(wèn)》 ②《正蒙?乾稱篇》,《張載集》 ③《陽(yáng)明全書》卷二《傳習(xí)錄中》 ④《陽(yáng)明全書》卷二《傳習(xí)錄中》 ⑤《陽(yáng)明全書》卷三《傳習(xí)錄下》 ⑥《陽(yáng)明全書》卷二《傳習(xí)錄中》 ⑦《孟子師說(shuō)卷二》 ⑧《明儒學(xué)案?自序》 ⑨《明夷待訪錄?原君》 ⑩《明夷待訪錄?原君》 B11《明夷待訪錄?原君》 B12《明夷待訪錄?原臣》 B13《明夷待訪錄?原法》 B14《明夷待訪錄?田制》
與電子工程.jpg)
.jpg)
學(xué)習(xí).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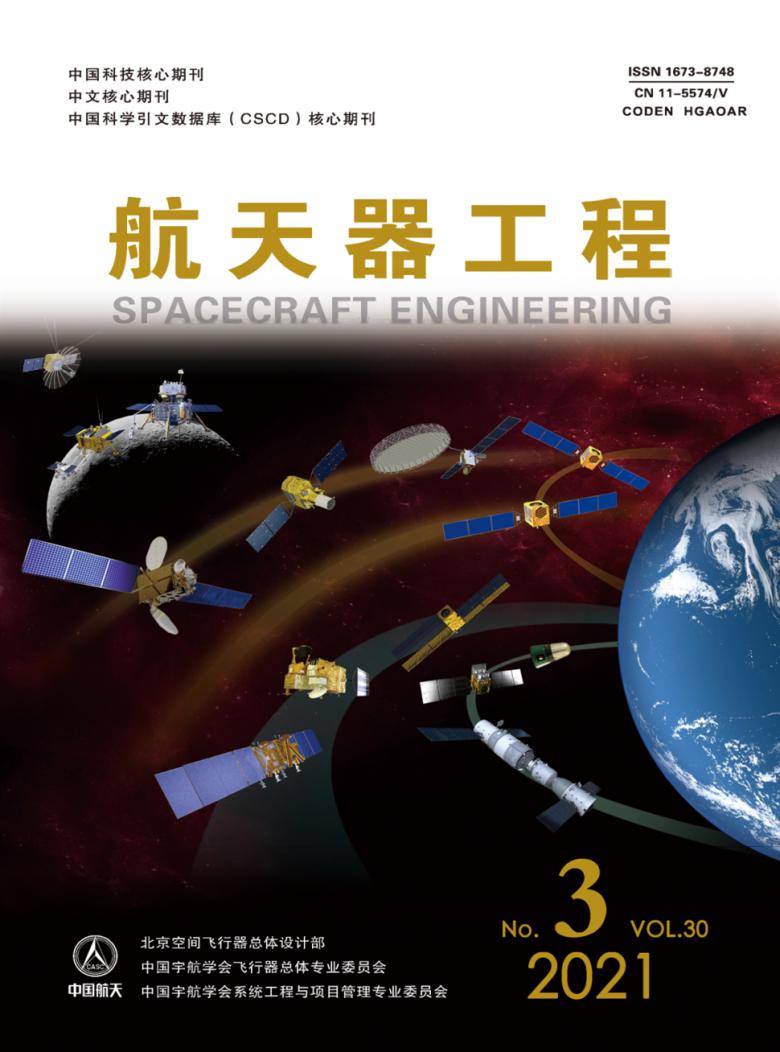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