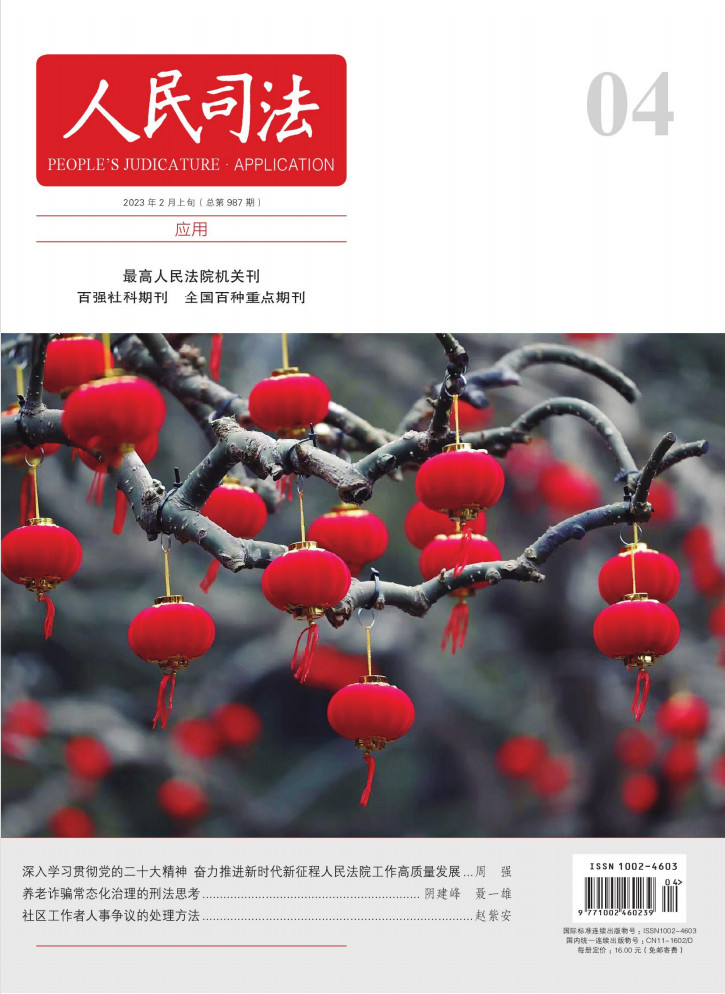晉商與近代山西的煤礦業
馬 偉
清末,晉商以275萬兩白銀從英國福公司手中贖回了山西礦權,捍衛了資源主權,為國家資源保護作出了巨大貢獻。但他們投資的機器采煤業的最大企業——保晉公司在經營中卻步履艱難。當時人發出感慨說:“噫!遍地黑金,而民困如此,所謂拿金飯碗討飯吃者,我山西人民也。”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有值得今人借鑒的自身原因,也
有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
自身原因有三:其一、晉商是在被動中投資近代煤礦業開發的。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古老的中國大地上出現了第一批近代化的工礦企業,這是中國人探求自強之路的努力,更是中國傳統的商業和產業發展受到極大挑戰之后逐漸形成的一種中國經濟發展同西方經濟相銜接的趨勢。然而遺憾的是,當時在票號時代進入極盛、具有雄厚資本的晉商對近代山西煤藏的大量發現和機器采煤業,在收回礦權運動之前幾乎是無動于衷的。中日甲午戰后,列強爭相在中國開礦筑路。正太鐵路修到娘子關時,晉人才如夢方醒,開始恐懼與憂慮,進而奮起抗爭。1905年,爆發了全國最大規模的爭回礦權運動,1907年,山西商人渠本翹、劉篤敬等創建了規模較大的股份制的山西保晉礦務公司。毫無疑問這是中國近代工業史上的一次偉大的愛國運動,但需要清醒地認識到,在爭礦運動中促使保晉公司建立的是政治原因大于經濟原因,渠本翹、劉篤敬等商人以及山西各界抵制洋商、挽回利權,更多是出于地方資源利權保護意識或者是閉關自衛和排外意識。
其二、晉商投資于機器采煤業的最大企業保晉公司先天不足,經營不善。山西最早、規模最大的近代煤礦企業——保晉礦務公司在政治風潮中創辦,因而它的經營,無論在資金上,還是設備、管理上都是準備不足的。公司成立之際,贖買礦權費用幾乎與公司全部資本相等,只剩很少的錢用于購買設備,僅以畝捐銀5萬兩為開辦之資,后又向山西當局領取畝捐銀15萬兩藉以布置。1908年,公司稟請當局在山西發行股票,但實際從1907年至1914年共集38萬6千余股,銀193萬余兩,僅為原計劃集股數的24%。更為致命的是,保晉公司本來是以山西地畝捐作抵押借晉商巨款支付福公司贖礦銀開辦起來的,但山西當局卻在1911年截留了全省的地畝捐,改用于軍費開支。保晉公司總經理渠本翹只好把公司吸收到的資本,大部分挪借給山西當局還款。可是山西當局卻一直拖欠這筆款項,造成了保晉公司資金長期短缺的局面,以致渠本翹因此辭去了首任總經理之職。從企業管理上看,由于受封建主義影響,加之非生產人員過多,管理也十分混亂。
其三、大多數商人像軍閥、官吏、地主一樣主要投資于手工煤窯,生產水平太低。從清末始,山西雖然開辦了一些近代煤炭企業,使山西的煤炭采掘、企業管理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但投資土法生產的煤礦無論戶數、礦區面積、煤炭產量仍占絕對優勢。據統計,1934年在全省1174座煤窯中,民營土煤窯達1125座,占全省總數的96%以上,煤炭產量達190萬噸,占全省產額的75%以上。盡管山西手工煤窯發展的三次高潮中,經營規模和生產技術有了一定的發展和提高,但總的來看,這些民辦煤礦的生產技術和生產方式都非常落后,大都屬于原始的手工操作,管理上保留著濃厚的封建色彩。山西商人這種經營煤礦業的落后陳舊的生產方式,注定是難以有所作為的。
晉商之所以沒有在近代煤礦業發展中崛起,除自身的原因外,還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第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外資對中國的煤炭市場的控制。近代中國,帝國主義通過不平等條約、武力侵占、借款控制等手段,侵占中國礦山,控制中國的煤炭業。據統計,早在1913年,帝國主義在中國煤礦業的投資額就占中國煤礦投資總額的80%,而包括山西在內的中國自營煤礦資本僅占總額的20%。在生產方面,1912年到1933年全國機械開采量,外資和中外合資礦占77%,而包括山西在內的中國自營礦僅占23%。在銷售市場上,以煤炭需量最多的上海、天津為例:1931年外資和中外合資煤以及進口煤分別占這兩個城市需量的86%和92%。由于帝國主義壟斷了中國的煤炭業,因而晉煤外銷一直處于帝國主義的打擊和排擠之下。當時晉煤之處境,正如時人所說:“外資各礦挾其雄厚之資力,對山西各礦極力排擠,晉煤銷路乃有日蹙百里之勢”。
第二,晉人的資源地方利權意識,助長了閻錫山官僚資本主義采煤業的壟斷。晉人爭礦運動中激發出來的煤炭資源地方利權意識非常強烈。1921年山西全省爆發了晉礦歸公風潮,起因是民國政府1914年頒布的《礦業條例》。這一條例侵害了山西的地方利益,當時有資力的達官貴人紛紛劃領礦區,這樣,山西民眾爭礦運動中所贖回的礦產,又被劃歸私人所有。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之后,三晉有識之士提出礦產歸公的理論,進而發動群眾掀起了晉礦歸公風潮。當時,閻錫山是山西省督軍兼省長,集軍事、政治、經濟大權于一身。他對這次群眾運動采取了利用的態度,在群眾運動中收買拉攏一些人為他服務,其結果不但晉礦歸公運動煙消云散,而且為閻錫山獨霸山西礦產鋪平了道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隨著閻錫山晉北礦務局、西北實業公司等官僚資本主義采煤業的出現和發展,絕大部分民營手工采煤業走向衰落。
第三,中國近代工業經濟的地理布局,使運銷問題始終成為山西煤炭業發展的嚴重制約因素。近代晉煤外運銷售的渠道非常有限,僅正太路(1905年通陽泉、1907年通太原)、平綏路(1914年通大同)兩條鐵路,且費用高昂,給晉煤外運造成了很大困難。此外,苛捐雜稅,戰事不斷,政局不穩,更使晉煤外運雪上加霜。自清季甲午戰爭到七七事變,四十多年的時間內,中國戰爭連綿,從未間斷。從1924年到1930年,閻錫山先是參加直奉戰爭,進攻直系軍閥,后又聯合直系軍閥進攻奉系軍閥,再又發起倒蔣之“中原大戰”,戰事連綿七年之久,鐵路經常因戰事停運,使晉煤外運銷售大受影響。爾后,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對華侵略戰爭,更使晉煤外運停頓,銷售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