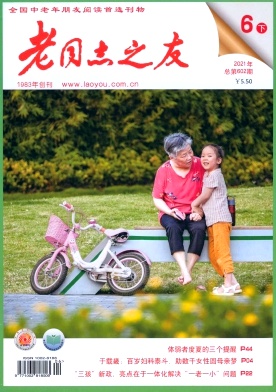論行政機關法解釋的審查基準
高秦偉
[關鍵詞] 行政機關 法律解釋 司法審查 基準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administrative organs take on a lot of tasks of interpretation of statutes. As the enhancement of the function of interpretation, it is a very important subject that how to confirm the standards that courts review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 interpretation. Whether a full-scale review, it is admitted that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prior to administrative organ interpretation, or a part of deference, only review the reasonableness? Based on the experiences in U.S.A, the paper mostly studies the standard of reasonableness, and comparatively analyses some factors that can use for reference.
Keywords: administrative organs; interpretation of statutes; judicial review; guideline
一、問題的提出
亞里斯多德將法治界說為“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自亞氏提出法治的定義以來,雖然內(nèi)涵不斷深化,但是核心意旨未變,“良法”與“普遍守法”至今仍是法治的基本含義。基于此,各國都極為重視立法工作,期望以良法之治實現(xiàn)法治理想。但畢竟立法者不是萬能的,“制定法面向未來。因為立法者不能準確地說明未來發(fā)生的問題的形成以及預言如壟斷貿(mào)易的新方式或新的消費問題,制定法只能使用總括性及靈活性的語言。”[[1]](P33)這使得法律總存在一定的漏洞,而同時立法者有時也會故意使行政法規(guī)范模糊化,給予行政機關相當大的解釋與裁量空間,從而充分發(fā)揮行政機關的能動性以適應日益復雜的社會需要。當下,“解釋成為行政必不可少的部分,因為行政資源中的語言內(nèi)涵經(jīng)常是模糊的、不確定的或抽象的。行政機關的首長與職員為工作便利,必須彌補這些漏洞,解決這些不確定性因素,以及減少抽象性而盡量具體化。”[[2]]隨著行政機關法解釋功能的不斷增強,法院對行政行為特別是行政機關法解釋的審查基準亦變得復雜起來。是全面審查,認為司法解釋絕對優(yōu)于行政機關的法解釋?還是部分尊重,僅審查其合理性呢?本文擬就此問題著重進行探討,并基于美國法的經(jīng)驗,指出其中具有借鑒意義的合理因素。
二、權力配置與司法尊重
研究行政法涉及的課題,不能不提及權力分立原則。法解釋問題更是如此,因為“解釋方法的選擇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機構權力配置的選擇。如果法院給行政機關對所實施法律的解釋予以強尊重的話,這種安排是將法律宣示的權力從法官移轉(zhuǎn)給了行政者。如果法院拒絕承認立法史的權威,將意味著從委員會或法案的發(fā)起者移轉(zhuǎn)給了行政機關或法院。如果法院在案件中承認立法至上,他們就認為自己是議會的附屬。”[[3]]所以有必要予以探討。
麥迪遜在《聯(lián)邦黨人文集》第47卷中講分權可能等于或不超過此種含義:即哪里政府某一個部門的所有權力被另一部門權力所支配,自由憲法的基本原則就會遭到破壞。此種理念下,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必須分開,行政機關是執(zhí)行法律的機關,必須依法行使行政權力。麥迪遜還認為:“立法、行政和司法權置于同一手中,不論是一個人,少數(shù)人或許多人,不論是世襲的、自己任命的或選舉的,均可公正地斷定是虐政。”權力分立且各司其職是分權理念形成時的核心課題,法律由民意代表機關制定,而行政權的任務則主要是嚴格地執(zhí)行法律。“可以這樣認為,作為美國憲政體系基本規(guī)則的是……立法機關不能行使行政或司法權;行政機關不能行使立法權或司法權;司法機關不能行使行政或立法權。”[i]“如果規(guī)則過于模糊,就存在行政機關成為立法者的危險,可預測性及選民的回應性將受到損害。”[[4]](P38)在形式主義的法治觀念的影響下,起初人們特別強調(diào)嚴格的依法行政原則,主張嚴格限制行政機關的裁量權,“無法律即無行政”,政府只能依法辦事,機械地執(zhí)行議會制定法律,權力分立理論的目的在于將各種權力分離出來,以權力制約權力,從而保障人民的政治自由和權利。
但現(xiàn)代行政機關的職能遠遠超出了傳統(tǒng)觀念的想象,其既包含有某些立法權能也包含有某些司法權能。不斷擴張的行政任務,不斷縮減的行政資源,不可避免地影響著行政法的理念,以至整個憲政理念。這種理念變化之一就是立法機關開始廣泛地向行政機關授權、司法機關開始廣泛地向行政機關放權。美國有學者比較1893年《聯(lián)邦鐵路安全設備法》(Federal Railway Safety Appliances Act of 1893)與1966年《國家交通與汽車工具安全法》(National Traffic and Motor Vehicle Safety Act of 1966)。認為前者以法律的形式詳細規(guī)定安全規(guī)則,而后者則是寬泛的詞語作一般性的指導。“因為法變得愈來愈復雜,適用它的機關對權威性的解釋需求也是越來越大。這些解釋可以從相關的行政機關那里獲得,其經(jīng)常愿意制定規(guī)則來指導公眾。”[[5]](P149)基于此,為適應社會發(fā)展,法院逐漸開始尊重行政機關在法解釋方面的優(yōu)勢與能力,尤其是在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認為這種尊重可以增強政府規(guī)制與給付系統(tǒng)執(zhí)行的統(tǒng)一性(uniformity),“當面臨法解釋問題時,法院將對從事該業(yè)務的官員或機構作出的法律解釋顯示更大的尊重。”[ii]實踐中雖然法院奉行的司法尊重原則(judicial deference doctrine)為法院贏得了一定的聲譽,但學者仍然對此提出了許多質(zhì)疑,認為尊重行政機關的法解釋“弱化而不是推進我們長期堅持的分權原則”,[iii]學者們進一步分析指出法院承認行政機關法解釋的效果是“法院向行政部門轉(zhuǎn)移責任與權力”,這樣給政府三個部門的權力分立與權力平衡帶來了極大的沖擊,因此法院應尋找一個“最好”的法解釋而不是去承認行政機關任何的合理解釋。[[6]]
盡管反對的聲音迄今依然存在,但實踐證明行政機關法解釋的重要作用不可替代,社會生活需要司法尊重行政機關合理的法解釋。分權的憲政原則亦需要司法尊重行政機關的法解釋。這有利于合理地配置權力,發(fā)揮各種權力的積極能動性。就日趨高度專業(yè)化與技術化的行政管理而言,行政機關無疑比司法機關更能了解社會的需要,對相關法律的目的與精神亦有其自身獨特的理解與把握。尊重行政機關的法解釋,不但是保證行政管理的連續(xù)性與效率性的需要,而且也是法院實行自律而避免過度介入行政領域的要求。早期的嚴格分權如今已經(jīng)沒有市場,分權更多意義上是一種程序意義上的概念,從此種意義上講,在現(xiàn)代社會,行政機關并非單純的“法執(zhí)行”機關,亦應是獨立的“法適用”機關。其不僅應關注法效果的執(zhí)行,更應著重于法構成要件的適用。雖然在分權的體制下,必須把各部分設計得使它們的工作目標不能完全相同,但“如果所涉及的問題可能主要是法律解釋或普通法問題,法官也許要比行政官更加合適;然而如果法律部門高度專業(yè)化,需要行政技術和解釋問題的知識(例如大多數(shù)行政法部門),將該問題交給行政裁判所或一個行政官解決則更為適宜。”[[7]](P208)提出這樣的論斷對一個具有濃郁普通法傳統(tǒng)的國家來說是極不容易的。美國更有學者撰文稱行政機關應成為現(xiàn)代美國的“普通法院”,[[8]]筆者認為其不僅寄托了該作者對行政機關提高法適用水準的殷殷期望,而且其更希望行政機關能夠切實肩負起現(xiàn)代行政國家法解釋的重任。
三、審查基準
行政機關對法律予以解釋是其更好地執(zhí)行公共政策、實現(xiàn)公共福祉的重要工具。很顯然,在適用法律層面,這種工具與法院對法律的宣示功能有些交叉。在行政訴訟過程中這一問題尤顯突出,如何解決呢?
美國法院早在19世紀就對這一問題的進行了關注并有了相關的判例,[iv]羅斯福新政之后,法院又通過一系列判例“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并由此確立了兩種不同的模式,即“尊重模式”(deferential model)與“獨立判斷模式”(independent judgment model)。[[9]]在尊重模式下,法院對合理的(reasonable)行政機關的法解釋予以尊重。[v]在獨立判斷模式下法院以自己對法的解釋來代替行政機關的解釋。[vi]基于這兩種模式,以及美國《聯(lián)邦行政程序法》(the Federal Administrative Procedural Act of 1982)及《州行政程序示范法》(Model Stat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of 1981)的相關規(guī)定,[vii]目前美國法院審查行政機關法解釋的基準大致有以下四種:
1.重新審理基準(de novo test)。其是指“依重新審查方式,法院既不給行政機關法律決定也不給行政機關事實認定最終的權力,相反,法院重新確定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先前已認定過的所有事實和法律問題。”[[10]]該標準有兩種形式:一種為純粹式重新審查(pure de novo),即允許審查法院從頭開始,法院可以舉行新的聽證會。另一種為記錄式重新審查(record de novo),即允許法院以自己的意見代替行政機關的意見,但法院對行政機關的記錄作有限審查,法院將不舉行新的聽證會,如果其發(fā)現(xiàn)記錄存在問題,將發(fā)回由行政機關自行認定事實或作出結(jié)論。大多重新審查都是基于記錄作出的。在這一標準之下,法院對行政機關行使最大程度的監(jiān)督和控制權力,法院行使審查權如同行政機關先前沒有作出決定一樣。這種判斷是基于合法性和正確性而作出的,法院具有完全的法律審查權。
2.實質(zhì)性證據(jù)基準(substantial evidence test)。最高法院第一次定義這一標準是在Consolidated Edison v. NLRB案:“實質(zhì)性證據(jù)不僅僅是星火一現(xiàn)。它意味著只要理性人會接受,相關證據(jù)就足以支持一個結(jié)論。” [viii]這一標準的采用使法院廣泛地尊重行政機關作出的事實調(diào)查問題。“對行政機關調(diào)查事實問題的司法尊重是相當合理的。在發(fā)現(xiàn)事實方面行政機關相對于審查法院具有實質(zhì)性的優(yōu)勢,因為他們極為熟悉行政記錄以及在需要解決的事實問題上的專業(yè)特長。”[[11]](P362)在實踐中,這一基準除大量適用于行政機關對事實的認定外,而且還適用于審查行政機關作出的正式性的法規(guī)范解釋行為(如立法性規(guī)則)。
3.專斷而反復無常基準(arbitrary and capricious test)。如果行政行為是通過非正式的裁決或非正式的規(guī)則制定行為作出的,那么法院的審查標準將是專斷而反復無常基準。這一標準在聯(lián)邦行政程序法、州行政程序示范法以及各州的行政程序法都有相關的規(guī)定,行政機關的決定如果不符合邏輯、不符合理性,將不被法院支持。聯(lián)邦最高法院認為第2、3項之間的區(qū)別在于后者要比前者更為寬大,但進一步的解釋以及為何后者更為寬大的原因,聯(lián)邦最高法院并未給出。而巡回法院則經(jīng)常視兩者為同一標準,名稱不一僅是“語義”上的差別。如今其內(nèi)涵基本趨于一致,即都要求在行政機關作出的決定中,相關證據(jù)必須是一個有正常理性的人可以接受的證據(jù)。
4.合理性原則基準(reasonableness)。其是指國會未就某一問題作出規(guī)定,且未明確授權行政機關,除非解釋不合理,否則不予駁回。這一標準是在Gray v. Powell案中確立的,[ix]該判決的中心意旨是,應按照合理性標準而不是正確性標準審查法律適用問題,不論法院是否同意行政機關的決定,只要這個決定合理,不是出于恣意和反復無常的裁量權濫用,法院就必須接受。這一案件所爭論的焦點是煙煤法中的“生產(chǎn)者”概念是否包括鐵路公司開采的煤礦。該鐵路公司和一個礦業(yè)承包人訂立合同,承租了一塊產(chǎn)煤地段。煤礦管理機關認為鐵路公司不能享受生產(chǎn)者的待遇。巡回法院撤銷了煤礦管理機關的決定,認為鐵路公司是生產(chǎn)者,因為礦業(yè)所有者是自己開采還是和他人訂約由后者替他開采并無區(qū)別。最高法院撤銷了上訴法院的判決,其認為:“雖然我們對于本案的證據(jù)性事實沒有爭議,但這并不意味著允許法院用自己的判斷取代行政機關的判斷。法院不能將其職權范圍擴展到行政職能之中,以至于使得執(zhí)行機關或立法機關成為單純的事實發(fā)現(xiàn)主體,從而不能采取迅速確定的行動”。法院認為,在將法律概念適用于無可爭議的事實時,只要行政機關的決定有合理的根據(jù),法院就應當維持行政機關的決定。
事實上,第2、3、4項之間很難作出明確的區(qū)分,有些人甚至將3、4項合并為一項。[x]也有學者認為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在確定行政機關法解釋的效力時,僅存在兩種不同的審查基準,即“合理性”與“正確性”基準。[[12]]合理性要求行政機關的解釋正當?shù)亟忉尫ㄒ?guī)范;而正確性則要求行政機關的解釋必須要符合司法機關的正確的解釋。合理性基準包括了第2、3、4項,正確性基準則對應于第1項。但事實并沒有這么簡單,在合理性基準形成過程中,產(chǎn)生了太多的疑惑與不確定性,給實踐操作帶來了極大的不便,在這一點上,許多法官也是頗多抱怨:“我們認為是時候認知一下最高法院關于這一課題的兩種標準,其總是與巡回法院選擇的正當方式相沖突。”[xi]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這一看似簡單的基準如此復雜呢?
四、合理性基準的形成軌跡:對幾個判例的分析
“對于那些研究法院和行政機關的相互關系的人來說,一直最令人困惑的問題之一乃為如何確定行政機關和法院在規(guī)制法律的解釋中的不同角色”。[[13]]在角色的抉擇之中,法院不愿放棄對法律問題的獨斷權以及面對日益復雜社會的那種無可奈何,或許正是法院一直并未統(tǒng)一合理性審查基準、明確合理性審查基準內(nèi)涵的重要原因。筆者認為要徹底探究合理性審查基準(盡管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有些不情愿),有必要介紹一下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的幾個重要判例,并以此為例證,才能系統(tǒng)整合合理性基準的內(nèi)涵。
1.Skidmore案
1944年的Skidmore v. Swift & Co.案[xii]涉及《勞工公平標準法》(Fair Labor Standards Act)適用的問題。國會建立了一個行政機關來實施該法,但并未授予其規(guī)則制定權。該行政機關以解釋性規(guī)則表明自己對某一法律問題的看法。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指出:“我們認為,行政人員的認定、解釋和意見……盡管不能因為其權力對法院有約束力,但的確可構成法院和訴訟當事人可以正當?shù)孬@得指導的一套經(jīng)驗和有見地的判斷。在某一特定案件中的此類判斷的分量,將取決于其考慮所表現(xiàn)出徹底性、其推理的有效性、其與先前和后來的聲明的一致性,及所有可獲得說服力的這些因素。”美國學者稱之為Skidmore尊重標準,“按照這一審查標準,法院只需提供給行政機關看法以不同程度的‘尊重'或'考慮',不管行政機關獲得何種程度的尊重,其必然是因其說服力而'贏得'此尊重的。”[[14]]根據(jù)本案“說服力”主要包涵有制定規(guī)則時徹底的調(diào)查、推理的有效性以及與先前聲明的一致性等。
2.Chevron案
1984年的Chevron U.S.A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案[xiii]是1977年清潔空氣法(Clean Air Act)修正案中的“固定的空氣污染源”(stationary sources of air pollution)一詞的含義(環(huán)境保護署通過的一項立法性規(guī)則來解釋該詞的含義)。法院提出了一種“兩步式”標準來審查行政機關法律解釋的效力,并由此確立了著名的Chevron尊重標準:第一步主要審查國會是否就涉及的問題作過準確的說明。如果國會的意圖十分清楚,問題結(jié)束;法院、行政機關都應服從于國會明確表示的意圖。但是,法院認為國會并沒有就涉及的問題作出過明示時,法院便不能簡單地將自己的解釋強加于制定法,當然,在缺少行政機關的解釋時可能這樣做是必須的。第二步,如果法律就相關問題沉默或較為模糊時,法院的作用在于判斷行政機關的回答是否基于一種允許的法律解釋之下。只要行政機關的法律解釋合理,法院就予以尊重。有些巡回法院認為Chevron第二步就等同于Skidmore尊重,即是關于合理性的探究。[xiv]但也有學者認為Skidmore案中的說服力基準(persuasiveness test)與Chevron案中的合理性基準(reasonableness test)有著本質(zhì)上的不同,[xv]但事實果然如此嗎?二者果真難以融合嗎?
3.Christensen 案與Mead案
Christensen v. Harris County案[xvi]與United States v. Mead Corp.案[xvii]均涉及行政機關解釋的效力確定問題。在前案中,聯(lián)邦最高法院最終以5比4的結(jié)果駁回了起訴人的請求,并在判決中就是否尊重美國勞工部工資與工時司意見書中的解釋問題闡發(fā)了意見?工與工時司的:“在此,我們面對的是包含在意見書中的解釋問題,而不是在經(jīng)過諸如正式裁決或通告評論制定規(guī)則等后所作的解釋。此類在意見書中的解釋――如包含在政策聲明、機關手冊和執(zhí)法指南中的解釋一樣,均無法律效力,不能獲得Chevron式的尊重。”“相反,包含在諸如意見書中的解釋,應依據(jù)我院在Skidmore v. Swift & Co.案判決‘予以尊重',但僅限于這些解釋具有'說服力'的程度。”后案爭議的核心問題是美國海關總署作出的關稅分類裁決是否應獲得司法尊重。根據(jù)美國法典,海關總署有權按照財政大臣所發(fā)布的法規(guī)和規(guī)則,最終確定適用于某商品的關稅和稅率。Mead公司不服海關總署作出的一項裁決,在該項裁決中海關總署對Mead公司進口的“記事本”作了解釋,認為屬于自己調(diào)整的范圍。最高法院以8比1的結(jié)果對案件作出裁判,“行政機關對某一特定法律規(guī)定的實施符合下列條件,有權得到Chevron式的尊重:它表明國會已授權該行政機關通常可以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規(guī)則,且要求得到尊重的行政機關的解釋是在行使此權力的情況下作出的。此種權力的委任可以以多種方式加以證明,如行政機關享有進行裁決或通告評論式規(guī)則制定的權力,或者通過其他方式表明國會類似的意圖。” 一些學者認為自此兩案后,Skidmore模式取代了Chevron模式,而成為審查行政機關法律解釋的基本標準,[[15]]其“基本規(guī)則是,立法對行政機關指令的模糊性由法官而不由行政機關來解決。”[xviii]
4.Walton案與Lynchburg College案
2002年發(fā)生的Barnhart v. Walton案繼續(xù)著聯(lián)邦高院的矛盾與慎重。[xix]本案涉及社會保障署(SSA)定義“傷殘”(disability)的含義從而為發(fā)放補助金提供標準。多年前SSA早已采納了該解釋,但僅是最近才將其納入到了一個通過“通知評論程序”制定的規(guī)則中。Mead案后,行政機關一般使用通知評論的程序來獲取對其解釋的Chevron尊重。原告認為法院不應理會行政機關的解釋,因為規(guī)則才出臺不久,或許就是對其訴訟的對應之策。“法院是否給予Chevron尊重取決于解釋的使用方法以及涉訴問題的性質(zhì)。”“在本案中,法律問題的補充(interstitial)特性,與之相關的行政機關的專業(yè)知識,法律執(zhí)行問題的重要性,該行政的復雜性,以及行政機關對此問題長期的深思熟慮,均表明Chevron將為審查涉訴問題的行政機關解釋的有效性提供正確的法律視角。” [xx]這一次Scalia大法官投了贊成票,因為本案明顯帶有Chevron模式的痕跡,在判決中法院在試圖調(diào)和Chevron與Skidmore之間的差異與矛盾。[xxi]這種綜合的態(tài)度持續(xù)到了2002年的另一起案件中,即Edelman v. Lynchburg College案,[xxii]在本案的判決中聯(lián)邦最高法院并未聲明(基本上是回避了)是選擇適用Chevron還是Skidmore原則的問題,僅寫道:“這里沒有必要解決任何尊重的問題。我們發(fā)現(xiàn)均等就業(yè)機會委員會(EEOC)的規(guī)則不僅是合理的,而且即使不是正式規(guī)則需要我們重新解釋時,我們的立場也是要采納之。因為我們極為同意EEOC的主張,而不需要去談尊重或問何種類型的尊重,或其程度。”[xxiii]可以認為本案是對Mead案的一次反動,法院認為問題的關鍵不在于規(guī)則的表現(xiàn)形式,而在于內(nèi)容的合理性。[xxiv]此種合理性的判斷,意在保持司法機關在政策形成中的特有作用,當然最佳狀態(tài)是其應在發(fā)揮自己能動性的同時,最大限度地得到行政機關的幫助。
在確定合理性基準時,Skidmore案與Chevron案中所提出的原則均極為重要,第3、4項中涉及的案件以及其他大量的案件基本上都是圍繞此二者來展開的。第3項中的兩案試圖區(qū)分二者的差別,但第4項中的兩案則試圖調(diào)和二者的共通之處。應該講這種調(diào)和是正確的,過分夸大二者的差異很難讓法官對合理性基準有一個準確的把握,而問題的關鍵恰恰在于對合理性因素的考量。從目前的發(fā)展來看,筆者認為二者的共通之處仍居多處,共同構成了合理性基準的內(nèi)涵。客觀地講,二者均存在一定的問題,惟有共存而不是互相取代才會促進合理性基準的不斷豐富和發(fā)展。Skidmore尊重模式對國會授權的強調(diào),凸顯了立法性規(guī)則與解釋性規(guī)則之間的差異,[xxv]所以法院認為審查基準應有所不同。但這種僅以名稱或僅以制定時適用的程序來判斷何種審查基準的方式顯得過于形式化。在Mead案中Scalia大法官的反對意見就認為選擇Skidmore尊重模式會約束行政機關的解釋能力而使規(guī)制法律僵化,[xxvi]他認為在Mead案中使用Skidmore尊重模式,就等于“要求法院自己來解釋——但如果當行政機關使用了正確的程序其也可能被撤銷……據(jù)我所知在聯(lián)邦法院整個歷史中并無一個案例,允許由行政機關駁回司法解釋——或允許行政機關改正低級法院提出的法律解釋。”[xxvii]“從這一點來看,盡管Mead案被視作是鼓勵行政機關用謹慎、透明的方式行使專業(yè)知識的一種嘗試,但其也可能在事實上剝奪了行政機關運用自己的專業(yè)知識來形成法律解釋的權力。”[[16]]亦有學者指出Skidmore式尊重制約了行政機關法解釋的靈活性,帶來的后果可能是行政機關能夠用立法規(guī)則(可適用Chevron原則)推翻(overrule)司法適用的Skidmore決定,[[17]]就實質(zhì)而言其實Skidmore式尊重才是反Marbury案的。[xxviii]而Chevron尊重模式對行政機關能力的強調(diào),突出了其參與公共政策形成過程中體現(xiàn)的專業(yè)性、知識性以及連續(xù)性等特點。但其規(guī)定的合理性基準過于原則化、簡單化,[[18]]若操作不當極易破壞民主、分權、法治等基本的憲政理念。所以在2002年的兩個案件中,法院對合理性基準進行了細化,強調(diào)合理性基準應該考慮授權、規(guī)則形式、專業(yè)與經(jīng)驗、一貫性等因素。這幾個重要案件映證了美國司法審查中合理性基準的形成軌跡,也正是如此,從1944至今的60年間,Skidmore尊重與Chevron尊重“殊途同歸”,互相修正、互相倚重,它們豐富的內(nèi)涵共同構成了合理性基準的主要內(nèi)容。
普通法的演變與傳承總是讓人難以知曉某個原則的確定內(nèi)涵,但它尤如靜水深流的意境一般,平靜中蘊含著從容,使它永遠都有應對社會變遷的方法。不過作為學術研究,仍然是要給出合理性基準的具體內(nèi)涵,盡管現(xiàn)實中美國各級法院對這種內(nèi)涵理解各異。其內(nèi)涵大致包括:在某行政機關的專業(yè)或技術領域內(nèi)、行政機關對相關問題已經(jīng)予以詳細的與徹底的考察、有效的推理、存在協(xié)調(diào)互相沖突的政策的需要、國會已經(jīng)明確授予行政機關規(guī)章制定權、解釋與行政機關采取落實制定法要求的措施同時提出、國會注意到行政機關的觀點而未對其加以變更,以及與行政機關已經(jīng)適用的解釋具有一致性等。而其他的因素如不適當?shù)膭訖C或目的、考慮不相關的因素、未考慮相關因素、非理性、惡意、恣意、反復、荒謬、違反平等原則、違反比例原則、違反合法期待等都有可能降低行政機關法解釋的合理性。
五、余論
在中國,行政機關也承擔著大量的法解釋的任務,根據(jù)實定法的規(guī)定,[xxix]其被稱為“行政解釋”。在現(xiàn)行體制下,每當一部關于行政的法律問世,行政主管部門總會有相應的實施細則或條例產(chǎn)生。法律包括一些基本法律的解釋權順著法律-實施細則(條例)-細則的解釋而流向主管部門,從而造成行政機關集立法權與行政權于一身、行政權在司法領域割據(jù)的局面。根據(jù)現(xiàn)行《行政訴訟法》第12條及第53條的規(guī)定,行政機關對自己立法所作的解釋,也不應在法院的審理范圍之內(nèi)。該法第12條規(guī)定的法院不受理之四種訴訟中,包括“行政法規(guī)、規(guī)章或者行政機關制定、發(fā)布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而這些文件中通常含有行政機關自己解釋的有關規(guī)定,該法第53條第2款規(guī)定,法院認為地方政府的規(guī)定與部委規(guī)章不一致、或部委規(guī)章之間不一致時,應由最高人民法院送請國務院作出解釋或裁決,可見規(guī)章的解釋權專屬于行政機構,不得由審判機構進行。在憲法及其他立法授權的范圍之內(nèi),行政機關對自己制定的法規(guī)進行的解釋活動,一般不受人大或法院系統(tǒng)的影響,處于一種接近封閉的運行狀態(tài)。這樣的現(xiàn)狀給我們研究審查基準帶來了難度。
基于前述情況,有人建議取消國務院及其所屬部門的法律解釋權,由于“國務院及所屬部門有權對所適用的行政法做出法律解釋,然而國務院及其所屬部門在適用法律的過程中同時也是行政法律關系的一方當事人,法律授權行政法律關系的行使國家權力的一方當事人來解釋行政法律規(guī)范,同時讓處于弱者地位的對方當事人即行政相對人來遵守這種解釋,自然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同時也違反了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即職權法定的原則。”所以“全國人大常委會應及時有效地行使好《立法法》賦予的法律解釋權。在法律適用過程中有關法律問題的解釋,應只授權給最高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司法解釋,因為法院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其職責是居中就當事人之間的 糾紛作出裁決,而不代表任何一方當事人的利益,因而依法賦予其行使法律解釋權是合理的。”[xxx]筆者認為這是一樣“因噎廢食”的做法,不能因為目前立法機關對行政機關的授權往往過于寬泛,行政立法過程缺少充分而完善的公眾參與渠道和利益協(xié)調(diào)機制,難以代表公眾的利益就懷疑行政機關對法律解釋的作用,這與現(xiàn)代法治的理念是背道而馳的。美國的相關實踐值得我們關注與省思:讓法院完全接受行政機關的法解釋是不可能的,這有違憲法所賦予它的司法權力,“但,憲法也沒有要求讓法院獨立決定每一個規(guī)制條款的含義或以自己的解釋代替行政機關對法律的解釋。”[[19]]在現(xiàn)代社會,或許正義不僅僅體現(xiàn)于法院,其還被檢察官、福利行政者、移民局的官員、經(jīng)濟規(guī)制者以及提供救濟金的官員來執(zhí)行與體現(xiàn)。[[20]](P1)中國尚需在這方面加強理論與實踐探索,進而提高司法權威與行政能力。不過,需要再次強調(diào)的是:一概由行政機關說了算或由法院進行全面審查的做法都是不科學的,可取的方法可能是針對不同類型的行政法規(guī)范解釋行為建立不同的審查基準、考量不同的審查因素,進而構建行政訴訟法中的合理性審查基準。
--------------------------------------------------------------------------------
[i] Springer v. Philippine Islands, 277 U.S. 189, 201(1928)。
[ii] Udall v. Tallman, 380 U.S. 1, 16(1965), cited in Johnson v. Robison, 415 U.S. 367, 369(1974)
[iii] Cass R. Sunstein,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in a Conservative Era, 39 Admin. L. Rev. 353, 360-61 (1987)。 不過后來Sunstein改變了看法,轉(zhuǎn)而支持Chevron案,并為其正當性作了大量的論證。See Cass R. Sunstein, Is Tobacco a Drug?: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as Common Law Courts,1998 Duke Law Journal 47.
[iv] See, e. g., United States v. Vowell & M'Lean, 9 U.S. (5 Cranch) 368, 372 (1808)。
[v] See, e.g., Ehlert v. United States, 402 U.S. 99(1971); Red Lion Broadcasting Co. v. FCC, 395 U.S. 367(1969)。
[vi] See, e.g., NLRB v. Bell Aerospace Co., 416 U.S. 267, 289(1974); Office Employees Int'l Union v. NLRB, 353 U.S. 313, 320(1957); Davies Warehouse Co. v. Bowles, 321 U.S. 144, 156(1944)。
[vii] See 5 U.S.C §706(2)(1982); 1981 MSAPA §5-116.
[viii] 305 U.S.197, 229(1938)。
[ix] 314 U.S. 402(1941)。
[x] “Unreasonable, arbitrary, Capricious”, see Arthur Earl Bonfield, State Administrative Rule Making,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86, pp. 574-575.
[xi] Pittson Stevendoring Corp. v. Dellaventura, 544 F. 2d 35, 49(2d Cir. 1976)。
[xii] 323 U.S. 134, 140(1944)。
[xiii] 467 U.S. 837(1984)。
[xiv] See, e.g., Evans v. Commissioner of Me. Dept. of Human Servs., 933 F. 2d 1, 7 (1st Cir. 1991)。
[xv] See Jamie A Yavelberg, The Revival of Skidmore v. Swift: Judicial Deference to Agency Interpretations after EEOC v. Aramco, 42 Duke L. J. 166(1992)(該學者認為Skidmore中考慮的“說服力”因素大體等同于APA中的“arbitrary and capricious”標準,但其在界定合理性標準時與對“arbitrary and capricious”標準的分析并無二致)。
[xvi] 529 U.S. 576 (2000)。
[xvii] 533 U.S. 218 (2001)。
[xviii] United States v. Mead Corp. 533 U.S. 244(2001)(Scalia, J., dissenting)。
[xix] 535 U.S.212, 220-22(2002)。
[xx] Id. at 222(citations omitted)。
[xxi] 第7巡回法院的Posner法官指出:“Walton案……是聯(lián)邦最高法院近來解釋Chevron的一個判決,試圖合并Chevron尊重與Skidmore式的……依據(jù)環(huán)境判斷對行政機關決定的尊重模式。”(Krzalic v. Republic Title Co., 314 F. 3d 875, 879(7th Cir. 2002)。) 同是該法院的Easterbrook也支持這一觀點,“我不喜歡在Walton案中的任何‘合并'……在Mead案中,曾努力對Chevron與Skidmore進行區(qū)分。”(Id. at 882.)
[xxii] 535 U.S. 106(2002) (本案源起于Edelman教授因非法歧視而被Lynchburg學院未續(xù)聘)。
[xxiii] Id. at 114.
[xxiv] See Edelman v. Lynchburg College, 535 U.S. 106(2002) (O' Connor, J. Concurring, joined by Justice Scalia)。
[xxv] 這兩種規(guī)則是美國聯(lián)邦行政程序的規(guī)定,前者適用程序較嚴,要求有國會的授權,其效力等同于法律。后者一般不具有拘束法院的效力。但在實踐中行政機關總是企圖通過解釋性規(guī)則或政策聲明來達到與立法性規(guī)則同樣的效果。在中國類似的情況更多。
[xxvi] See United States v. Mead Corp., 533 U.S. 218, 239, 247-50(2001) (Scalia, J., dissenting)。
[xxvii] Id. at 248-49 (Scalia, J., dissenting)。
[xxviii] “old Skidmore as new Counter- Marbury”,這是個借喻,早期的Sunstein曾認為Chevron是反Marbury案的(see Cass R. Sunstein, Law and Administration after Chevron, 90 Columbia Law Review 2071, 1990. ),also see Russell L. Weaver & Thomas A. Schweitzer, Deference to Agency Interpretations of Regulations: A Post- Chevron Assessment, 22 Memphis St. U. L. Rev. 411, 422(1992); Thomas W. Merrill, Judicial Deference to Exectutive Precedent, The Yale L. J. Vol. 101, 1992, p.993-98.
[xxix] 參見現(xiàn)行《憲法》、《立法法》及1981年6月10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頒布的《關于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的相關規(guī)定。
[xxx] 關于該觀點可參見田雪梅:《關于完善我國行政立法的思考》,載http://www.qddx.gov.cn/journal/20020627.htm,2004年11月4日訪問。
--------------------------------------------------------------------------------
[1] Lief Carter & Christine Harrington, Administrative Law and Politics, Addison Wesley Longman, Inc., 2000.
[2] Michael Asimow, Nonlegislative Rulemaking and Regulatory Reform, 1985 Duke Law Journal.
[3] John F. Manning, Constitutional Structure and Statutory Formalism, 66 U. Chi. L. Rev. 685, 691-692 (1999) (citation omitted)。
[4] Stephen G. Breyer, Richard B. Stewart, Cass R. Sunstein & Matthew L. Spitzer, Administrative Law and Regulatory Policy: Problems, Text and Cases, 5th ed., Aspen Publishers, Inc., 2002.
[5] Bernard Schwartz, Administrative Law, 3rd editi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1.
[6] See Abner Greene, Checks and Balance in an Era of Presidential Lawmaking, 61 Uni. Of Chicago L. Rev. 123 ( 1994)。
[7] [英]W. Ivor. 詹丹斯。法與憲法[M].蘇力。三聯(lián)書店,1997.
[8] See Cass R. Sunstein, Is Tobacco a Drug?: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as Common Law Courts,1998 Duke Law Journal 47.
[9] See Cynthia R. Farina,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89 Colum. L. Rev. 452, 453-54 (1989); also see Kenneth W. Starr, Judicial Review in the Post – Chevron Era, 3 Yale J. on Reg. 283, 300-07(1986)。
[10] Ann Woolhandler, Judicial Deference to Administrative Action- A Rivisionist History, 43 Admin. L. Rev. 200(1991)。
[11] Richard J. Pierce, Jr., Sidney A. Shapiro & Paul R. Verkuil, Administrative Law and Process, 3rd edition, Foundation Press, 1999.
[12] See Stephen M. Lynch, Framework for Judicial Review of an Agency's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Chevron, U.S.A., Inc.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1985 Duke L. J. 469 (1985)。
[13] Cynthia R. Farina,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89 Colum. L. Rev. 452.
[14] Cooley R. Howarth, Jr., United States v. Mead Corp.: More Pieces for the Chevron/Skidmore Deference Puzzled, Admin. L. Rev., Vol.54, No.2, Spring 2002.
[15] See Cooley R. Howarth, Jr., United States v. Mead Corp.: More Pieces for the Chevron/Skidmore Deference Puzzle, Admin. L. Rev. Vol.54, No.2, Spring 2002.
[16] Richard W. Murphy, A “New” Counter- Marbury: Reconciling Skidmore Deference And Agency Interpretive Freedom, Admin. L. Rev. Vol. 56, No.1, Winter 2004.
[17] See Paul A. Dame, Note, Stare Decisis, Chevron, and Skidmore: Do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Have the Power to Overrule Courts?, 44 Wm. & Mary L. Rev. 405, 435-36(2002)。
[18] See Breyer, Judicial Review of Questions of Law and Policy, 38 Admin. L. Rev. 363(1986)。
[19] Russell L. Weaver, The Emperor Has No Clothes: Christensen, Mead and Dual Deference Standards, 54 Admin. L. Rev. 173(2002)。
[20]See Kenneth Culp Davis, Discretionary Justice in Europe and Americ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6.
業(yè)經(jīng)濟研究.jpg)

展.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