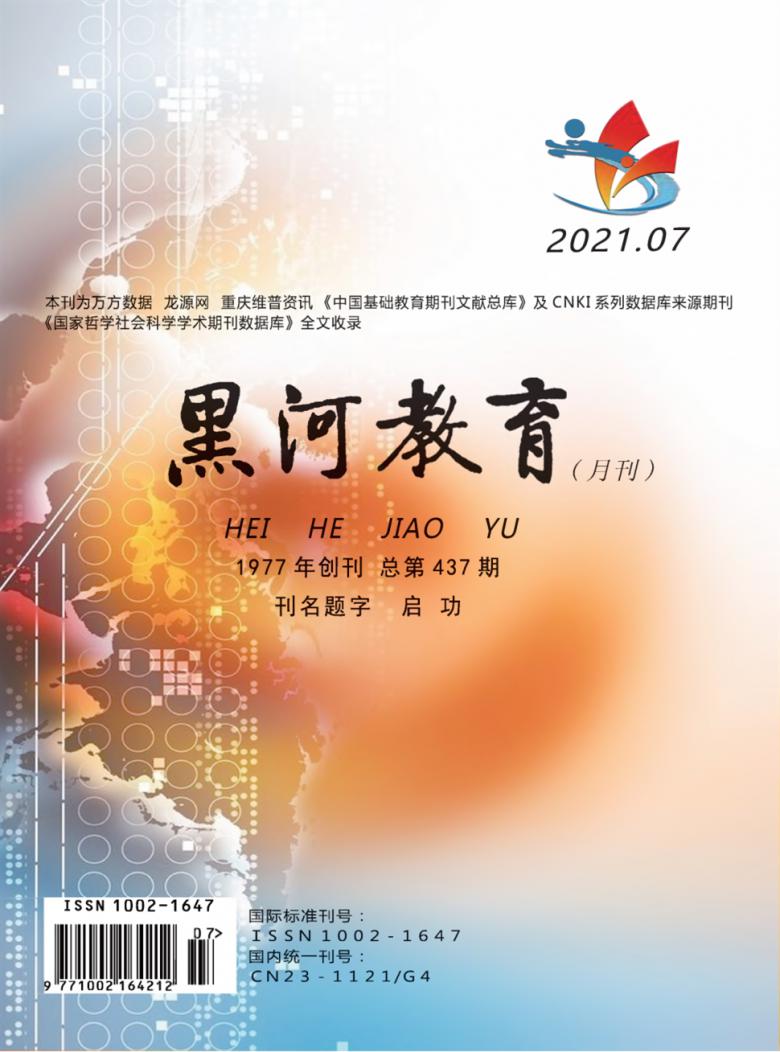行政實體法的拘束程度與行政機關的調查義務和舉證責任
王天華
我國從行政訴訟制度創立伊始就十分重視其舉證責任分配問題。從1989年公布的《行政訴訟法》(以下簡稱“《行訴》”)到2000年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高院解釋》”),乃至2002年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髙院規定》”),都對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問題作了專門規定(以下將這三者中存在的舉證責任規定統稱為“行政訴訟舉證責任規定”)。這些行政訴訟舉證責任規定,毫無疑問,是以關于行政訴訟舉證責任的特定的理解為基礎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在范疇上是行政訴訟舉證責任論的一部分。
恰逢行政訴訟制度的改革乃至《行訴》的修改被提上了議事日程[1],本文試圖從舉證責任問題的理論原點出發,參照德國、日本的有關理論,對我國的行政訴訟舉證責任論――包括行政訴訟舉證責任規定――進行一個比較徹底的反思,以供參考。
一、問題的狀況
總體而言,我國目前的行政訴訟舉證責任規定并不周延,它沒有完整地涵蓋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問題的基本方面;與這種行政訴訟舉證責任規定的不周延性相關,學說處于眾說紛紜的狀態,判例處于亟需梳理和充實的狀態(特別是其“判決理由”部分)。
(一)關于原告對具體行政行為違法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的情形
1、《行訴》第32條規定:
“被告對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應當提供作出該具體行政行為的證據和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
作為對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問題的立法性解決,本條的規定至少在文面上并不周延。因為,它既沒有規定、也沒有規定特別是。
2、根據《行訴》第32條,有人認為“行政機關的舉證責任是單方責任,即被訴的行政機關負舉證責任”[2],還有人認為“被告對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實質上是一種“舉證責任倒置”、即“將原來的由原告負擔的證明責任予以免除,而就該待證事實的反面事實由被告負證明責任”[3].按照這一理解,這一命題是成立的。
3、而實際上,這一命題并不符合裁判實踐。至少,(1)原告指控行政機關濫用職權(如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毆打辱罵了原告)時,(2)被告證明了自己的行為合法以后、原告還主張被告行為違法時,原告是要承擔與其主張相應的舉證責任的[4].
「案例1」國家外匯管理局、中國證監會、國家工商管理局(95)匯管函字第191號《關于查處非法外匯期貨(按金)交易活動的通知》(以下簡稱“《查處通知》”)第1條第1項規定:對經營外匯期貨(按金)交易并已對外接盤、下單的機構,由外匯管理部門進行處理。同時,《查處通知》第2條第3項規定:對以經營商品期貨交易、信息、投資咨詢為名,實際進行外匯期貨交易,且未與境外接盤下單的機構,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按超范圍經營進行處理。
本案中,原告公司未經國家證監會、中國人民銀行、國家外匯管理局批準和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核準注冊,擅自接收客戶從事了香港恒生指數期貨交易。被告市工商局依據《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施行細則》(以下簡稱“《細則》”)第66條第1款第(四)項、國辦發(94)69號《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務院證券委員會關于堅決制止期貨市場盲目發展若干意見請示的通知》(以下簡稱“《制止通知》”)第5條,以原告公司超范圍經營為由對其進行了處罰(本件處罰)。對此,原告公司提起撤銷之訴,引用《查處通知》第1條第1項的規定,主張本件處罰顯屬越權(本件主張)。
法院首先對被告工商局提供的原告公司超經營范圍從事期貨交易的證據和所依據的行政法規和規章(本件處罰的要件認定)進行了審查核實,然后要求原告公司提供其已經接盤下單的證據。由于原告公司沒能提供該證據,法院認定被告工商局在本件處罰中沒有越權,判決維持本件處罰。[5]
在這個案件里,原告超經營范圍從事期貨交易這一事實是沒有爭議的,正因為如此,法院首先認定被告已經完成其舉證責任。有爭議的是原告擅自從事期貨交易是否“已對外接盤下單”。如果這一事實存在,根據《查處通知》第1條第1項的規定,應該由外匯管理部門而不是被告對原告作出處罰。法院就該事實向原告求證,原告沒能提供相應證據,法院據此否定了原告的本件主張,判決其敗訴。應該認為,在這里,原告承擔了對“(自己)已對外接盤下單”這一事實的舉證責任[6].
4、為了解決《行訴》第32條的不周延性,《髙院解釋》和《髙院規定》對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問題作出了更加詳細的規定。
我們注意到,這些以司法解釋形式存在的舉證責任規定,主要是明確了原告關于其起訴符合起訴條件的事實、行政不作為案件中其曾經提出申請的事實、行政賠償訴訟中其(因受到被訴行為侵害而)受到損失的事實的舉證責任(《髙院解釋》第27條,《髙院規定》第4條、第5條)。從這些規定的內容我們可以看取這些司法解釋的制定者的一個很明顯的問題意識:明確這一認識。特別是《髙院解釋》第27條第(四)項的兜底規定(“其他應當由原告承擔舉證責任的事項”),更是在邏輯上為涵蓋的情形留下了充分的解釋空間。
但是,《髙院解釋》第27條第(四)項兜底規定所預留下的解釋空間,被《髙院規定》第6條消除了。該條規定:“原告可以提供證明被訴具體行政行為違法的證據。原告提供的證據不成立的,不免除被告對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舉證責任。”如果對該條作嚴格的語義解釋,我們不得不認為,它是在表達這樣一個意思:[7].
結果,行政訴訟舉證責任規定的不周延性并沒有因為司法解釋的出臺而解消[8].
5、關于的情形的存在,除了姜明安之外,其他學者亦有論述。如,劉善春指出,在如下情形下,原告要承擔相應的舉證責任[9]:
(1)原告主張被告“作出了法律禁止其作出的行為”,可以由原告負舉證責任。??????被告對行政行為合法性構成要件證明,不能沖抵的余下的事實爭執點,只能由原告證明的情形下,由原告負舉證責任。
(2)關于登記、注冊、行政確認或許可等授益行政行為,申請材料的實質真實,在行政訴訟中,仍由申請人或登記、注冊權利人負舉證責任,登記、注冊機關可以不負舉證責任。
另外,劉飛也曾經指出:
“在首先負舉證責任的一方為其實體請求的舉證足以使法院認定其實體請求合法的情況下,舉證責任才能轉移到訴訟中的另一方當事人,并且,舉證責任還可以依此在雙方當事人之間不斷轉移。”[10]
在引文的觀念里,這一命題是成立的。
6、但是,不能忽視的是,還有學者一方面承認在行政訴訟中原告也應該承擔一定的舉證責任,另一方面對原告所承擔的“舉證責任”與被告的加以嚴格區別。認為:
原告為了推動訴訟的進行,應當首先證明起訴符合行政訴訟法規定的起訴條件、為了勝訴還必須進一步提出證據動搖被訴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使審判人員對被告的舉證產生懷疑或者有進一步調查的必要性。即,在行政訴訟中,被告承擔的舉證責任是說服責任,實質是一種敗訴風險的承擔,而原告所承擔的證明責任則是推進責任。[11]
另外,還有學者在對提證責任和法定責任加以分別之后,認為行政訴訟中原告“主要負提證責任,被告在行政訴訟主要承擔法定責任”[12].
這些觀點似乎都沒有意識到的情形的存在。
(二)關于被告的舉證責任的性質與證明的程度
行政訴訟舉證責任規定的不周延性,不光表現在原告所應承擔的舉證責任問題上,還表現在被告所承擔的舉證責任的性質(是作為后果責任的所謂“客觀證明責任”還是作為行為責任的所謂“證據提出責任”?)問題上。這個問題與通常所說的被告舉證的“程度”或“證明標準”有關。
1、《行訴》第54條第(一)項規定:“具體行政行為證據確鑿,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符合法定程序的,判決維持。”
根據這一規定,有學者指出:通常認為,我國行政訴訟的證明標準是“確鑿、充分標準”,即行政機關向法庭提供的其做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證據必須達到“確鑿、充分”的程度[13].更有學者明確指出了其背后的思想基礎:
“我國三大訴訟法有關證明標準的規定雖然在措辭上有所不同,但實際上實行的仍然是一元化的證明標準,即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我國證據制度是建立在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理論基礎之上的。根據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客觀世界是可以被認識的,同任何其他客觀事物一樣,案件事實也是完全可以被認識的。基于這一思想,我國學者通常都認為,只要辦案人員發揮主觀能動性,全面正確地收集和審查判斷證據,訴訟案件的事實真相是完全可以發現的。” [14]
2、與上述被告舉證的“程度”或“證明標準”相呼應,關于行政訴訟中被告所承擔的舉證責任的性質,一般的理解是它在本質上是一種作為后果責任的所謂“客觀證明責任”。如劉善春明確指出:
“在大陸法系國家如德國,客觀證明責任成為主導概念。所謂客觀舉證責任是指訴訟進行到終結,而爭議中的事實仍處于真偽不明狀態,由哪一方當事人負擔敗訴責任。這個定義,著眼于訴訟后果,而不是過程,應當說抓住了舉證責任的要害。行政訴訟完結,行政行為的事實根據和法律根據缺乏或不足,被告行政機關負敗訴責任,這才是舉證責任的本質。??????被告負擔后果責任,是行政訴訟舉證程序的啟動器或動力源,也是訴訟完結之后勝敗評判的準繩。就行政行為合法性舉證責任而言,行政訴訟中提供證據的責任以承擔后果責任為前提,只有承擔后果責任,才承擔提供證據的責任,不承擔后果責任,也就不承擔提供證據的責任。后果責任和提供證據的責任同時存在。承擔后果責任的被告,首先負有提供證據的責任。這是我國行政訴訟舉證責任的根本特征之一。”(下線筆者)[15]
另外,還有學者參照英美法系學者的理解,將舉證責任分為推進責任和說服責任,并把說服責任定義為“當事人提出證據使法官或者陪審團確信其實體主張成立的義務,否則必然遭受不利的裁判”[16],認為“《行政訴訟法》第32條規定,如果被告不能證明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合法,人民法院只能判決撤銷具體行政行為,這是說服責任。”[17].應該認為,這種觀點與劉善春的觀點相比,只是用語上有所不同,其內涵是一致的。
3、但是,或者說,無疑是不可能的。有學者這樣指出:
在很多情況下,案件事實達到百分之百的客觀真實對于訴訟活動而言,既是不需要的,也是不可能的。??????筆者認為,行政訴訟證明標準的確定,必須考慮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行政訴訟證明標準的中間性。行政訴訟的證明標準在總體上應當低于刑事訴訟而高于民事訴訟。第二,行政訴訟證明標準的審查性。行政訴訟證明標準的確定,必須考慮行政程序的證明標準。第三,行政訴訟證明標準的多元性。不同的行政案件所涉及的權益大小及所適用的程序繁簡各不相同,所要求的證明標準也不相同。由于行政訴訟證明標準與行政程序證明標準存在對應關系,行政訴訟證明標準自然也存在多元性。[18]
應當認為,這一觀點切中要害。問題隨之而來:
既然在一些場合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不可能在對案件事實取得百分之百確信的前提下才發動行政權力、作出具體行政行為,那么不得不說,在這些場合里,被告在行政訴訟程序中不可能負擔客觀證明責任。
4、在一些場合里被告不可能負擔客觀證明責任,有如下案例為佐證。
「案例2」《上海市收容遣送管理條例》(本件條例)規定,有關行政機關可以對“露宿街頭,生活無著的”實行收容遣送。
1993年某日,一個民警在巡邏時,發現男子(A)露宿街頭。民警上前詢問,A稱:剛從外地來滬打工,因尋工無著,又舉目無親所以暫棲街頭。民警所屬的公安分局將A送往上海市遣送站(被告)。被告接受A后,根據公安分局移交的材料和A本人的陳述,認定A露宿街頭,生活無著,作出將其收容遣送的決定(本件決定);同時向A居住地人民政府發電,通知其家屬來滬領回。
收容期間,A身體虛弱,不愿進食。工作人員幾次送他到醫務室和上海市第九人民醫院診治,未能查出病因。數日后,值班人員發現A已經死亡。
A的父親(原告)以A不屬于收容遣送對象為由起訴,請求撤銷本件決定。
在行政訴訟中,被告提供了相關筆錄和本件條例[19];原告則提供了確鑿的證據證明:A在上海有正常工作,不屬于本件條例規定的收容遣送對象。法院判決維持本件決定[20].
本案中,被告在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收容遣送決定)時所根據的事實認定并不符合客觀實際,其在行政訴訟中也沒能證明A確屬收容遣送對象。既然如此,如何理解本案中被告所應承擔的、關于本件決定的合法性的舉證責任呢?
5、在本判決里,被告對具體行政行為的要件(“露宿街頭,生活無著的”)認定所承擔的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客觀證明責任,而是證據提出責任。這一點應該是沒有異議的。問題在于,如何理解本案中被告的這種證據提出責任與《行訴》第32條規定的舉證責任的關系?如何將這種證據提出責任正當化?
筆者所接觸到的對于本案的評析,都沒有明確回答上述問題。有的評析將重點放在了本件決定的合法與否上,認為:被告接受公安分局移送的證據是A 露宿街頭的事實,被告對A進一步審查時,根據A本人陳述和分局移送的證據,只能推斷A系露宿街頭、生活無著的人;被告據此作出本件決定,于法有據、合情合理[21].有的評析雖然意識到本案在舉證責任問題上的特殊性,認為本案之所以會引發爭議,關鍵在于A在行政程序中的陳述與事實不符;并提起問題:“原告(在行政程序中稱為相對人)在行政程序中未舉證證明其行為合法,甚至作出虛假陳述,導致具體行政行為認定事實錯誤,在行政訴訟中敗訴責任應由誰承擔呢?” [22]同樣沒有回答筆者上面提出的問題。
6、毋庸諱言,如果將《行訴》第32條和第54條作整合性解釋,那么我國目前的行政訴訟舉證責任規定,沒有涵蓋被告在行政訴訟里不承擔客觀證明責任、只承擔證據提出責任的情形。與此相關,目前的學說或者沒有充分意識到這種情形的存在、或者沒有明確對其加以表述;有的判例如「案例2」雖然實際上減輕了被告的舉證責任負擔――相對于《行訴》第32條的上述通說性解釋而言――,但是對這種減輕沒有進行充分的說明。
二、問題的癥結
上面我們看到,我國目前的行政訴訟舉證責任規定,沒有完整地涵蓋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問題的基本方面。即,
(1)原告對具體行政行為違法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的情形
(2)被告在行政訴訟里不承擔客觀證明責任、只承擔證據提出責任的情形
與此相關,學說中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混亂,判例中存在著的問題。
筆者認為,我國行政訴訟舉證責任論的這種狀況,并非只是因為我國行政訴訟制度的歷史較短、關于行政訴訟的舉證責任問題的經驗積累在數量上比較有限;它實際上反映了我國行政訴訟舉證責任論在理論前提上存在著若干誤區。換句話說,這種狀況只是結果和表象,其背后有著深刻的理論原因。
(一)關于行政訴訟舉證責任與民事訴訟舉證責任的關系(固有還是特殊體現?)
1、在我國,行政訴訟法與民事訴訟法和刑事訴訟法一起,并列為國家三大訴訟法律部門[23].應該說,這種理解是對行政訴訟法在我國訴訟法律體系中的一種高度抽象的定位,有討論余地,但并不宜且不易直接證偽。問題在于,與這種定位相呼應,[24]這一觀點,在如今的行政法學界還頗有影響。而所謂的“很大的差異”一般被概括為 [25].
這一命題,很顯然,與前述的這一現象有著邏輯上的聯系。
2、其實,我國有的學者并沒有認為《行訴》第32條所規定的被告的舉證責任是行政訴訟所固有、與民事訴訟有著很大差異,也就沒有忽視原告對具體行政行為違法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這一情形的存在。如,姜明安于1993年在其所著的教科書中曾經這樣指出:
“被告對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是‘誰主張,誰舉證’的一般舉證責任原則在行政訴訟中的特殊體現。舉證責任的一般原則是誰主張,誰舉證,行政訴訟的舉證規則并不與這一規則沖突,因為行政訴訟主要是審查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而不是審查原告行為的合法性,??????被告如不能提供充分確鑿的證據證明自己的行為合法,法院就推定被告的行為違法,原告無須為被告的行為違法舉證。只有被告已提供了充分確鑿的證據證明了自己的行為合法以后,原告還主張被告行為違法,例如提出被告濫用職權,其行為侵犯了其合法權益,這時才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原告不能證明自己的主張,即要承擔敗訴的后果。所有這些,都并不違反‘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而恰恰是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的體現。”[26]
劉飛在1998年的論文中指出:
,忽視了“被告為其作出的行政行為負舉證責任”和“被告在行政訴訟中負舉證責任”的區別,否定了訴訟中舉證責任在雙方當事人之間的轉移;,將“被告對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負舉證責任”與“誰主張,誰舉證”相對立,因而是錯誤的。《行訴》第32條是基于行政訴訟制度的特性對“誰主張,誰舉證”這一舉證責任基本原則的重申。[27]
(劉飛沒有否定的情形的存在如前所述。一(一)5.)
3、而另一方面,還是有學者堅持認為:“我國行政訴訟應當繼續堅持被告承擔舉證責任的制度,摒棄‘誰主張,誰舉證’的主張”[28].――顯然,這種觀點與上述姜明安、劉飛的觀點是對立的。
4、筆者愿意這樣理解我國的行政訴訟舉證責任規定:《行訴》第32條的規定,是立法者基于我國國情以明確規定的方式對進行的特別強調。這種“特別強調性的重申”,既照顧了我國國情和行政訴訟的特性,又注意了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在舉證責任分配問題上的共性——正如《高院解釋》第27條第(四)項的兜底規定所顯示的那樣, 這一命題是成立的――無論是在法理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有其合理性。
但是,后來的《髙院規定》第6條,過度強調了被告的舉證責任。這種過度強調,與學說中的的觀點相呼應,導致了對原告所應承擔的(對具體行政行為違法的事實的)舉證責任的忽視。
(二)關于舉證責任的本質和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準(行政實體法還是行政訴訟法?)
1、要理解舉證責任的本質、進而明確其分配的標準,得從“訴訟”這一人類活動的特殊性談起。這是一個需要引用法哲學、法哲學史、法史學等方面的廣博的知識進行論述的極為復雜的問題,當然不是本文所能完成的。本文只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直接提示一個筆者認為爭議最少的結論:
到各個實體法里去尋找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準,提倡這種做法的代表人物當首推德國法學家羅森伯格(Leo Rosenberg)。他是這樣理解法的適用與舉證責任之間的關系的[31]:
(1)法規范只有在其要件事實實際發生時,才要求其命令的實現。
(2)但是,不能避免的是,當事人的證明有時并不能確實得足以說服法官。
(3)解決這一問題的是舉證責任。在事實主張的真偽難以確定的情況下,它指示法官應該如何判決。舉證責任規范的本質和價值就在于此。
(4)所以,舉證責任的理論是法律適用理論的一部分,舉證責任規范甚至可以與各個具體的訴訟無關地、從各個法條的抽象性命題中得出。
2、以羅森伯格為代表人物的、這一做法,依據的是這樣一種“舉證責任觀”:[32].
這種“舉證責任觀”在德國和日本乃至我國的臺灣一直處于支配地位。挑戰它的支配地位的,或者因為最后不得不回歸到實體法上來而反證了它的生命力(德國學者萊伊波爾特),或者并未引起多大反響而不得不自守其說(日本學者石田穰)[33].
從這一意義上講,作為法制后發展國家的我國,要想構建自己的行政訴訟舉證責任論,不可能也不應該跳過這一做法,因為它畢竟是一個到目前為止比較公認的、人類共同的智慧成果。
3、反觀我國目前的行政訴訟舉證責任論,馬上產生一個疑問:我國是在《行政訴訟法》這一實定程序法中對行政訴訟舉證責任作出了明確規定,相對于這一做法,是否屬于另辟蹊徑?
《行政訴訟法》雖然相對于各個行政實體法規而言屬于程序法范疇,但是,在這個程序法中作出某些實體規定也是可能的。這樣看的話,上述疑問還只是一種疑問。
關鍵在于我國的行政法學是如何論證《行訴》第32條的。
4、我國學者一般是這樣表述《行訴》第32條的主要理論和實踐依據的[34]:
(1)由被告方負舉證責任,有利于保護原告一方的訴權(與證據的距離)。
(2)由被告方負舉證責任,有利于充分發揮行政主體的舉證優勢(舉證能力與專業知識)。
(3)由被告方負舉證責任,有利于促進行政主體依法行政(“先取證,后裁決”)。
以上三點,(3)可以直接理解為一種一般的――在這個意義上――行政實體法規范,(1)和(2)則可以作為解釋各個行政實體法從而抽出其中的舉證責任規范時所必須考慮的要素。總體而言,從以上三點來看,上述疑問仍然只是一個疑問。盡管我們不能否認:我國的行政訴訟舉證責任論,從整體上看行政實體法的觀念比較淡薄;而且,在《行政訴訟法》中規定舉證責任,容易引起誤解。
(三)關于行政訴訟舉證責任論的存在形式(統一規定還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我國是在《行政訴訟法》這一實定程序法中對行政訴訟舉證責任作出了明確規定的,這是否意味著我國實際上已經放棄了的做法而另辟蹊徑?――如上所述,由于《行訴》第32條也可以理解為一個行政實體法規范,這還只是一個疑問。我們不能用它來責難這一做法。
1、但是,我們必須注意,這一做法本身,存在著一種危險:用一般的行政法原則代替各個具體的行政實體法來規定舉證責任,極有可能導致一刀切,迫使法官在某些類型的行政案件的裁判中不得不采用與《行政訴訟法》的舉證責任規定不盡整合的舉證責任分配。
應該說,「案例2」就是這種危險變成了現實的典型。
2、在訴訟法中規定舉證責任這一做法,從世界各國的立法實踐來看,是比較少見的。
1877年1月30日制定的德國民事訴訟法,在立法過程中雖然曾經試圖對舉證責任分配法則進行明確規定――等等――,但最后那些規定都被刪除了[35].1935年的中國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和匈牙利民事訴訟法第269條雖然明確規定了舉證責任分配法則――其內容與1877年德國民事訴訟法草案中的舉證責任規定類同――,但是,由于實際的舉證責任的分配最后還不得不到實體法中去尋找線索――如,是某一事實的存在(如善意)使權利成立,還是該事實的不存在(即惡意)妨礙權利的成立?――被認為并無多大實際意義[36].
3、是否在訴訟法中規定舉證責任?由于兩者各有利弊,其選擇依據立法者的衡量和判斷:是使舉證責任分配有法可依、以避免學說和判例的混亂?還是從舉證責任問題的性質出發而預留下靈活柔軟的解釋空間、以避免一刀切?[37]
可以推測,我國《行訴》的立法者和司法解釋的制定者選擇了前者。
應當認為(參見前述二(一)4),這種選擇在行政訴訟法制度初創、理論有待發展、知識有待普及的特定國情下,有其合理性。但是,這種選擇必然伴隨著導致一刀切的風險。
4、從我國《行政訴訟法》到目前為止的執行情況來看,在訴訟法中規定舉證責任,除了必須冒一刀切的風險之外,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雖然努力地追求全面、不斷地補充和修改舉證責任規定(主要是以司法解釋的形式),但還是難免遺漏。因為各個行政實體法情況各異,無法窮盡列舉。
5、所以,那種認為還應該繼續對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問題作出明確立法規定的主張[38],是有商榷余地的。
(四)關于原告的訴權保護與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分配的關系(訴權還是法秩序?)
1、以上的所有考察,最后都可能面對一個非常嚴厲的反問:主張行政訴訟的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在本質上與民事訴訟并無差異,結果必然是承認 的情形的存在;主張,無非是要涵蓋 的情形;主張舉證責任規定存在本身有討論余地、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分配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無非是要為正當化的情形預留下解釋空間。既然如此,這些主張,難道不妨礙對原告的訴權的保護嗎?難道不妨礙行政訴訟的制度目的的實現嗎?
實際上,有學者從保護原告訴權的目的意識出發,主張“確定被告承擔舉證責任的舉證責任制度,摒棄‘誰主張,誰舉證’的主張,仍然是現階段我國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制度的最佳選擇。”甚至認為:強調或過分強調原告的舉證責任,在行政權力過于膨脹的今天,會使行政訴訟出現扭曲,甚至出現對行政訴訟宗旨的嚴重違背;《高院解釋》第27條第(四)項的兜底規定并不妥當[39].
應當認為,這種觀點與本文的主張所可能遭遇的反問其宗旨是一致的。也就是說,上述“反問”也許并非只是筆者的假設。
2、“反問”的出發點無可非議。如前所述,本文把《行訴》第32條的規定解釋為是對“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的“特別強調性的重申”,這意味著本文也認為,立法者在《行訴》第32條里表達了一個很強烈的意志:要通過制定舉證責任規定實現保護原告的權利的制度目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反問”在出發點上與《行訴》的立法精神是一致的。
3、但是,如前所述(二(一)4),《行訴》第32條的規定可以理解為是對“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的“特別強調性的重申”,既照顧了我國國情和行政訴訟的特性,又注意了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在舉證責任分配問題上的共性――并沒有排除的情形的存在;同時,在邏輯上,由于“舉證責任”既可以理解為“客觀證明責任”又可以理解為“證據提出責任”,也可以說并沒有排除的情形的存在――.在這個意義上,毋庸諱言,“反問”與《行訴》的立法精神相一致的,也只是在其出發點上。
4、另一方面,如下的對“反問”的反駁也是成立的。
首先,“反問”本身并不見得有利于保護原告的訴權。因為,行政訴訟舉證責任的分配是由各個行政實體法的規定推導出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是客觀的;法院并不會也不應該從保護原告訴權的良好愿望出發無視行政實體法的規定、無視國家的法秩序而免除原告的舉證責任或者在任何情況下都堅持由被告行政機關負擔客觀證明責任,「案例1」和「案例2」中法院的判斷就是例證。既然如此,在法學理論中抽象地談論由被告單方面承擔舉證責任、或者在行政訴訟舉證責任規定中明示原告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承擔對具體行政行為違法的事實的舉證責任,反而有一種誤導的嫌疑,可能使相對人疏于證據的收集和保全。
其次,承認的情形、的情形的存在,并不等于不要保護原告的訴權。法秩序是客觀的,把客觀的法秩序充分地予以揭示,這本身就是對法律的可預見性的一種貢獻,有利于原告通過行政訴訟實現其權利。
何況,如后所述,通過對行政實體法的解釋對的情形乃至的情形加以認定時,是要考慮行政行為的性質、關系人與證據的距離等要素的;換言之,本文的主張把保護原告的訴權的目的意識和操作要素預設在各個行政實體法的解釋中了。
三、解決的方策
找到了問題及其癥結,下一步就是考慮如何解決它。筆者認為,以下的工作――轉變觀念和引進概念――在目前是必要的:
(一)不要過于強調與民事訴訟相比行政訴訟舉證責任的特殊性。
如前所述,過于強調行政訴訟及其舉證責任的特殊性,容易忽視行政訴訟中原告所應承擔的關于具體行政行為違法性的舉證責任。
(二)回歸到各個具體的行政實體法規范
為了把法官從在「案例2」里所遇到的那種窘境里解脫出來,我們應該到各個具體的行政實體法規范中去尋找適合于各個行政案件的舉證責任分配基準。比如,行政處罰案件,我們要到《行政處罰法》等行政法規中去尋找;行政許可案件,我們要到規定了該許可行為的行政法規中去尋找;收容遣送案件,我們要到規定了該收容遣送行為的行政法規中去尋找。
這里需要特別強調的是,行政訴訟舉證責任論應該回歸到各個具體的行政實體法規范,并不意味著制定統一的行政訴訟舉證責任規定(主要是司法解釋)毫無意義。如前所述,應當認為,在行政訴訟法制度初創、理論有待發展、知識有待普及的特定國情下,在實定法(包括司法解釋)中以一般性的行政法原則為依據對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做出一定限度的統一規定,有著相當的現實意義。
本文只是在肯定這種現實意義的同時,提醒行政訴訟舉證責任規定的制定者:這種做法伴隨著一刀切的危險,并且不利于與國際接軌。況且,可以想見,隨著判例公開制度的完善,司法解釋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判例來完成。
還需要贅言一句:回歸到各個具體的行政實體法規范,意味著我們必須把實際分配行政訴訟舉證責任的任務交給處于審判第一線的法官,把說明、指導、監督法官的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分配的任務交給學者。也許會有同志以“有可能引起混亂”為由表示反對,但如前所述,由法官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地分配行政訴訟的舉證責任,符合法理和時代趨勢,是遲早的事情。這種信任是必須的也是應當的。
(三)導入(行政機關的)“調查義務”概念
上面我們看到,在「案例2」里,行政機關所承擔的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客觀證明責任,而是證據提出責任。如何將這種證據提出責任正當化是該判決留給我們的作業。
要想正當化行政機關所承當的證據提出責任,我們需要引進一個工具概念:行政機關的“調查義務”。把調查義務概念導入行政訴訟舉證責任論,這一做法的首倡者是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小早川光郎。他主張:
為了避免特定關系人的利益受到違法侵害,行政機關應該在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進行充分的調查研究。這是行政機關在誠實地執行立法的過程中對該關系人所承擔的義務。我們稱其為“行政機關的調查義務”[40].
一般而言,被告行政機關應該在其對該相對人所承擔的調查義務的范圍內,對具體行政行為的要件事實、關于行政主體本身的權限的事實、具體行政行為所應遵守的行政程序和形式等負舉證責任[41].而另一方面,行政機關在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不一定在任何情況下都承擔對進行積極調查的義務,也不一定在任何情況下都承擔對進行積極調查的義務[42].對于這些事項,舉證責任需要另行分配[43].
從引文中可以看出,“調查義務”這一概念,既可以成為減輕被告行政機關的舉證負擔的工具,也可以成為行政程序中行政機關的調查取證活動與行政訴訟中(被告)行政機關的舉證活動之間的媒介。在行政程序中的舉證責任與行政訴訟中的舉證責任之間的內在聯系日益受到重視[44]的今天,其價值是顯而易見的。
下面嘗試用“調查義務”這一概念來論證「案例2」中被告所承擔的證據提出責任。
被告作出本件決定是基于這樣的事實認定:A屬于“露宿街頭,生活無著的”(本件條例規定的收容遣送對象之一)。而“露宿街頭,生活無著的”的認定包含著很復雜的問題。第一,在邏輯上,它應該包含著兩個步驟:(1)看相對一方是否露宿街頭;(2)看相對一方是否生活無著。第二,這兩個步驟,需要復雜的判斷過程來完成:(1)“露宿街頭”是一個直觀事實,很容易認定,但它在決定是否實施收容遣送的判斷過程中不過是一個起點、并非關節點――主管行政機關(民警)不可能也不應該收容并遣送每一個他所見到的露宿街頭的人,有的人甚至可能只是醉酒不歸家而已。(2)“生活無著”是關節點,它的認定卻很復雜 ――要想認定它,需要了解相對一方在本市是否有正常工作、是否有正當生活來源等情況,而這些情況,其信息源在相對一方,主管行政機關要想了解這些情況,只能通過察看身份證、工作證、口頭或電話詢問等手段進行調查;而這種調查因為涉及到“尊重相對一方的人格”等與人權相關的問題,如何掌握調查的“度”是個關鍵。
決定調查的“度”的關鍵要素是調查的目的行為的性質(在本案中是收容遣送行為,在其他案件中可能是行政處罰行為或稅收行為等)。一般而言, “侵害行為”與“授益行為”相比,其調查的“度”要高――因為“侵害行為”蘊含的危險更大,不得不更加慎重。本件決定性質比較復雜。一方面,它意味著(為了維護大城市的治安、人文環境)要對相對一方的人身自由進行一定的限制,從這個意義上講,具有“侵害行為”的屬性;另一方面,它還意味著行政機關(為了保護“生活無著”等處于困境的人的基本人權)向處于困境的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資料和其他人道主義救助,從這個意義上講,它又有“授益行為”的屬性[45].收容遣送決定行為的這種“授益行為”的屬性大大地調低了行政機關在作出該行為時進行調查的“度”。
從該類行為的性質來看,應該認為:行政機關只要(1)看到相對一方露宿街頭,(2)經任意的而不是強制的證件驗看和詢問、獲得相對一方的關于“生活無著”的本人陳述,即完成了其調查義務,可以據此作出收容遣送決定。
本案中,被告提供了相關筆錄,應當認定:被告已經在其(在行政程序中對相對一方所承擔的)調查義務的范圍內進行了充分的舉證;本件決定在這個限度內是合法的(如果原告還主張本件決定違法,必須承擔相應的舉證責任)。
在以上“嘗試”里,被告行政機關對具體行政行為(本件決定)的要件事實所應承擔的舉證責任(證據提出責任而非客觀證明責任),通過調查義務這一媒介概念,從行政實體法(本件條例)直接推導了出來。同時,原告對具體行政行為違法的事實所應承擔的舉證責任,也在邏輯上得以預置。
四、結論與課題
(一)結論
1、回答“在行政訴訟中,舉證責任應該如何分配?”這一問題的、本文的核心論點是:
在對行政訴訟本案審理階段(原告的起訴符合法定起訴條件,行政訴訟進入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司法審查的階段)的舉證責任進行分配時,首先應該通過對各個行政實體法進行解釋(解釋時,需要考慮具體行政行為的性質、關系人對證據的距離等因素),根據該行政實體法對行政機關的拘束程度來明確行政程序中行政機關對相對人所承擔的調查義務的范圍,進而據此決定行政訴訟中被告行政機關所應承擔的舉證責任的性質(是客觀證明責任還是證據提出責任)和范圍(是局限于要件事實、行政程序事實,還是擴大到其他事實,比如關于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等要考慮事項的事實);在此基礎上,結合原告的主張和其所提出的證據,確定原告對具體行政行為違法所承擔的舉證責任及其范圍。
2、這一論點力圖回到舉證責任問題的理論原點,從這一“舉證責任觀”出發,主張,具體而言是。這是其基本理論前提。
與之相應,這一論點從、這一“行政實體法拘束程度觀”出發,從正面承認的情形的存在,進而導入“(行政機關的)調查義務”概念,用它來把與聯系起來。這是其基本理論特征[46].
同時,這一論點并不認為關于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或違法原告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承擔舉證責任、或者說只由被告一方承擔舉證責任。換言之,這一論點從正面承認的情形的存在。這并非本文的獨家見解――如前所述,很多學者認為有時原告是要承擔對具體行政行為違法性的舉證責任的。
3、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本文的核心論點雖然不主張在行政訴訟法和司法解釋里作出統一的舉證責任規定,但是,其本身并不與現行舉證責任規定的基本部分相矛盾。即,《行訴》第32條所規定的“舉證責任”既可以解釋為客觀證明責任又可以解釋為證據提出責任――如何將《行訴》第32條和第54條作整合性解釋是另外一個問題――、而且它沒有排除原告對具體行政行為違法的事實的舉證責任。
換言之,盡管是否制定舉證責任規定這一問題本身有商榷余地,但是,只要實際制定的舉證責任規定預留下足夠的解釋空間以避免一刀切,考慮到我國的特殊國情,不妨予以保留甚至繼續制定。當然,預留下足夠的解釋空間意味著規定的抽象程度比較高,這很可能有違“使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分配有法可依”的初衷,但這是屬于立法技術范疇的另外一個問題。
但是,毋庸諱言,《髙院規定》第6條明顯容易引起誤解,本文的核心論點無法與之整合。
4、如上所述,盡管本文的核心論點在一定程度上與現行舉證責任規定是可以整合的,在一些方面與現存的各種學說也有著這樣那樣的一致,但是,應該說,本文的核心論點在基本理論前提上和基本理論特征上,都與我國目前的行政訴訟舉證責任論(包括行政訴訟舉證責任規定)有著較大差異。從這個意義上,筆者斗膽稱其為“重構”。
(二)課題
1、本文針對我國行政訴訟舉證責任論目前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這些見解,產生于筆者在日常的教學實踐中對我國的行政判例和對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基本理論的思考,同時,還借鑒了日本以及德國的相關理論。應當承認,日本的行政訴訟制度與我國存在著比較大的差異,這種差異――比如――有可能影響到舉證責任問題,有的學者明確指出:
“在行政訴訟中,原告承擔的舉證責任屬于程序性的推進責任,還是實體性的說服責任其實很難分清。這與一國的法制狀況、當事人的舉證能力等等有相當大的關系。總體而言,奉行當事人主義的國家,原告既承擔推進責任,也承擔一些說服責任;而奉行職權主義的國家,原告一般承擔的是推進責任。我國屬于后者。”[47]
在引文里,我國的行政訴訟制度被理解為采用了職權主義,同時,原告所承擔的舉證責任的性質被理解為“推進責任”。筆者認為,關于我國的行政訴訟制度是采用了職權主義還是采用了當事人主義、以及應該采用兩種主義中的何者,需要進一步思考和討論。
2、另一方面,本文將考察的范圍限定于行政訴訟的“本案審理”階段(原告的起訴符合法定起訴條件,行政訴訟進入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司法審查的階段),而實際上,行政訴訟的“要件審理”階段(法院審查原告的起訴是否符合法定起訴條件的階段)與“本案審理”階段存在著內在的關聯性 [48],把兩個階段中的舉證責任問題合在一起進行考察,有助于對行政訴訟的過程進行全面、充分的描述和說明,比如,對前述劉飛所指出的“訴訟中舉證責任在雙方當事人之間的轉移”的現象進行描述和說明。
但是,將行政訴訟的“要件審理”階段和“本案審理”階段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需要從若干在我國現階段也許不被認可的理論前提――如――出發,導入“行政法上的請求權”或者“撤銷請求權”等概念。這一伴隨著復雜的理論問題的作業不是本文所能完成的,只能留待它日另文討論了。
注釋:
[1]參見:馬懷德主編《司法改革與行政訴訟制度的完善――修改建議稿及理由說明書》代序(馬懷德執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
[2]張鑾英、王琦《行政訴訟的證據規則及其運用》,羅豪才主編《行政審判問題研究》第十五章,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224頁。
[3]楊芳、陳雁凌《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倒置制度評價》,《行政與法》2003年第9期第81頁。
[4]參見:姜明安著《行政訴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8月,第143-145頁。
[5] 參見:方世榮主編《行政訴訟法案例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案例66.
[6] 本案中,《查處通知》以“(相對人)是否已對外接盤、下單”為基準對外匯管理部門與工商管理部門的權限進行了劃分。“(相對人)是否已對外接盤、下單”的認定,盡管與行政主體的權限有著密切關系,但是從事物的性質來看,應該是由主張其存在的一方即原告來證明的事項。因為,舉證的必要性存在于主張一方而不是否定的一方(necessitasprobandiincumbiteiquidicitnoneiquinegat)(參見: Nicholas.Rescher,Dialectics:AControversy-OrientedApproachtothe TheoryofKnowledge,NewYork,1977. 日譯本(內田種臣譯《對話的邏輯――辯證法再考》紀伊國屋書店1981年)第50頁。)另一方面,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對超出經營范圍進行經營活動的企業作出行政處罰的權限,已經在其它行政法規中規定,從這個意義上講,本案中被告原則上擁有行政處罰權,只有在《查處通知》這一特別規定所規定的例外的事實(“(相對人)是否已對外接盤、下單”)發生的情況下,其行政處罰權才轉移給外匯管理部門。也就是說,對被告的行政處罰權成立與否而言,“(相對人)是否已對外接盤、下單”這一事實屬于權利消滅要件事實。基于以上兩個理由,筆者認為,本案中法院就“是否已對外接盤、下單”這一事實向原告求證、在原告沒有提供相應證據的情況下判決其敗訴是可以首肯的。
[7] 參見:姜明安主編《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0月,第348頁(劉恒執筆)。
[8] 參見:馬懷德主編《行政訴訟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4月,第265頁(王萬華執筆)。
[9]劉善春:《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分配規則論綱》,《中國法學》2003年第3期,第72頁。
[10] 劉飛《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分析》,《行政法學研究》1998年第2期,第53頁、第98頁。
[11]張樹義主編《行政訴訟證據判例與理論分析》,法律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17頁、第127頁。
[12]趙紅偉、劉偉《行政訴訟舉證責任的新視角》,《行政與法》2003年第4期,第73頁。
[13]夏立彬《行政訴訟中的舉證責任及證明標準》http://www.law-lib.com/lw/lw_view.asp?no=3029.
[14] 馬懷德、劉東亮《行政訴訟證據問題研究》,《證據學論壇》第4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2年。
[15]前揭劉善春《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分配規則論綱》第69頁。
[16]前揭張樹義主編《行政訴訟證據判例與理論分析》第115頁。
[17]前揭張樹義主編《行政訴訟證據判例與理論分析》第117頁。
[18]前揭馬懷德、劉東亮《行政訴訟證據問題研究》。
[19] 關于規范性文件是否為證據,有討論余地。本文對此暫且予以擱置,留待他日詳論。
[20] 參見:前揭張樹義主編《行政訴訟證據判例與理論分析》第三章案例5;最高人民法院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編《人民法院案例選行政卷(1992年-1996年合訂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4月,案例137.
[21] 前揭《人民法院案例選 行政卷(1992年-1996年合訂本)》第776頁。
[22]前揭張樹義主編《行政訴訟證據判例與理論分析》第137頁。
[23]參見:前揭姜明安主編《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第300頁(王寶明執筆)。
[24]參見:前揭姜明安主編《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第347頁(劉恒執筆)。
[25]參見:前揭姜明安主編《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第347頁(劉恒執筆)。
[26]前揭姜明安著《行政訴訟法學》第145頁。需要注意的是,姜明安在被告的舉證前面加了一個限定語“充分確鑿”。筆者更愿意認為,由于他在此論述的并非被告的舉證責任的性質或者證明標準問題,他使用這一限定語只是出于一種書寫習慣。
[27]前揭劉飛《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分析》第51-53頁。
[28]前揭馬懷德主編《司法改革與行政訴訟制度的完善》第219頁(執筆者不詳)。
[29]參見:(日)兼子一著《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講座第2卷》有斐閣1954年,第571頁。
[30]參見:前揭(日)兼子一著《舉證責任》第575頁。
[31]Leo Rosenberg,Die Beweislast 5.Aufl.(1965)S.1-3. 參見(日)春日偉知郎《證明責任論的一個視點——從西德證明責任論得到的啟示》,判例Times第350號第102頁。
[32]參見:畢玉謙《舉證責任分配體系之構建》法學研究1999年第2期第51頁。
[33] 參見:前揭畢玉謙《舉證責任分配體系之構建》第57頁。
[34] 參見:前揭姜明安主編《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第348頁(劉恒執筆)。
[35] 參見:(日)龍崎喜助《舉證責任論序說(一)――德國舉證責任論中的行為責任和后果責任的交錯》,《法協雜志》第92號第1457-1458頁。
[36]前揭(日)兼子一著《舉證責任》第573-574頁。
[37]參見:前揭(日)龍崎喜助《舉證責任論序說(一)》第1458頁。
[38]參見:前揭張樹義主編《行政訴訟證據判例與理論分析》第151頁。
[39]前揭馬懷德主編《司法改革與行政訴訟制度的完善》第221-222頁(執筆者不詳)。
[40] (日)小早川光郎《調查??處分??證明――撤銷之訴中的證明責任問題的一個考察》,《雄川一郎先生獻呈論集行政法的諸問題 中》有斐閣1990年,第267頁。
[41] 前揭(日)小早川光郎《調查??處分??證明》第271-272頁。
[42] 前揭(日)小早川光郎《調查??處分??證明》第277頁。
[43] 前揭(日)小早川光郎《調查??處分??證明》第273-274頁。
[44] 比如,劉善春??前揭《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分配規則論綱》第70頁明確提出:“行政程序中的舉證責任分配基本決定了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分配”;余凌云周云川《對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分配理論的再思考》認為“行政訴訟舉證責任是行政執法程序證明責任的延續和再現”。
[45]關于收容遣送行為的性質,參見前揭《人民法院案例選行政卷(1992年-1996年合訂本)》第775頁。
[46] 主張“行政訴訟證明標準的差別適用體系”的觀點是存在的,但這種觀點沒有明確提示“證明標準差別適用”的依據,盡管其具體的論述中實質上將行政行為的性質列入了考慮要素。參見王曉杰《行政訴訟證明標準的重構》行政法學研究2004年第2期;前揭馬懷德、劉東亮《行政訴訟證據問題研究》。
[47]前揭張樹義主編《行政訴訟證據判例與理論分析》第121頁。
[48]參照:(日)遠藤博也《對行政法上的請求權的一個考察》,《北海道大學法學論集》第38卷第5??6合并號(1988年),第15-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