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尚武愛國教育思想及現(xiàn)代啟示探討
佚名
【摘要】人才是強軍之本、安國之基;國防教育事業(yè)是立將之本,治軍之基。國防教育事業(yè)的核心價值理念是培養(yǎng)合格的治軍用戰(zhàn)的“將才”(即將兵之才)。國防教育事業(yè)興則將才興、軍隊興、國防興,一興俱興。因此,借鑒孔子的“教戰(zhàn)”思想,既要對全體國民加強國防教育,提升全民族的尚武愛國精神;同時,又要辦好軍校和國防生培育基地,培養(yǎng)更多的時代需要的治軍用戰(zhàn)的優(yōu)秀人才。
關于孔子的尚武精神,梁啟超在《中國之武士道》一書中已有闡發(fā)。孔子不僅尚武,而且是尚武教育理論的開拓者和實踐者。[1]孔子一生不輟地教授軍事、培育將才,將其尚武思想與教育思想相結合,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尚武愛國教育思想體系,對當代人文教育具有重要時代價值。
一、安邦強國勿忘“足兵”
尚武愛國教育實質上是一種國防教育。增強受教育對象的國防觀念和正確看待國防和軍人的價值,是尚武愛國教育的首要任務。孔子把國防實力納入綜合國力體系,視“足兵”為安邦強國之要本,體現(xiàn)了他從國家安全的戰(zhàn)略高度出發(fā),對國防建設的高度重視,對軍人價值的承認、肯定與尊重。孔子時代,民族矛盾、階級矛盾、政治集團與政治集團之間的矛盾不僅客觀存在,而且不斷激化。戰(zhàn)爭正是解決這些矛盾的最高形式。只要這些矛盾存在,戰(zhàn)爭就有可能發(fā)生。孔子正是基于對戰(zhàn)爭(特別是攻伐戰(zhàn)爭)的不可避免性及其嚴峻的戰(zhàn)事形勢的客觀分析,提出了“足兵”的思想。據《論語?顏淵》載: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足食”在于增強經濟實力,“足兵”在于增強國防實力,“民信”在于增強國民凝聚力。這三者既有區(qū)別,又有聯(lián)系,是構成了三位一體完整的綜合國力體系。顯然,孔子的“足兵”說,是對國防和軍人價值戰(zhàn)略定位的理性把握,具有核心戰(zhàn)略意義。在這個問題上,孔子與兵圣孫武不謀而合。與孔子同時代、年齡稍幼于孔子的孫武曾斷言警世:“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2《]管子?參患》說:“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國家與政權的得失存亡,民族與人民的安危禍福,無不系之于“兵”。孔子不僅從理論上、而且用事實解讀了“兵”在安邦強國中的價值地位。“足兵”既不是軍備的可有可無,也不是一般地養(yǎng)兵,而是強調要有充足的武備力量,使之足以維護政權,保衛(wèi)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防止和消除內亂外患,實現(xiàn)和捍衛(wèi)和平。“足兵”的價值在于滿足安邦強國的需要;同時,也只有這樣的能夠滿足國民安全需要之“兵”,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足兵”,才具有最大化的現(xiàn)實價值。誠然,孔子也有“去兵”的表示,但這是有條件的。據《論語?顏淵》載:“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可以看出,孔子并非愿意主動“去兵”,只是在“足兵”與“足食”、“民信”發(fā)生激烈價值沖突,而又必須做出戰(zhàn)略性選擇時,為了確保“食”與“信”的價值實現(xiàn),“去兵”才成為不得已而為之的權宜之計。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的“去兵”并不是取消武備。在這個問題上后人多有誤讀。“去兵”可有兩種釋義,一是消除武備存在的空間,即不要兵;二是在一定條件下提升武備的緊迫性和速度,被限制在“足食”、“民信”之下,即三者只有先后之別,提升的速度與比例有快慢多寡之別,但并非顧此失彼,或是一定要削弱“武備”,降低國防實力的絕對值。從“足兵”到“去兵”的問對邏輯可以看出,孔子“去兵”之意當是后者。可見,孔子“去兵”的本意既不是弭兵,也不是要削弱國防實力,而是把發(fā)展經濟、提升國民凝聚力放在更為優(yōu)先的戰(zhàn)略地位;同時,也只有這樣不得已而為之的暫時“忍耐”性的“去兵”,才能更好地凝聚力量發(fā)展經濟(即足食、民信),進而也更有效地實現(xiàn)“足兵”。孔子所謂的“去兵”,實際上正是其“足兵”說的一大閃光之處。它揭示了這樣一條真理:“足兵”必須以經濟實力和國民凝聚力為基礎。孔子的這一思想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有其重要的實踐價值。孔門師生“足兵”“去兵”的問對,蘊含著“重點論”的思想。但是“重點”與“非重點”始終存在著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同一性。孔子的“去兵”論是鑒于對常態(tài)下的“重點”分析。這就是說,在情況變化了的特殊歷史條件下,以“足兵”為重點也是應當而且必然的。
二、報效祖國人人有責
在孔子的價值視域里,為祖國而獻身是每個公民應盡的責任和最高的價值實現(xiàn)。孔子就是一個身體力行的愛國主義者。孔子視祖國為“父母之國”,以對祖先、父母的敬愛之心愛之,并教育弟子要為祖國而獻身。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公元前486年,齊國欲發(fā)兵犯魯,孔子得知后,動情地指教弟子說:“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所謂“墳墓所處”之國就是“祖上之國”,亦即“祖國”,與“父母之國”聯(lián)系在一起解讀,就是“祖國母親”之意。母親的安全受到威脅,兒女們必當挺身而出;“祖國母親”安全受到威脅,祖國的兒女們也應當而且必須挺身而出。這是孔子的邏輯。弟子們聽了老師的訓教,很受感動,一致表示共赴國難。“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孔子最終選中了軍事外交家子貢出使齊國周旋,終于止息了“齊魯之戰(zhàn)”,保證了“祖國母親”的安全。孔子身體力行,為人師表,給學生樹起了一面愛國主義的旗幟。在孔子看來,愛國是最崇高的仁德,具有超越其它一切禮儀道德規(guī)范的本質定性。孔子之“仁”,其本質是“愛”;但“愛”有層次之分。《國語?晉語》中說:“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管仲初相公子糾,后轉而輔佐迫死公子糾的齊桓公,弟子們有疑,問孔子“管仲非仁者與?”孔子不無肯定地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fā)左衽矣。”(《論語?憲問》)。在孔子看來,管仲盡管沒有為公子糾本人“盡忠”,但是能助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人民得到好處,使國家免于外族侵撓、征服,這不就是最大的仁德嗎!孔子雖然主張“克己復禮為仁”,可是當愛國之“仁”與通行之“禮”發(fā)生矛盾時,孔子卻毫不猶豫地主張違禮、變禮,以實現(xiàn)和彰顯愛國之“仁”的價值。據《左傳》載,一次齊國攻打魯國,魯小僮汪锜乘車參戰(zhàn),為國捐軀,魯國人便破格以成人葬禮安葬小僮。對這種明顯的違反葬禮的行為,孔子不但不反對,反而積極支持,為其辯護,高度評價小僮之死,他說:“能執(zhí)干戈以衛(wèi)社稷,可無殤也。”(《哀公十一年》)。就是說,小僮是為保衛(wèi)國家而犧牲的,不是一般孩童早夭,所以可以不按小孩的葬禮行事。這反映了孔子把國家的利益看得比“復禮”重要得多;同時也生動地說明,為祖國利益而獻身者,具有至高無上的人生價值和榮譽。從孔子訓導弟子、高度褒獎管仲和小僮來看,無論官、民、老、幼,報效祖國是每一個國民應盡的責任和義務,可謂“祖國興亡,人人有責”。足見其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源遠流長。
三、善教民戰(zhàn)寓兵于民
“教戰(zhàn)”是提升戰(zhàn)斗力的基本途徑,也是“仁者愛人”的具體體現(xiàn)。孔子強調,凡是從軍作戰(zhàn)的人,必須經過長期的教育訓練。他說:“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戰(zhàn),是謂棄之。”(《論語?子路》)。孔子時代,軍事技術有了長足發(fā)展,殺傷力顯著增強,戰(zhàn)爭規(guī)模日益擴大,職業(yè)軍人隊伍迅速膨脹,戰(zhàn)陣傷亡人數急劇增加,“智”日益取代了“禮”在戰(zhàn)爭中的地位。據史書載:公元前632年的晉、楚城濮之戰(zhàn)時,晉投入兵力約2萬余,戰(zhàn)車700乘。至公元前529年(即孔子22歲時),各國諸侯平丘之會時,晉國為了震懾諸侯,出動戰(zhàn)車達4000乘,兵力約12萬。因此,要滿足大規(guī)模戰(zhàn)爭對兵員數量和素質上的需求,必須在更廣泛的國民層面上實施較長時期的軍事教育訓練。所謂“教民七年”,是對“以不教民戰(zhàn)”或短暫教民亦可“即戎”的否定。孔子在這里所說的“民”,顯然不是指軍人,而是“即戎”之前的平民,如同他所教授的“有教無類”的弟子一樣,至少是預備役人員,實有“寓兵于民”之意。也許孔子是借助西周時的經驗。西周時期,由于生產力和軍事技術等條件的限制,沒有職業(yè)軍隊,所實行的是“寓兵于農”、“兵農合一”的民兵制。至孔子時代,隨著生產力的發(fā)展、井田制的崩潰和郡縣制的產生,征兵制代替了民兵制,各諸侯國普遍建立了職業(yè)化的常備軍。常備軍的建立,導致兵民分離,民的軍事素質急劇下降,即兵源素質的下降。這與戰(zhàn)爭對兵員的需求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在這樣的背景下,孔子順應軍事革命的潮流,面對國防建設出現(xiàn)的新情況、新問題、新矛盾,提出“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的主張,是有遠見卓識的戰(zhàn)略性政見。先教后用,寓兵于民是孔子“足兵”“教戰(zhàn)”思想的重要內涵,對后世、對今天都具有重要的戰(zhàn)略意義和普遍的價值導向意義。它告誡世人:“教戰(zhàn)”尚武不只是軍人的事,而是全體國民共同的價值擔當;在建立發(fā)展常備軍和軍事國防現(xiàn)代化的條件下,對全體國民的軍事教育和訓練不但不能削弱、放棄,而且必須更加重視和強化。因為,全民族的尚武精神和應戰(zhàn)能力,是最偉大的戰(zhàn)斗力,只有經過長期“教戰(zhàn)”養(yǎng)成良好尚武精神氣質和軍事素質的國民,才符合戰(zhàn)爭的需要。這既是贏得戰(zhàn)爭勝利的重要保證,也是對國家的安全、對國民生命的極端負責。
四、教授軍事,培育將才
將帥的軍事素質是實現(xiàn)安國的首要因素。孔子順應歷史潮流,從時代對人才的需求出發(fā),私人辦教育,教授弟子軍旅之術,培養(yǎng)治軍安邦的將才,堪稱是“將才先師”。孔子的尚武愛國教育思想體系有兩大組成部分:一是武德思想教育,如保衛(wèi)“父母之國”的愛國主義教育,正義戰(zhàn)爭觀(“仁戰(zhàn)”觀)教育,智、仁、勇兼?zhèn)涞奈涞氯烁窠逃龋欢俏幕逃c軍事技術教育相結合,他的教學內容是禮、樂、射、御、書、數,這六藝中就有“射”、“御”兩大軍事科目。對于培養(yǎng)軍事人才來說,禮、樂、書、數是文化基礎科目,射、御是專業(yè)技術科目。兩大科目相結合,學文習武,文武相濟,是孔子培養(yǎng)人才的顯著特色。《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有“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這七十二位“身通六藝”的弟子,當然對于射、御也必然是精通的。其他近三千弟子,雖然不及七十二高徒,但是必定也接受過孔子“六藝”的教育訓練,因而也必然不同程度地掌握了一些射、御等軍事技能。時代需要軍事人才,人才需要教育培養(yǎng)。孔子走在了時代的前列。試想,孔子的教育若不能滿足當時時代的需要,怎么可能會出現(xiàn)那么多的弟子云集于門下的教育盛況呢?又怎么會有那么多的弟子成為軍事精英人物呢?

.jpg)
大學學報.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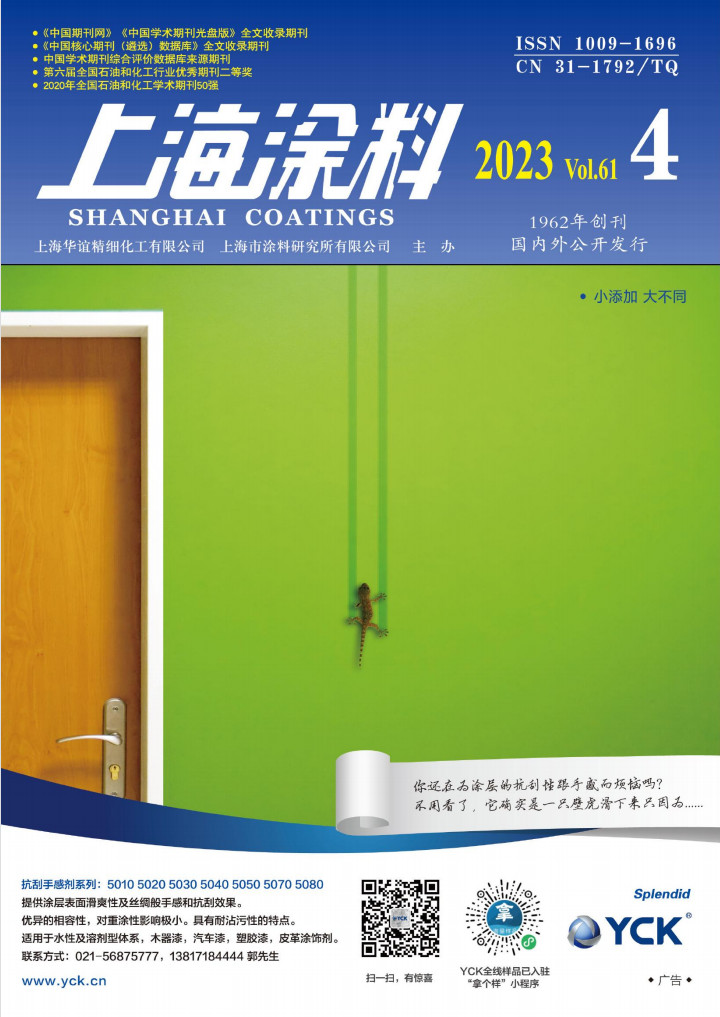
網學報.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