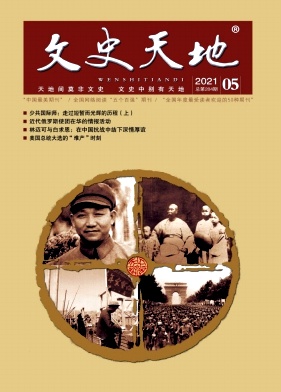淺談清代的尊經(jīng)觀及其代表
顧錫冬
【摘要】 尊敬觀是中醫(yī)學的一大特色。尊經(jīng)觀的來源主要是由于儒家文化的熏陶,到了清代正式成熟。探討了清代各醫(yī)家及錢塘醫(yī)派對中醫(yī)學尊經(jīng)觀的影響。
【關鍵詞】 尊經(jīng)觀;黃元御;陳修園;徐大椿;錢塘醫(yī)派;張卿子;張遂辰
尊經(jīng)是中醫(yī)學的一大特色。在幾千年的傳承中,引經(jīng)據(jù)典,考鏡源流,一直為我們中醫(yī)學所重視,從而形成了中醫(yī)學的尊經(jīng)觀。
1 尊經(jīng)來源
尊經(jīng)觀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間,而是從古及今一步步發(fā)展而來[1]。明清時期,由于各種原因儒學一統(tǒng)天下。“一宗朱子之學,令學者非五經(jīng)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陳鼎《東林列傳》卷二)。儒家文化中的尊經(jīng)崇古思想非常濃烈,“文必西漢,詩必盛唐”,突出地表現(xiàn)為對古代圣賢的崇拜和對傳統(tǒng)經(jīng)典的迷信。它使得人們習慣于借用經(jīng)典來表達自己的思想,一定要吸收傳統(tǒng)經(jīng)典的養(yǎng)分,才能發(fā)表自己的觀點,即所謂的言論必須“引經(jīng)據(jù)典”。這種思維方式反應在中醫(yī)學上就是徐大椿所云:“儒者不能舍至圣求道,醫(yī)者豈能外仲師之書以治療?[2]及至清代乾嘉年間,尊經(jīng)復古和考據(jù)之風盛行,更是將注釋、闡發(fā)乃至輯佚古代經(jīng)典醫(yī)著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2 尊經(jīng)代表人物
綜觀清代對古典醫(yī)籍的研究,名家大家輩出,學派屢現(xiàn)。
2.1 推尊“四圣”之黃元御
黃元御(1705-1758),名玉路,字以行,又字坤載,號研農(nóng),別號玉揪子,清代山東昌邑黃家辛埠村人。黃氏素有才華,聰明過人,嘗“諸子百家書籍,過目冰消,入耳瓦解”。不幸三十歲時患目疾,為庸醫(yī)所誤,左目失明。自此“委棄試帖”,“考鏡靈蘭之秘,詎讀仲景傷寒”,對《內(nèi)經(jīng)》、《難經(jīng)》、《傷寒論》、《金匱要略》等經(jīng)典著作,刻苦攻讀,溯本求源,理論結合實踐,終于成為一代名醫(yī),乾隆皇帝親賜“妙悟岐黃”以示表彰。
黃氏尊岐伯、黃帝、秦越人、張仲景為“四圣”,稱其著作“爭光日月”。常言自四圣以降,候孫思邈不失古圣之旨。黃氏推崇四圣,認為后人著述多無一線微通,每以錯簡抨擊后世編纂之醫(yī)經(jīng)著作,故其著多名之曰“懸解”。其精心研讀《素問》、《靈樞》、《難經(jīng)》、《傷寒論》與《金匱玉函經(jīng)》,對內(nèi)、難、傷寒、金匱均有精辟的見解,確有“理必內(nèi)經(jīng),法必仲景,藥必本經(jīng)”之感[3]。
2.2 厚古薄今之陳念祖
陳念祖,清代醫(yī)家學(1766-1833年),字修園、良有,號慎修,福建長樂人。幼時家貧,攻舉子業(yè),并兼習醫(yī)學。嘗隨泉州名醫(yī)蔡宗玉(茗莊)學醫(yī),頗有心得。嘗于嵩山井山草堂講學。平生著述甚豐,其醫(yī)學思想皆本《內(nèi)經(jīng)》、《傷寒論》、《金匱要略》,撰成《金匱要略淺注》、《金匱方歌括》、《傷寒論淺注》、《傷寒醫(yī)訣串解》、《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讀》。于仲景之學,他反對“錢塘三張”的錯簡論,其治學嚴謹,力求以“深入淺出,返博為約”,“由淺入深,從簡及繁”。后世將其醫(yī)書合刊為《南雅堂醫(yī)書全集》或稱《陳修園醫(yī)書十六種》。
陳念祖是一位特別尊經(jīng)崇古的醫(yī)家,這一點在《醫(yī)學三字經(jīng)》中尤為明顯。他在原著“凡例”中稱:“是書論證治法,悉尊古訓,絕無臆說浮談。以時法列于前,仲師法列于后,由淺入深之意也。”又云“學醫(yī)始基在于入門,入門正則始終皆正,入門錯則始終皆錯,是書闡明圣法,為入門之準。”在其自注中,推崇贊頌仲景方治之語比比皆是,對張仲景及其著作尊崇到了頂禮膜拜的地步,而同時對仲景之后的歷代醫(yī)家的方治,則往往持鄙視態(tài)度,有時貶之過甚,失于偏頗。在他看來,明清諸家雖各有所長,但以古代經(jīng)典衡量,皆有缺憾,大多徘徊逡巡于仲景之門,很少深入內(nèi)室者。在他的心目中,此期只有柯琴、徐彬、尤怡、喻昌、張志聰、高世拭等才能領悟經(jīng)典之旨,直窺仲景堂奧。
陳修園推崇這些研治《傷寒論》、《金匱要略》的著名醫(yī)家是有其道理的,因為他認為“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學醫(yī)者只有認真學習經(jīng)典,才能打下厚實的基礎。若為圖省力,走捷徑,棄中醫(yī)經(jīng)典而不讀,只看一些明清時醫(yī)方書,雖也能于臨證時應付,卻終難成為良醫(yī)。這一點上來說,對于現(xiàn)今的中醫(yī)學教育現(xiàn)狀更加有意義。但是他的這種態(tài)度使得他對清代崛起于醫(yī)界的新興醫(yī)學理論——溫病學說及其代表人物葉天士、薛生白、吳鞠通等只字未提,足可見其思想陳舊保守,及對溫病新學說偏見之深。
2.3 不薄今人愛古人之徐大椿
“不薄今人愛古人”之說基本上表達了清代康乾名醫(yī)徐大椿的古今醫(yī)藥觀[4]。徐大椿,字靈胎,晚號洄溪老人,世居江蘇吳縣。在《清史稿》和著名文學家袁枚的《小倉山房續(xù)文集》中有其傳。他在如何評價古代醫(yī)藥成就這一問題上,他大致繼承了儒家崇古尊經(jīng)的思想傳統(tǒng),認定神農(nóng)、岐伯、黃帝是創(chuàng)立醫(yī)藥學的圣人,《神農(nóng)本草》、《黃帝內(nèi)經(jīng)》為不可移易之經(jīng)典。尤其對張仲景推崇備至,乃至無以復加:“夫仲景先生,乃千古集大成之圣人,猶儒宗之孔子。”“仲景《傷寒論》中諸方,字字金科玉律,不可增減一字。猶之錄六經(jīng)四子語。”他主張醫(yī)者“言必本于圣經(jīng),治必尊乎古法,學有淵源,而師承不絕”,否則,難稱之為醫(yī)。后人對他的這一主張褒貶不一,毀譽參半。
他雖然尊經(jīng)崇古,但不像陳修園那樣偏激。他精辟地分析了后世某些藥效不可憑信的多種原因。例如誤將一方之效作為一藥之效:“或古方治某病,其藥不止一品,而誤以方中此藥專治此病者。”這種移方效做藥效的錯誤作法即便在現(xiàn)代依然存在。此外,還有“以己意推測而知者,又或偶愈一病,實非此藥之功而強著其效者者,種種難信”。對金、元醫(yī)家創(chuàng)立的歸經(jīng)引經(jīng)之說,在徐大樁看來更是主觀“穿鑿”。像這樣一針見血分析中藥某些效用的不可憑信之處,千古之下,唯有徐大椿!
3 尊經(jīng)代表醫(yī)派
除了以上介紹的各個醫(yī)家,在江南的杭州,誕生了尊經(jīng)崇古的一個學派,即錢塘醫(yī)派[5],他們著書立說,開壇講課,成為了清代尊經(jīng)崇古的中流砥柱。
“錢塘醫(yī)派指的是明末及清代,以錢塘醫(yī)家張卿子為開山祖,以張志聰、張錫駒為中堅人物,并有高世拭與仲學輅為傳承代表的,以侶山堂為主要活動場所,集講學、研究與診療活動為一體的,以維護舊論為學術主張的醫(yī)學流派”[6]。
這個醫(yī)派有三個特點,一是臨床療效卓著而名噪深巷,二是理論功底深厚以維護醫(yī)經(jīng)舊論見長,三是醫(yī)學教育與集體研究相結合而富有創(chuàng)新啟后的傳承力量。
錢塘醫(yī)派的“維護舊論”,其本質是“尊經(jīng)崇古”,也就是對《黃帝內(nèi)經(jīng)》、《傷寒論》、《金匱要略》、《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等醫(yī)學典籍正本清源,全面繼承。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有其深刻的社會文化背景的。仲學輅認為,“元代以前太醫(yī)院之所以名醫(yī)多,是因為考試科目包括《素問》、《難經(jīng)》、《千金方》等經(jīng)典醫(yī)籍,選授嚴格。明代太醫(yī)院之所以名醫(yī)少,是因為不考核經(jīng)典,僅考一篇文章,一首歌訣,選技條件過低。”明末清初時期,不少醫(yī)生“重今輕古”,不愿意在醫(yī)學經(jīng)典的研習上下苦功,一意走捷徑,圖速成,僅憑當時流行的通俗醫(yī)書方書行醫(yī),結果根基淺、基礎差而醫(yī)術低下。
錢塘醫(yī)派面對這種庸醫(yī)泛濫、積重難返的局面,振臂高呼,固本洞源,尊經(jīng)崇古,而且苦下功夫,積極實踐,這實際上是一個力挽狂瀾的舉措。
3.1 錢塘醫(yī)派的開山祖張卿子
張卿子,名遂辰,號相期,生于明萬歷十七年(公元1589年),卒于清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原籍江西,其祖遷居浙江錢塘定居。其與弟子張志聰、張錫駒并稱“錢塘三張”。《仁和縣志》稱他“少贏弱,醫(yī)不獲治,乃自檢方書,上自歧、鵲,下至近代劉、張、朱、李諸大家,皆務窮其旨”。遂辰自學成才,臨證經(jīng)驗豐富,對傷寒猶有研究。其首倡“維護舊論”,是醫(yī)家中尊王(叔和)贊成(無己)之甚力者。所著《張卿子傷寒論》至今仍是研究傷寒學必讀之書,另外尚著有《張卿子經(jīng)驗方》、《秘方集驗》。遂辰于醫(yī)學最大貢獻莫過于培植了一批學驗俱富的弟子。這些弟子繼承和發(fā)展了他的學術思想,為維護和恢復醫(yī)經(jīng)的本來面目相繼作了不懈的努力。
3.2 錢塘醫(yī)派的中堅人物張志聰
張志聰,字隱庵,生于明萬歷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約卒于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志聰從師張卿子,盡得其傳,而“維舊尊古”思想則更勝其師。一生著作有:《侶山堂類辨》、《本草蒙原》、《素問集注》、《靈樞集注》、《傷寒論集注》、《金匱要略集注》等。由于志聰建侶山堂論醫(yī)講學,同道及生徒從學者甚眾,故名望在遂辰之上,錢塘醫(yī)派的真正形成可以說是由他完成的。志聰除同學張開之,沈亮辰、張錫駒外,尚有莫仲超等十多人,其門人有朱濟公等十多人,堪稱一代大師。張志聰主持編著的《黃帝內(nèi)經(jīng)素問集注》和《黃帝內(nèi)經(jīng)靈樞集注》,是一種影響頗大的《內(nèi)經(jīng)》全注本。
張志聰提出“醫(yī)以力學為先”。“《素問》注疏告竣,復借同學諸公,舉《靈樞》而詮釋之。因知經(jīng)意深微,旨趣層析,一字一理,確有旨歸,以理會針,以針悟證,殫心研慮,雞鳴風雨,未敢少休。”他二十年如一日鉆研仲景之學,在完成《傷寒論宗印》時感到尚有不足之處,乃先請同學們一起來訂正,又在講課中征求大家的意見,最終形成二稿,定名《傷寒論綱目》。接著又在《傷寒論綱目》的基礎上,撰著《傷寒論集注》,功力之深,可見一斑。
錢塘醫(yī)派的學術思想特色可以概括為四個字:維舊尊古。他們主張學歧黃術必潛心研讀醫(yī)經(jīng),而除《內(nèi)經(jīng)》與仲景之書外,其他都不可讀,甚至認為《難經(jīng)》也是后人偽作而不足信。這顯然失之片面。然而,他們反對對醫(yī)學經(jīng)典著作的隨意增減章節(jié)與竄修,為了恢復醫(yī)經(jīng)的本來面目下苦功夫,他們端本洞源,引經(jīng)據(jù)典,著書立說,且前赴后繼數(shù)十年之久,無可爭議的是為尊經(jīng)復古的中堅力量。
尊經(jīng)觀自開始萌芽到正式形成,直到錢塘醫(yī)派達到頂峰,其間或支持或反對,不乏其人。但是尊經(jīng)觀在中醫(yī)學中生根發(fā)芽已經(jīng)是一個不爭事實。清代是尊經(jīng)觀發(fā)展的成熟時期,其眾多的代表人物和學派的形成即是證明。研究尊經(jīng)觀對中醫(yī)學的影響,必將有益于我們認識和推廣中醫(yī)學,并且實現(xiàn)中醫(yī)藥走向世界的夢想。
【


酵工業(yè).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