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農(nóng)家收支研究
張 研
一、農(nóng)家生活消費
在消費、生產(chǎn)、交換、分配構(gòu)成的社會生產(chǎn)全過程中,消費既是起點,又是終點,既是生產(chǎn)發(fā)展的原因和動力,又是生產(chǎn)發(fā)展的結(jié)果和體現(xiàn)。消費分時期、分層。處于不同時期、不同經(jīng)濟地位的人,消費觀念、消費內(nèi)容、消費質(zhì)量、消費水平均不相同。18世紀前后,中國農(nóng)業(yè)人口占總?cè)丝诘?0%左右。農(nóng)民的生活消費代表了全社會普通生活消費的主流。而不同階層的農(nóng)民,生活消費方式與質(zhì)量又均不同。為簡明、集約考察總體上的情況,我們選擇以自耕農(nóng)為主體的“小農(nóng)”作為待“解剖”的“麻雀”(以下農(nóng)家生計收入亦同)。
這是由于,清初自耕農(nóng)經(jīng)濟有較大規(guī)模的發(fā)展,成為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的巨大推動力量之一。清中后期,因移民墾荒、邊疆開發(fā)以及由傳統(tǒng)“諸子平分”繼承法而引起大土地所有的不斷細分,新的自耕農(nóng)經(jīng)濟仍然不斷生長。盡管自耕農(nóng)經(jīng)濟十分脆弱,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中屬于常變量,隨著人口增多或遇天災(zāi)人禍,有被地主吞噬而淪為佃農(nóng)或流民的趨勢;盡管清代“農(nóng)民”的構(gòu)成呈現(xiàn)出階段性的變化,某一地區(qū)某一時期某一階段自耕農(nóng)經(jīng)濟為主或被地主——佃農(nóng)經(jīng)濟、被大地主經(jīng)濟為主所取代,但較多地區(qū)較長時段自耕農(nóng)經(jīng)濟發(fā)揮主要作用仍是不爭的事實。特別如姜濤所說,地主與農(nóng)民之間,尤其是那些處于邊緣的中小地主與富裕農(nóng)民之間,已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一些力農(nóng)起家的富裕農(nóng)民有可能很快上升為地主,若干地主僅因分家析產(chǎn)便可降為普通農(nóng)戶。土地所有權(quán)與使用權(quán)的進一步分離,還使得不少地方出現(xiàn)了地主與佃戶分掌“田底”與“田面”的現(xiàn)象,地主對土地的任意支配權(quán)也受到了抑制。[1]方行提出佃農(nóng)中農(nóng)化的命題[2];胡成提出由于農(nóng)業(yè)雇工工價上漲導致地主經(jīng)營式農(nóng)場衰敗的命題[3];章有義列舉佃仆大都擁有自己獨立經(jīng)濟的示例[4];張研征引中小地主艱難度日的佐證[5]等,均可見“農(nóng)民”構(gòu)成兩端階層的生活向以自耕農(nóng)為主體的“小農(nóng)”靠攏的現(xiàn)象。
生活消費,包括延續(xù)家庭成員生命的“生存消費”,以及提高家庭成員德性、智力和滿足家庭成員精神生活的“文化消費”兩部分。其中,“生存消費”屬于基礎(chǔ)層次,消費需求彈性小,只有保證這一層次的消費,消費需求才會向上一層次的“文化消費”延伸和發(fā)展。
清代農(nóng)民“生存消費”的首位,是食物。那么,清代農(nóng)民食物的第一個問題是“肉食,還是素食”呢?
二千多年前,中國傳統(tǒng)社會便分為“肉食者”與“素食者”兩個對立集團。明清以農(nóng)民為主體的絕大多數(shù)人仍然以糧食為主要食物,很少吃肉或根本不吃肉。很多縣志記載“貧家終年不見肉”,有人終生不知肉味。一般農(nóng)家只喜喪、祭祀、餉賓、年節(jié)[6]、農(nóng)事大忙之日方略動葷腥,“七八口之家割肉不過一二斤,和以雜菜面粉淆亂一炊”;“度歲乃割片肉為水餃”,“平日則滾湯粗糲而已”[7]。方行估計明清江南農(nóng)民全年大約有20個吃葷日,其余345日吃素。當然,他又說,這345日也不是絕對食素,有的地區(qū)“間用魚”。明代松江西鄉(xiāng)農(nóng)民即已“吃魚干白米飯種田”[8]。
農(nóng)家不食或少食肉,并不妨礙他們從經(jīng)營角度出發(fā)供給雇工肉食,因為他們諳熟“善使長工惡使牛”的道理。“以雇工而言,口惠無實即離心生……做工之人要三好:銀色好、吃口好、相與好;做家之人要三早,起身早、煮飯早、洗腳早,三號以結(jié)其心,三早以出其力,無有不濟”,因而他們自家“非祭祀不割牲,非客至不設(shè)肉”,以蔬食為主,卻設(shè)法給雇工食肉,以免“灶邊荒了田地”[9]。據(jù)張履祥《補農(nóng)書》記載,明中期供應(yīng)雇工飲食的舊規(guī)是夏秋1日葷2日素;春冬1日葷3日素。清前期雇工“非酒食不能勸,比百年以前,大不同矣”,為夏秋1日葷1日素,重活累活連日葷;春冬1日葷2日素,重活累活多加葷。也就是說,清前期夏秋農(nóng)忙季節(jié),雇工每月吃葷日從明中期的10天增為15天,體力勞動繁重時“連日葷”;春冬農(nóng)閑季節(jié),每月吃葷日從明中期的七八天增為10天,體力勞動繁重時“多加葷”。據(jù)陶煦《租核》記載,到清末,農(nóng)業(yè)雇工夏秋日總20日葷、春冬總10日葷。農(nóng)忙的夏秋兩季,每月吃葷日數(shù)又增加了5天。明末以前,葷日“鲞肉每斤食八人,豬腸每斤食五人,魚亦五人”,數(shù)量與質(zhì)量均無變動,只是從吃葷日數(shù)的增加上,體現(xiàn)供應(yīng)數(shù)量的增加。清中期以后,葷菜鲞肉、豬腸之類改為豬肉,數(shù)量亦有增加——“葷不用豬腸而用肉”,忙工1人“食肉半斤”,雇工4人“食肉一斤”,“余曰亦不純素,間用魚”。[10]
方行以為,雇工食物供給一般以農(nóng)民生活水平為準,“水漲船高”,明末至清末雇工食物供給的改善,應(yīng)該反映了農(nóng)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1]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農(nóng)民有飲燒酒的習慣。如山西孝義縣“民用儉約”,“所食粗糲,不堪下咽”,“獨不能戒酒”[12]。方苞認為,10人之中至少有4人飲酒,“一人其量以中人為率,一日之飲必耗二日所食之谷”[13]。酒與肉往往相聯(lián)。清中后期有不少如下記載:“村人趁墟食貨交易,酒罌肉碗四顧狼籍”;“貧民無產(chǎn),傭力耕作,索值日不百錢,酒食必責豐備,狂飲大嚼”;“值令節(jié)乃豐豆饌,下逮傭作酒肉恣飯啖無吝焉。惟獨嗜酒,雖窮鄉(xiāng)僻壤,皆家有藏酒,以備不時之需”;“民喜口腹甚之。家無擔石之儲,一聚飲間羅列珍膳,若素封之家,雖稱貸不惜也”;“飲食無貧富,多好飲酒,款客肴饌,務(wù)豐一席,所費動至五六千三四千不等”,“不必歲時伏臘,即偶爾小聚,亦必盡醉,呼拳拇戰(zhàn),聲達街衢,以茲三里之城,酒館林立”[14]。這些或可作為方行結(jié)論的佐證。
盡管如此,在歐洲人眼中,中國屬于“肉食者”的人,吃肉也很少。無論“多么有錢,地位有多高”,消費的肉食“為數(shù)甚微”,“好像只是為了增加食欲才夾幾塊豬肉、雞肉或別的肉吃”。“肉切成能一口吞下的小塊,有時甚至剁成餡,作為‘菜’的配料使用”。歐洲人看來,不管中國烹調(diào)事實上多么講究,肉還是少得叫人吃驚。歐洲畜牧業(yè)不僅提供大量畜力,而且還提供相當數(shù)量的肉食和乳品。中世紀后期德國每人每年肉食達100公斤以上,柏林每人每天的肉食量為3磅;意大利佛羅倫薩城9000居民一年吃掉了4000頭牛、60000頭綿羊、20000頭山羊、30000只豬。[15]
素食,固然與中國發(fā)達的農(nóng)耕環(huán)境及傳統(tǒng)飲食習慣有關(guān),但布羅代爾以為,食物是一個人社會地位的標志,也是他周圍文明或文化的標志。每當人口增長超過一定水平,人們就勢必更多地依賴植物。總體上吃糧食或吃肉,取決于人口的多少。道理十分簡單:如果按單位面積計算,農(nóng)業(yè)提供的熱量遠遠勝過畜牧業(yè)。撇開事物質(zhì)量的好壞不談,農(nóng)業(yè)養(yǎng)活的人數(shù)要比畜養(yǎng)牲畜多10至20倍。如孟德斯鳩所說:“別處用以養(yǎng)育牲畜的土地,在這里直接為人的生存服務(wù)”。一位18世紀在北京工作的傳教士明確指出:人口過多,迫使中國人不養(yǎng)牛羊,因為供牛羊生活的土地必須用來養(yǎng)活人”,“法國與中國的養(yǎng)牛數(shù)量至少為十比一”,于是“田里缺少肥料,飯桌上缺少肉,打仗缺少馬”,“為收獲同等數(shù)量的糧食需要付出更多的勞動,使用更多的人”[16]。
第二個問題是,“素食,食什么”?
明清江南農(nóng)民主要食用稻米。布羅代爾引用來華傳教士的記述:“中國人每天吃的都是一盤不加鹽的米飯,這就是一日三餐的面包”;四五碗飯,“左手端碗送到嘴邊,右手拿雙筷急匆匆送進肚里,簡直就像朝口袋里裝一樣,吃一口還先朝碗上吹一口氣”;“米飯在中國總是用白水煮,中國人吃飯就像歐洲人吃面包一樣,從不生厭”。米價的變動在中國能影響一切,士兵的餉銀也以米價為升降指數(shù)。[17] 方行指出,明末清初江南雖有麥豆(統(tǒng)稱“春花”)種植,但當時人口較少,口糧多為稻米。《補農(nóng)書》中未見有以蠶豆、二麥為食,只見有以大麥飼豬喂鵝鴨的記載。清中期以后,江南地區(qū)多熟復種制度發(fā)展,農(nóng)民食雜糧日多。如蘇松地區(qū)“農(nóng)民當春夏之交,藉此麥飯,以種大熟”,蠶豆“自濕至乾,皆可為糧”。夏初,農(nóng)民“磨麥穗以為面,雜以蠶豆”而食,口糧中“麥當其三之一”。[18] 華北農(nóng)民主要食用谷類雜糧。尤以小米、高粱和春麥為主食,雜以豆類、薯類食物和蔬菜。小麥和稻米只有過節(jié)或遇有婚喪嫁娶、招待親朋好友時才可能食用。據(jù)徐浩所舉華北各地民食列表如下[19]:
隨著清中后期人口壓力的增加、玉米蕃薯等作物的普及,南北方種植結(jié)構(gòu)越來越趨向于向少數(shù)高產(chǎn)、粗糧作物集中。農(nóng)民的主食結(jié)構(gòu)也轉(zhuǎn)向粗糧化、搭配式。“常日兩頓,工作三頓,干飯只一頓,早晚兩頓則湯粥間加餅饃,雖有力之家亦然”。其中干飯吃大米,其他兩頓都是雜糧,山民則多吃包谷,“窮民連包煮食,或摘子炒食”,佐以苦蕎、燕麥、洋芋等雜糧[20]。史志宏認為,這種一天吃兩頓、干稀搭配、多吃粗糧雜糧的情況,是當時各地的普遍情形。能做到一天三頓細糧的,只是少數(shù)富人之家。[21]
主食之外還有副食。副食即油鹽、醬醋、菜蔬一類佐餐之食。農(nóng)民種植油菜、花生等榨油食用。油菜“畝收子二石,可榨油八十斤”;“花生菜蔬基本自種自給”。南方“園中菜果瓜蒲,惟其所植。每地一畝,十口之家,四時之蔬,不出戶而皆給”。北方“春冬以菜蔬紅薯白菜,夏秋以羅卜北瓜等物為菜羹,用以佐餐”;“佐味為豆腐小豆腐咸菜番椒。豆腐以黃豆為之,小豆腐以豆汁與各種蔬菜為之”。不少地方“春夏多食野菜,以蔥韭豆腐雞卵為甘旨,菘薯為珍味”。[22]
最后是,“食多少?支出多少?”
前文討論畝產(chǎn)量時,已涉及到清代每人每天吃多少的問題:一般概念是平均每人每日食米1升,月食3斗,“人一歲食米三石六斗”[23]。《補農(nóng)書》中所記農(nóng)民口糧標準是,“凡人計腹而食,日米一升,能者倍之”。雇工口糧是每人每年“吃米五石五斗”,每日吃米1.52升。方行以江南農(nóng)戶多為核心家庭,由夫婦及子女組成,至少有1~2個成年勞動力屬于所謂“能者倍之”之列,5口之家大小口牽算,平均仍可每人日食1升,全年食糧為3.6石,符合江南“大口小口,一月三斗”的民諺。
方行按此算了一筆賬:
農(nóng)戶全年全家口糧約為米18石,常年米價銀1兩1石,則農(nóng)戶每年口糧支出是為銀18兩,副食約每年每人為銀1.4兩[24]。全家5口全年支出為銀7兩。主副食共計25兩,合錢25 000文。
清后期,江南地區(qū)多熟復種制度發(fā)展,農(nóng)家全年食米18石,因1/3改食大麥,余食米12石。時價米石銀2.13兩,銀1兩約錢1 600文。12石米,共約銀25.5兩,合錢40 896文。《安吳四種》載:“大麥較米不及半價,以充口食,一石可抵七斗。和稻米煮粥飯,計麥百斤,可得米七十斤”。按大麥7斗,充口食可抵米5斗計,農(nóng)民口糧大米6石,折成大麥應(yīng)為8.4石。《租核》說,春熟種豆,“畝可得錢七八百,麥亦如之”。假定此800文為大麥畝產(chǎn)7斗之價,則大麥8.4石,應(yīng)約為錢9 600文。加上上述米值,全部口糧約共為錢50 496文,合銀31.56兩。副食中肉類全年按吃葷日20天計,人日用錢30文,全家全年共約用錢3 000文。吃素345日,較雇工日用錢20文折半計算,全家全年用錢共約17 250文。 油鹽柴醬之類副食,消費彈性較小,按人歲約用錢3 000計,全家全年共約用錢15 000文。因稻柴費用另計,須在此扣除8 640文,共約為錢6 350文,飲酒費用納入吃葷日飲食支出費用之內(nèi),不另計。以上副食各項,共約為錢26 600文,合銀16.63兩。主副食共計70 096文,合銀43.81兩。[25]
最后是,“食多少?支出多少?”
前文討論畝產(chǎn)量時,已涉及到清代每人每天吃多少的問題:一般概念是平均每人每日食米1升,月食3斗,“人一歲食米三石六斗”[23]。《補農(nóng)書》中所記農(nóng)民口糧標準是,“凡人計腹而食,日米一升,能者倍之”。雇工口糧是每人每年“吃米五石五斗”,每日吃米1.52升。方行以江南農(nóng)戶多為核心家庭,由夫婦及子女組成,至少有1~2個成年勞動力屬于所謂“能者倍之”之列,5口之家大小口牽算,平均仍可每人日食1升,全年食糧為3.6石,符合江南“大口小口,一月三斗”的民諺。
方行按此算了一筆賬:
農(nóng)戶全年全家口糧約為米18石,常年米價銀1兩1石,則農(nóng)戶每年口糧支出是為銀18兩,副食約每年每人為銀1.4兩[24]。全家5口全年支出為銀7兩。主副食共計25兩,合錢25 000文。
清后期,江南地區(qū)多熟復種制度發(fā)展,農(nóng)家全年食米18石,因1/3改食大麥,余食米12石。時價米石銀2.13兩,銀1兩約錢1 600文。12石米,共約銀25.5兩,合錢40 896文。《安吳四種》載:“大麥較米不及半價,以充口食,一石可抵七斗。和稻米煮粥飯,計麥百斤,可得米七十斤”。按大麥7斗,充口食可抵米5斗計,農(nóng)民口糧大米6石,折成大麥應(yīng)為8.4石。《租核》說,春熟種豆,“畝可得錢七八百,麥亦如之”。假定此800文為大麥畝產(chǎn)7斗之價,則大麥8.4石,應(yīng)約為錢9 600文。加上上述米值,全部口糧約共為錢50 496文,合銀31.56兩。副食中肉類全年按吃葷日20天計,人日用錢30文,全家全年共約用錢3 000文。吃素345日,較雇工日用錢20文折半計算,全家全年用錢共約17 250文。 油鹽柴醬之類副食,消費彈性較小,按人歲約用錢3 000計,全家全年共約用錢15 000文。因稻柴費用另計,須在此扣除8 640文,共約為錢6 350文,飲酒費用納入吃葷日飲食支出費用之內(nèi),不另計。以上副食各項,共約為錢26 600文,合銀16.63兩。主副食共計70 096文,合銀43.81兩。[25]
其他生存資料包括衣被、住房、燃料等。
衣被:據(jù)方行考查,南方農(nóng)民衣被的年消費量,明末所謂“人生所需”,“歲不過布二匹”;清乾隆年間,“一人之身,歲得布五丈,即可無寒”。江南棉布1匹一般長2丈,5丈即為布2匹半。農(nóng)家按男女大小口平均,包括衣服、被帳在內(nèi),每人每年用布2匹,全家5口,每年約用布10匹。明末清初,江南嘉湖一帶,棉布可能還未完全普及,農(nóng)民還要穿用一部分麻布衣,所謂“夏則衣苧,冬則木棉”,“湖州家家種苧為線,多者為布”,西鄉(xiāng)女工“績苧麻黃草以成布疋”。冬衣用布多,夏衣用布少。前述10匹,可按棉6麻4估算。布價取中,按每匹為銀0.33兩計,農(nóng)戶全年用布六匹,約為銀2兩。麻布每匹約為銀0.26兩,4匹約合銀1兩左右。農(nóng)家全年衣用支出共約銀3兩,合錢3000文。
北方農(nóng)民衣被的年消費量,據(jù)徐浩考查,支出不大。如直隸望都“居民率衣土布,自織自用,只取其蔽體御寒,不求華美。尋常衣服,棉改袷,袷改單,敝而后已,雖襤褸之衣,方作鞋履之用,不肯輕于一擲”;山西孝義“鄉(xiāng)民則布絮縷縷,終歲不制衣者十室而九”;五臺“農(nóng)人夏一袷,冬一襖一褲,商賈隆冬走山谷,布襖之外,襲老羊皮馬褂,士類一棉布袍,一棉馬褂,無衣裘衣帛者”。[26] 農(nóng)家平均歲用土布5匹左右,或自織,或買于集市。[27]
清后期,棉布日益普遍,衣著質(zhì)量應(yīng)較粗麻布為優(yōu)。其時土布“每匹約市錢五百文”,全家全年用棉布10匹,是共約錢5 000文,合銀3.13兩。[28]
住房:江南普通民居盛行磚瓦平房,或帶木板的閣樓。蘇州一套普通民居一般為3間6架(檁),一明兩暗,中間正房堂屋為明,兩側(cè)次間臥室為暗,面積共12.16方丈,合91.96平方米[29]。蘇式住房可能因地方潮濕,比其他地區(qū)住房大(其他地區(qū)一般一步架為5~6尺,蘇式一步架為8尺)。但有能力之家仍嫌狹窄,有5間甚至9間開間的。11間以上屬富戶另論。[30] 一般農(nóng)民則居屋簡陋,“鑿坯為門,編茅蓋屋,所在皆是”。
江淮、北方農(nóng)民多居住覆草的土坯房。阜陽、鳳臺一些農(nóng)民土坯墻外鑲一層單磚,名曰“里生外熟”。宅居習慣向陽,因廟門向南開,不取正南向,取東南或西南向。主房一般三間,一明兩暗,明為客廳,暗為臥室,側(cè)跨偏房用作牛屋或廚房。富人家有磚木結(jié)構(gòu)的瓦房,并有深宅大院,高墻門樓,烏漆大門,少數(shù)還蓋有樓房。屋架多用5架檁(3間),也有用7架(5間)、9架(7間)的。多層次住房講究前層低,中、后層依次拔高,避免遮陽。[31]
其他各地區(qū)各民族都有不同風格的宅居。如藏式宅居為石墻平頂?shù)飿牵幻墒秸訛檩p骨架氈包;維吾爾式宅居為平頂木架土坯房;朝鮮式宅居為席地而坐的地炕式宅居;西南少數(shù)民族宅居為干欄式竹樓木樓。另有黃土高原的窯洞、閩南的土樓、云南的“一顆印”以及東北的滿族老屋等。東北民居南北西三面圍炕,西炕供神供祖,南炕睡長輩、北炕睡晚輩。窮人有兩家合住一屋,分住南北大炕的。
置房支出,順治十五年(1658),江南昆山為守墓人出“錢十二緡”贖“瓦居三楹”,即按當時銀價,購一套3間瓦房民居的支出約合銀l0.8兩;乾隆十八年(1753)蘇州“圩田上瓦屋兩間”(屋在“圩田上”,顯系農(nóng)民住房)賣價為銀6兩。[32] 乾隆年間蕪湖莊房3間賣絕價銀4兩[33]。北方農(nóng)民住房支出,徐浩未將其列入家庭經(jīng)常性開支,他以為,置房屬一次性投資,雖花去農(nóng)家多年儲蓄,但可以使用多年[34]。
租房支出,乾隆十六年,蘇州租“在田瓦屋一所”7間,“每年租金四兩七錢”,“內(nèi)扣除修理一兩一錢,實還租銀三兩六錢”;乾隆十八年蘇州租“瓦房三間半,該每年屋租銀一兩六錢”,“內(nèi)免屋租銀四錢,作每年修理之費”,兩項房租,均“隨租米一并交清”[35]。乾隆四十八年徽州租樓房1進計2間,“每年交租錢一千文”,合銀1兩[36]。取中按租3.5間算,每年農(nóng)家租房支出約為銀1.6兩。當然,另有不少佃農(nóng)居住地主提供的“隨田莊屋”,房租不單計算;還有租地基造屋,每年還房地基租銀的,如乾隆十一年徽州“史佑孫租三間屋地基豎造住屋一堂,每年交租九五銀三錢五分”;還有租廁所的,如乾隆三十八年徽州萬富租廁所1個,每年交租錢140文等。[37]
清后期銀錢比價有所變化,1兩銀約合錢1600文。仍以租3.5間、租銀1.6兩算,是為錢2560文。
燃料:方行指出,清代江南平原地區(qū)無煤炭林木,燃料艱難,“日用所急,薪、米二事為重”。農(nóng)民一般用稻草燒茶煮飯。據(jù)陳恒力調(diào)查,舊中國蘇嘉湖杭地區(qū),農(nóng)家每天平均燒稻草15斤,一個月燒450斤,一年應(yīng)需5400斤[38]。據(jù)《沈氏農(nóng)書》記載,“稻草一千八百斤,約價一兩”,5 400斤為銀3兩,農(nóng)家每年燃料支出共約銀3兩。
清后期,據(jù)《租核》記載,稻柴每擔約110~200文,按每擔160文,農(nóng)家全年用稻柴54擔,共約為錢8640文。
方行將清初與清末江南農(nóng)民的生活消費加以比較,結(jié)果是:糧食消費數(shù)量沒有減少,質(zhì)量則有所降低——從全部食用稻米,到稻米與雜糧兼食;衣被數(shù)量沒有變動,質(zhì)量卻有所提高——從棉麻兼用,到棉布普及,再到“以布為恥,綾緞綢紗爭新色新樣”[39]。住房水平?jīng)]有降低,也沒有提高。從支出角度看,糧食支出由銀18兩增為31.5兩,燃料支出由3兩增為5.4兩,消費數(shù)量沒有增加,支出增加主要是物價上漲的原因。住房支出均為銀1.6兩,沒有變動。衣服支出由銀3兩增為銀3.1兩,布的質(zhì)量雖有所提高,但支出基本沒有變動。副食支出由7兩增為16.6兩,增加了9.6兩,則主要是由于副食的數(shù)量和質(zhì)量均有提高。可見清末由于生活水平提高所導致生活消費支出的增加數(shù),約為清初生活消費總支出的30%左右。方行算了一筆賬:
清前期農(nóng)家“生存資料”,即每年用于生活消費的支出=糧食(主食18兩+副食7兩)+衣物3兩+住房1.6兩+燃料3兩=32.6兩。
清后期農(nóng)家“生存資料”,即每年用于生活消費的支出=糧食(主食50 496文+副食26 600文)+衣物5 000文+住房2 560文+燃料8 640文=93 296文(合銀58.31兩)。其中,食物支出約占生活消費總支出的83%,其中,糧食支出約占54%,副食支出約占29%。
可知江南農(nóng)民消費結(jié)構(gòu)的變動,主要表現(xiàn)為食物消費支出在生活消費總支出中的比重上升——由76%上升為83%。其中糧食支出由占生活消費總支出的55%下降為54%,而副食支出卻從占生活消費總支出的21%上升為29%。這種變動是農(nóng)民從蔬食到飲酒吃肉增多的結(jié)果,反映其生活水平的提高。
“文化消費”包括文化教育、祭祀祈賽、婚喪嫁娶等,其重要性雖遠不及維持家庭成員生存、繁衍的“生存消費”,但仍是生活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屬于必要性消費項目。
文化教育:讀書做官、光宗耀祖的傳統(tǒng)價值觀在社會上影響很大,農(nóng)家稍有條件,節(jié)衣縮食也要讓子弟讀書。同時,宗族耕讀助學之風,官學之外書院、社學、義學、族塾、家塾的廣泛存在,科舉制度下下層士人在家鄉(xiāng)教館為生的普遍現(xiàn)象,均為農(nóng)家子弟就近讀書提供了可能。徐浩估計,多數(shù)農(nóng)家子弟大約都接受過或長或短的蒙學教育,所謂“民間子弟七八歲時延塾師教習,先孝經(jīng)四書,漸習本經(jīng)學作文藝,雖冠禮未行,而束發(fā)受書者遵循規(guī)矩,并無浮囂之習,誦讀之聲四境不絕”[40]。
讀書費用低廉,如河南鹿邑“士無恒產(chǎn)”,率以教授為業(yè),一年“饋緡錢數(shù)十千便為極豐”。數(shù)十學童均攤,大約每人每年學費1000文。如嘉道年間徽人包世臣之父借僧舍集蒙童作塾師,所得僅能供兩人口食,“無可寄贍家者”。“兩人口食”是7.6石,合銀7.6兩,一塾學童一般10來人,均攤,大約每人每年學費不到1兩,其時銀貴,仍約合1000文左右。[41] 盡管如此,由于生活貧困,農(nóng)家子弟仍往往輟學。所謂“力田者僅菜粥自給,雖有聰穎子弟,亦多不免失學。村塾之師聚童稚數(shù)十人于老屋中,儀節(jié)不立,咿唔莫辨,每至登麥、刈禾時輒罷業(yè)散去。九月復集則十僅三四矣。往往修補(脯)不給……如是者數(shù)歲,父兄病其無成,俾改習耕作,或操工賈之業(yè)”[42]。
羅茲曼估計,農(nóng)民中“粗通文墨”的人約占30~20%[43]。農(nóng)家的“生存消費支出”,以“制約”的形式,在“教育消費支出”上打下了相應(yīng)的烙印。
祭祀祈賽:包括祭祀、祈報、迎神、賽會等內(nèi)容,按歲時節(jié)慶[44]有序進行,或隨時隨地酬神許愿。此類活動是農(nóng)民的節(jié)日,是常年千辛萬苦卻又前程未卜之際一種不可多得的精神寄托、心靈慰藉,是千愁萬緒的排解和宣泄,所以無不踴躍參加。
祭祀分祭祖、祭神兩種。
祭祖,南方通常家設(shè)祠堂或牌位,族有始祖祠、分支祖祠、大宗祠、小宗祠等。有的宗族祠堂數(shù)量達數(shù)十數(shù)百座之多,如湖南醴陵3000人以上的93個宗族共建祠堂603 個,其中丁氏一族即建有祠堂77座。茶陵“一姓分建宗祉有至數(shù)百所者” [45]。北方大族、士夫故家“多立宗祠,設(shè)祭田,春秋拜掃惟謹,祭畢聚族宴祠中”或“廟祀先祖”,“隆于祀先,雖費而不惜”,一般百姓則“頗忽于祀先”,而“恪事外神”[46]。祭祖務(wù)求供品豐厚,福祚均沾,開銷很大。正式的祠祭一般每年3次:除夕(元旦)、清明、中元(或冬至)。休寧程氏,每年除夕元旦前二日為其祖忠壯公生辰,全體族人要制花燈娛神5日,參加者不下6000人[47]。其他小祭又有花朝、春社、端午、薦新、秋社、重陽、送寒衣以及各祖生辰祭日,也少不得金銀紙錠、三牲果品、酒肉羹飯等花費。祠祭外還有墓祭,乾隆時巨族“祭每從豐而莫重于清明之墓祭”,墓祭時“畫船絡(luò)繹,鼓吹喧鬧,婦女亦乘之以嬉游”。有5年、10年或20年一次的合祭,時“會集族眾,按門分派,豬羊每至百余只,旗傘執(zhí)事,鮮妍擁道,鑼鼓小樂隨行”,“香案古玩、器皿俱備,有功名者皆冠帶輿馬,族大繁者動以千數(shù)”[48]。
祭祖費用一般情況下或者出于族田祀產(chǎn)所入,或者出于族中按戶攤派之費。另有一種是醵金入股,成立各種祀先會、祭祖會等,祭祀受胙的范圍和權(quán)利也由醵金多少、“占股”多少劃定。如清代乾隆、嘉慶年間徽州祁門立有祭祀程氏始遷祖的3會,包括“世忠會”(此會分11牌,前10牌每牌會友10人,11牌會友2人,共102人),正月十三日祭祀;“鑾光會”,(共10會,每會1~2人不等),每年八月十八日祭祀始遷祖生辰;“涼傘會”(此會共5會,每會2人),每年八月十九日集會為始遷祖“送神”。“會”下的“牌”、“會”,是按會眾認股而形成的組織機構(gòu),有的一股一會,每會(股1~2人至10人不等),有的數(shù)股一會。各會輪流主辦對始遷祖的祭祀。[49]
祭神,囊括了祈報、迎神、賽會等內(nèi)容。
祖先神靈并不主宰一切。在這里,“共同社會性”與“利益社會性”互為表里,揉雜儒、道、佛、帝王將相、鬼怪神仙、文人俠客等各種素材,構(gòu)筑了極為龐雜的民間信仰體系。其表現(xiàn)一為神祇崇拜;一為春秋祈報;一為迎神賽會。
神祇崇拜有體現(xiàn)上層統(tǒng)治權(quán)力的神祇崇拜,如自明朝洪武年間敕令各府州縣建立的城隍系統(tǒng),如歷代賢良忠臣祠廟系統(tǒng)、孔孟文廟系統(tǒng)等。更有體現(xiàn)著地方特定區(qū)域社會共同渴望與追求的神祇崇拜。如安徽歙縣有張許二將軍祠,所祀唐朝張巡、許遠二將軍成為當?shù)乇Wo神。每年三月二十八日民人群聚祠下,割牲瀝酒,薦獻娛神,以酬謝其對地方的保佑。[50]涇縣東鄉(xiāng)崇拜牛王大帝。牛王大帝即漢渤海太守龔遂,鄉(xiāng)人以賣刀買牛故事訛傳之,稱為牛王大帝,以為地方保護神。凡二三十里以內(nèi)人家,必備香火往酬,甚至有百里外而來者。[51]上述祁門六都村,有新、老張王會分別為11會、13會,會首25人,每年七月二十四日祭祀唐朝忠烈王汪公大帝、東平王張公大帝,“以祈福生人”,即以汪公、張公作為地方保護神。[52]小農(nóng)家庭的神祇崇拜體現(xiàn)更多的實用功利性,他們熱衷于拜財神、拜觀音、拜關(guān)公……以求財求子求利求福。所謂“佞佛之風,村民最盛。每歲二三月之間,荒棄所業(yè),奔走寺觀,燃香誦佛,雜沓成群”[53]。
祈報又囊括了迎神、賽會等內(nèi)容。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靠天吃飯,農(nóng)家春天祈禱一年風調(diào)雨順、五谷豐登;秋后酬報諸神、老天的恩賜,由此形成農(nóng)家春秋祈報習俗。除此之外,天旱求雨,得雨還愿等也十分普遍。祈報時殺豬宰羊、聚餐演戲,或賽龍舟,或跑旱船,或游火龍,或抬神輿出巡,或扮百戲娛神,或擁神游街演劇,鳴金擊鼓,晝夜不絕。
祭神費用自然要納入農(nóng)家的支出,所謂“醵錢演戲”;“春秋祈報,長者斂資,少者趨事”;“每秋后竟作賀作會,醵錢相助,喧闐來往,無虛日”;“秋趨各村鄉(xiāng)醵錢祀里社五谷之神,行報賽禮,亦有行有三四月者,謂之春祈,納稼后雨”等。[54]
至于祭神費用的數(shù)量,有記載說,“農(nóng)家一歲之入,或不足一歲交際之用,有展轉(zhuǎn)負累以至于貧者”[55]。地區(qū)性的祈報活動一般按村落、宗族輪年值首,通常一二十年輪一次。既輪,全族全村均“視為重大問題,籌募款費,推舉司事,以辦此平安神戲”。有“值年之村戶,往往因貧而售典產(chǎn)業(yè)以當此門戶”,以為若破此例,“當犯神譴而觸眾怒也”[56]。農(nóng)家參加祈報活動或自行祈神、進香、還愿,也不吝解囊,所謂“衣食唯布蔬”,“唯迎神賽會最為靡耗”,“演戲獻神,溫飽之家隨時侈糜,貧戶亦典質(zhì)裳衣,詣廟祈福”[57]。
婚喪嫁娶,徐浩指出,由于習俗使然,農(nóng)家在這些項目上的消費往往是盡其所有,不少人家甚至于超過自己所能夠承受的極限,從而使本來很有限的家庭收入超負荷支出,嚴重影響了農(nóng)家正常的生產(chǎn)生活安排。
北方農(nóng)家生產(chǎn)生活水平相對江南農(nóng)家要低,可推知江南農(nóng)家婚喪嫁娶方面的消費支出。
二、農(nóng)家生計收入
農(nóng)民家庭既是消費單位,又是生產(chǎn)單位。以上生活消費支出,需要生計收入的支持。那末,農(nóng)民采取何種經(jīng)營規(guī)模和經(jīng)營方式,方能維持收入與支出的平衡,養(yǎng)活一家老小呢?
制約經(jīng)營規(guī)模的因素,第一是生存消費的需求;第二是土地畝產(chǎn)量;第三是生產(chǎn)能力。以下分別南、北方,將這三點結(jié)合起來進行考察和分析。
南方 在前文關(guān)于土地資源配置的討論中,已知李伯重、方行提出或論證了清代江南普通農(nóng)戶經(jīng)營規(guī)模中“人耕10畝”的標準模式,認為這種模式既是最佳的、又是可能的、而且是實際存在的人地資源配置模式。
如前述,按黃冕堂推算,清代江浙平均畝產(chǎn)2~2.67石(稻谷);李伯重推算,清中期江南畝產(chǎn)約為4.6石(稻谷)。即以李伯重推算為準:江南農(nóng)戶5口之家2個勞動力,種田20畝,每年收獲稻谷92石。晾曬減去5%[58],供賦役減去4%[59],再減去種子1.6石(0.08石/畝),還剩82.3石,合米41.2石或銀41.2兩(清后期合錢62920文)。
清前期全家一年口糧需求約為米18石合銀18兩,副食需求約為7兩,加衣物3兩、住房1.6兩、燃料3兩共32.6兩;清后期全家一年口糧需求約為米18石合銀31.84兩或錢50 496文,副食需求約為銀16.63兩或錢26600文,加衣物銀3.125兩或錢5000文、住房銀1.6兩或錢2560文、燃料銀5.4兩或錢8640文,共約銀58.31兩或錢93296文。可知清前期江南農(nóng)戶依據(jù)農(nóng)田收入的生存消費支出有余,清后期江南農(nóng)戶依據(jù)農(nóng)田收入的生存消費支出不足。如下表。
而李伯重所謂的“人耕10畝”,似乎等同于或傾向于“戶耕10畝”,因為他以江南農(nóng)戶5口之家一夫一婦2個勞動力中婦女多不事耕種,或在耕種中只起輔助作用。事實上,他從人口與耕地數(shù)字的角度,明確論述了江南明清兩代人口最多時期農(nóng)戶平均耕地接近“戶耕10畝”的狀況:“在1620年前后大約是每戶(即一個家庭農(nóng)場)平均有耕地14.5畝,而1850年時則是每戶約耕8.5畝”,“就清代中期的情況而言,‘戶耕十畝’之說”“可以大致成立”,“而在清代前期,由于農(nóng)戶數(shù)比1850年數(shù)少,戶均耕地更接近于10畝”[60]。
這樣,如果一戶農(nóng)家種田10畝,每年收獲46石,晾曬減去5%[61],供賦役減去4%[62],再減去種子0.8石(0.08石/畝),還剩41.15石,合米20.6石或銀20.6兩(清后期合錢32 960文)。可知清前期江南農(nóng)戶依據(jù)農(nóng)田收入的生存消費支出不足,清后期江南農(nóng)戶依據(jù)農(nóng)田收入的生存消費支出嚴重不足。如下表:
需要注意的是,這里只計算了生存消費支出,如果將文化消費支出完全省略(實際并無可能),那末還有不能省略的生產(chǎn)工本支出沒有計算在內(nèi)。而李伯重又舉清人張海珊之言:乾隆時江南“一夫耕(田)不能十畝”,“(蘇州府)人浮于田,計一家所耕田不能五畝”;姜皋之言:道光時,松江佃農(nóng)多“自種租田三五畝”;英國傳教士之言:光緒時,江蘇南部一個農(nóng)業(yè)雇工僅耕種水田6畝,杭州亦然。[63] 如此,缺額占需求百分比將達到70%以上,真真是叫人沒法活了。


展.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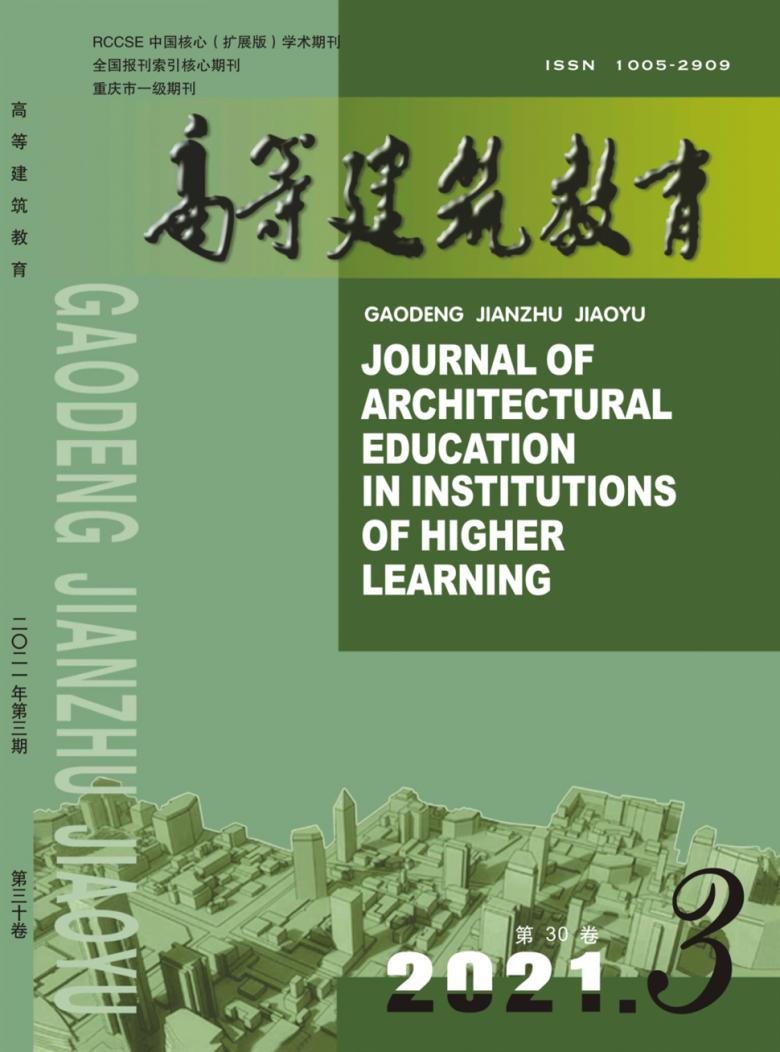
于我們.jpeg)